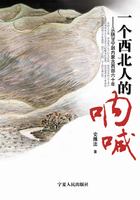【荒野来客】
吉尔阿特和塔门尔图
在吉尔阿特,站在最高的山顶上四面张望,也看不到一棵树,看不到一个人。光秃秃的沙砾坡地连绵起伏,阴影处白雪厚积。遥远而孤独的羊群在半山坡上缓慢曼延,倾斜的天空光滑而清脆。吉尔阿特的确是荒凉的,但作为春牧场,它的温暖与坦阔深深安慰着刚从遥远寒冷的南方荒野跋涉而来的牧羊人们的心灵。
还不到五月,卡西就换上了短袖T恤,在微凉的空气中露出了健康明亮的胳膊。我们拎着大大的编织袋去南面山谷里拾牛粪。我们小心地绕过沼泽,沿着山脚陡峭的石壁侧身前行。
阳光畅通无阻地注满世界,荒野的阴冷地气在阳光推进下,深暗而沉重地缓缓下降,像水位线那样下降,一直降到脚踝处才停止,如坚硬的固体般凝结在那个位置,与灿烂阳光强强对峙。直到盛大的六月来临,那寒气才会彻底瘫软、融解,深深渗入大地。
无论如何,春天已经来了。白色的芨芨草丛在大地上稀稀拉拉扎生出纤细绿叶,灰绿色野草稀稀拉拉冒出细碎的点状叶片。尤其在低处的水流和沼泽一带,远远看去甚至已涂抹了成片的明显绿意。但走到近处会发现,那些绿不过是水边的苔藓和微弱的野草。
流经我们驻扎的山坡下的那条浅浅溪流就是从这条山谷的沼泽中渗出的。由于附近的牲畜全在这片沼泽边饮水,山谷里的小道上和芨芨草枯草丛中遍布着大块大块的牛马粪团。我们一路走去,遇到看上去很干的,先踢一脚,其分量在脚尖微妙地触动了一下,加之滚动时的速度和形态,立刻能判断它是否干透了。干透的自然拾走。没干透的,那一脚恰好使它翻了个面,潮湿之处袒曝在阳光下,加快了最后的潮气的挥发速度。于是,在回去的路上或者第二天路过时,再踢一脚就可以把它顺手拾起丢进袋子里了。
有时候踢翻一块牛粪,突然暴露出一大窝沸沸扬扬的屎壳郎,好像揭开了正在大宴宾客的宫殿屋顶。屎壳郎的名字虽然不好听,其实算得上是漂亮可爱的昆虫。它有明净发亮的甲壳和纤细整齐的肢爪,身子圆溜溜的,笨拙而勤奋。相比之下,张牙舞爪、色泽诡异的蝎子之类才让人畏惧而不快。
每当卡西踢翻一块大大的干牛粪看到那幕情景,总会夸张地大叫,指给我和胡安西看,然后冲它吐口水。
越往下走,我们三人彼此间离得越远,肩上扛的袋子也越来越沉重。我走到一块大石头边放下袋子休息了一会儿。抬头环顾,在沼泽对岸看到了卡西,她正躺在阳光下明亮的空地上休息。她的红T恤在荒野中就像电灯泡在黑夜里一样耀眼。离她不远处,男孩胡安西手持一根长棍往沼泽水里捅来捅去地玩,他后脑勺两条细细的小辫在风中飘扬。
半个小时后我们扛着各自鼓鼓的大袋子会合,走上回家的路。胡安西也背了小半袋,劳动令这个六岁的孩子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沉静而懂事。他一声不吭走在最后面,累了就悄悄靠在路边石头上休息一下。
快到家的时候,我们在半坡上站定了回头看,胡安西仍在视野下方远远的荒野中缓缓走着,孤零零的,小小的一点点儿,扛着袋子,深深地弓着腰身。
坡顶上,毡房门口,亲爱的扎克拜妈妈蹲在火坑边。她扒开清晨烧茶后的粪团灰烬,再搓碎一块干马粪撒在上面,俯下身子连吹几口气。很快,看似熄透了的灰烬如苏醒一般在粪渣间平稳升起几缕纤细的青烟。她又不慌不忙盖上几块碎牛粪,这时大风悠长地吹上山坡,烟越发浓稠纷乱。她再猛吹几口气,透明的火苗轰然爆发,像经过漫长的睡眠后猛地睁开了眼睛。
我连忙赶上前放下肩上的袋子,将所有牛粪倾倒在火坑边。妈妈拾捡几块最大的,团团围住火焰。一束束细锐锋利的火苗从干燥的牛粪缝隙中喷射出来。妈妈在火坑上支起三脚架,调好高度,挂上早已被烟火熏得黑乎乎的歪嘴铝壶。
就是在这一天,可可走了,斯马胡力来了。
毡房后停着两辆摩托车和一匹白蹄黑马。除了斯马胡力,扎克拜妈妈的二女儿莎勒玛罕及丈夫马吾列也来了。骑马来的则是卡西的一个同学。
我和卡西洗手进毡房之前,把又脏又破的外套脱下来塞进缠绕在毡房外的花带子缝隙里,再从同样的地方抽出一把梳子拢了拢头发,取下发夹重新别了一遍,还互相问一问脸脏不脏。
明明只来了四个客人和两个孩子,却顿觉房间里挤得满满当当。大家围着矮桌喝茶,食物摊开了一桌子。可可缩在堆叠被褥的角落里翻看相片簿,两个小孩子跑来跑去。还有一个跑不利索的婴儿端端正正地靠着矮桌号啕大哭。
我们在吉尔阿特唯一的邻居阿勒玛罕大姐也过来帮忙了,此时她正斜偎在巨大的锡盆边大力揉面,说要做“满得”招待客人。“满得”其实就是包子一样的食物。
昨天,妈妈和阿勒玛罕去了北面停驻在额尔齐斯河南岸的托汗爷爷家喝茶,带回了好几块宴席上吃剩的羊尾巴肥肉,煮得腻白腻白。另外还有好几大片厚厚的、浮在肉汤上的白色凝固油脂。当我得知阿勒玛罕要把这些好东西剁碎了做包子馅时,吓得一声不吭,暗暗决定等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突然嚷嚷肚子疼。
但真到了包子热气腾腾出锅的时候,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在拼命忍抑的情况下还是不知不觉吃了三个……边吃边极力提醒自己:嘴里正嚼的是白白的肥肉,腻汪汪的羊油……一点儿用也没有。
想在荒野里抗拒食物,几乎不可能。在这样的地方,但凡能入口的东西总是发疯似的香美诱人,枣核大的一截野生郁金香的根茎所释放的一点儿薄薄的清甜,都能满满当当充填口腔,经久不消。
饱餐之后总会令人心生倦意。大家在花毡上或卧或坐,很少交谈。
卡西的同学是东面五公里处的邻居,来认领自家失群的羊羔。这小子坐在上席,一声不吭地吃这吃那,把可可放羊时从悬崖上摘回的一大把野葱吃得只剩三根。
昨天傍晚我们赶羊归圈时,发现多出了一只羊羔,可可就把它单独拴起来。今天出去放羊时他散布出这个消息,中午失主就找上门了。
那只怒火万丈的褐色羊羔就拴在门口。一看到有人靠近,它立刻后退三步,两只前蹄用力抵住地面,做出要拼命的架势,并偏过头来紧盯对方膝盖以下的某个部位。我走过去扯住它细细的小蹄子一把拽过来,抚摸它柔软的脑门和粉红的嘴唇。它拼命挣扎,但无可奈何。
我搂着羊羔向远处张望,一行大雁正缓慢而浩荡地经过天空。等这行雁阵完全飞过后,天空一片空白,饥渴不已。
很快又有两只鹤平静而悠扬地盘旋进入这空白之中。后来又来了三只。共五只,经久不去。
我早就知道可可要离开的事情,他的妻子再过两个月就要分娩。去年初冬,当南下的羊群经过乌伦古河南岸的春秋定居点阿克哈拉时,这夫妻俩就停留下来,没有继续深入艰苦的冬牧场。今年春天羊群北上时,可可才暂时离开妻子,帮着家人把羊群赶往额尔齐斯河北岸的春牧场。这次前来代替可可放羊的是斯马胡力,可可的弟弟,扎克拜妈妈的第四个孩子,刚满二十岁。这个夏天里,作为这个家庭里的唯一男性,他将成为我们的顶梁柱。这小子一到家,和客人寒暄了两句,就赶紧掏出随身带的旧皮鞋换下脚上的新皮鞋,然后坐在门口不胜爱怜地大打鞋油,忙个不停。
我很喜欢可可,他害羞而漂亮,脸膛黑黑的,又瘦又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我在荒野里迷了路,已经独自转了半天。当我爬到附近最高的山顶上,远远的,一眼看到对面山梁上骑着马的可可时,一阵狂喜。我拼命挥手,大声呼喊,激动得不得了。但心里又隐隐害怕,毕竟这荒山野岭的……其实可可是善良的,他永远不会伤害别人。这片空旷无物的荒野本身就充满了安全感,生存在这里的牧人都有着明亮的眼睛和从容的心。
后来才知道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很多年的冬天里,可可常去我家杂货店里买东西。他能记得我,我却总是糊里糊涂的。而就在这次见面前不久,我还去了他位于阿克哈拉定居点的家中拜访他和他的父亲沙阿,当时还和他面对面坐着喝茶,说了半天话。
——可那会儿,我却冲上山梁,笔直冲向他,大喊:“老乡!请问这条路去往可可的房子吗?老乡!请问你认识可可吗?”……
至于前来的二姐夫马吾列一家,他们开着一个流动的小杂货店,已经在额尔齐斯河北岸驻扎了快一个月,这次是来送面粉并道别的。三天后,他家杂货店就要出发进入夏牧场了。我们则还要再等一个月才走。
马吾列姐夫人高马大,头发刚硬,面无表情。家里两个孩子都长得像他,有事没事统统吊着脸。
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马吾列一家才起身告辞。莎勒玛罕姐姐用大衣把三岁半的玛妮拉裹得刀枪不入,稳稳当当架在摩托车上,再把一岁半的小女儿阿依地旦紧紧掖在怀里。在我们的注视下,一家人一辆车绝尘而去。
斯马胡力也是骑摩托车来的,从阿克哈拉过来得穿过阿尔泰前山一带的大片戈壁荒野,再经过县城进入吉尔阿特连绵的丘陵地带。我也曾坐摩托车走过那条荒野中的路,八个多小时,迷了两次路,顶着大风,被吹得龇牙咧嘴。到地方后,门牙被风沙吹得黑乎乎的,板结着厚厚的泥土,刘海像打了半瓶啫喱一样硬如钢丝。
此时,可可也将沿那条路离去,把摩托车再骑回阿克哈拉。
我们站在门口,看着他骑着摩托车绕过毡房,冲向坡底,经过溪水时溅起老高的水花。很快,一人一骑消失在北面的山谷尽头,只剩摩托引擎声在空谷间回荡。
客人散尽的吉尔阿特,寂静得就像阿姆斯特朗到来之前的月球表面。当然,客人还在的时候也没有掀起过什么喧哗。
自那天起,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再没见过其他人了。直到一天清晨,一支搬迁的驼队远远经过山脚下的土路。
我和卡西站在毡房门口看了半天。一共三匹马,三峰负重的骆驼,一架婴儿摇篮和一只狗。羊也不多,大大小小百十只。看来是一个刚分出大家庭不久的小家户。
早在前天,斯马胡力放羊回来,在晚餐桌边就告诉了我们:南面牧场的某某家快要转移牧场了。于是这两天扎克拜妈妈一直等着他们经过,还为之准备了一点点儿酸奶。
春牧场上母牛产奶量低,又刚接了春犊,几乎没什么奶水可供人食用。其实从冬天以来,扎克拜妈妈家就很少喝奶茶了。平时我们只喝茯砖煮的黑茶,只在茶里放一点儿盐。也没有黄油了,只有白油(用绵羊尾巴上的肥肉提炼出来的凝固油脂)可供抹在馕块(干面包,我们的日常主食)上或泡进茶里食用。难得某一天能往黑茶里加一点点儿牛奶。尽管这样,妈妈还是想法子省出了一些做成了全脂酸奶。
那天,看到驼队刚出现在南面山谷口,妈妈就转身回毡房。她解下头上绿底紫花的棉线头巾重新扎了一遍,换上一件干净体面的外套,再拧下暖水瓶的塑料盖,从查巴(发酵酸奶的帆布袋)里小心地倒出了大半盖子酸奶,然后端着出门走下山坡,远远前去迎接。
我们一直站在门口看着,看到队伍缓缓停下来。马背上的人接过妈妈递上的酸奶,喝几口再递还给妈妈,妈妈又将它送向另一匹马上的人。这个暖水瓶盖子在马背上的三个人之间传来传去,直到喝空为止。寒暄了几句,他们就继续打马前进。妈妈也持着空盖子往回走。但她走到半坡上又站住,转身目送队伍远去,直到完全消失在土路拐弯处的山背后。
给路过自家门口的搬迁驼队准备酸奶,是哈萨克牧民的传统礼性。黏糊糊的酸奶是牛奶的华美蜕变,又解渴又能充饥。对于辛苦行进在转场途中的人们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妈妈回来后对我们说:“我们也快要搬啦,吉尔阿特,哎——吉尔阿特!”
我问卡西:“我们下一个牧场在哪里?”
“塔门尔图。”
“远吗?”
“很近,骑马一天的时间。”
“那里人多吗?”
“多!”她掰着指头列举,“有爷爷家,还有努尔兰家……还有……”
又想了半天,却说:“没了!”
我一听,总共就两家邻居嘛。不过总算比吉尔阿特强些,吉尔阿特只有阿勒玛罕一家邻居,之间还隔了一座小山。
又高兴地问:“我们会在那里住多久呢?”
“十天。”
我气馁。
“多住几天不行吗?”
“那里羊多,草不好。”
我心想:那不就和现在的吉尔阿特一样吗?何必再搬?
尽管如此,还是非常向往。
在吉尔阿特的生活,寂静得如漂流在大海上。海天一色,四面茫茫。
但有一天,喝上午的第二遍茶的时候,山谷里突然回响起摩托车的声音,于是漂流在茫茫大海中的我们总算发现了一点点儿岛屿的影子。大家赶紧一起跑出去。果然,看到两辆摩托车在荒野中远远过来了。我们注视着他们来到山脚下,熄了火,把车停放在水流对面,然后两人一起向坡上走来。
妈妈说:“是汉族,收山羊绒的。”
我们家有二三十只山羊,这个季节刚刚梳完羊绒,用一个装过面粉的口袋装着,有大半袋呢。上次马吾列姐夫来的时候,拼命往袋子上浇热茶,希望它能吸收潮气变得沉重一些。妈妈大声呵斥他,但并没有真正地阻止。
但是这天这笔生意没做成,价钱始终谈不拢。两个汉族人茶也没喝就走了。我们又站在老地方目送他们离去。妈妈说:“羊绒、羊毛,越来越便宜了!油啊面粉啊,越来越贵!”
但我觉得哪怕羊绒真的越来越便宜了,那些深入荒野做这种生意的人仍然很辛苦。何况他们大约还不知道绒上浇过水。
(嗯,后来,这袋山羊绒到底还是卖给干坏事的马吾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