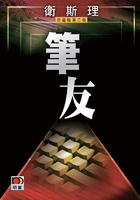七岁时,爷爷说:“再不能耍了,再耍就耍野了。”于是他牵着我的手,像牵狗一样把我牵到了学校。
我们的学校在村子的南边,是一座由旧戏楼改造而成的简易教室,戏楼中间隔了一堵泥墙,一边是一年级,一边是二年级,靠戏楼边上分出的一角支着一张破旧的木桌,就算是老师临时的办公地点了。戏楼前面是一片空地,空地旁边是一条水渠,过了水渠,就是我们村里唯一一条横贯南北的土路了。
我的启蒙老师姓谢,叫谢四光,是从邻村谢家圪崂聘过来的民办教师,个子很大,一口烟牙。他是那种头顶长得很尖的人,因而总感觉他戴的帽子一个劲地往周围塌,尤其是后脑勺那里,塌得尤其厉害,就像是谁故意在那里压了一把一样。谢老师那时大约五十岁左右的样子,嘴里叼着根旱烟棒,正在靠近门口的铁炉子上熬中药。我和爷爷进去时,教室里已弥漫了一层很浓的旱烟味和中草药味。
谢老师抬起头,和我爷爷打招呼:“老人家,你咋来了?”
他把我爷爷叫老人家。
爷爷说:“给我孙子报个名,到上学的年龄了。”
谢老师说:“还早着呢,你让娃娃先耍两年嘛。”
爷爷说:“再不能叫耍了,再耍就耍野了。这跟调牲口一样,一生牙就要调,等牙长满再调就调不住了。”
谢老师便对着爷爷伸了一下大拇指:“你老人家还是明事理,娃上学就是不能年龄太大,太大了难开窍。我原先说,娃上学的年龄七八岁正好,可你们村里人犟,说七八岁懂个啥,连尿都不会尿。可结果呢?十一二岁才领过来,一个比一个猪。”
爷爷便得意地捋着胡子笑了。
报完名,领了课本,谢老师便让我坐到前排的一个座位上。所谓座位,就是些土台子,两边用砖头支着,顺砖墙横搭一条长长的木板,高的是桌子,低的便是凳子。教室里一共有三排这样的座位。一排坐四个学生,三排便是十二个学生了。后排的学生大,占地方,谢老师便让我坐在了紧靠讲台的第一排。
看着爷爷慢慢走出教室,走上土路,我趴在木板上差点就掉下泪来。
谢老师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学生了,学生可不能像放羊娃,放羊娃没纪律,学生得有纪律。记下了吗?”
我茫然地点点头,感觉脑子一片空白。
我注意到,教室里的学生,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不管认不认识,他们的年龄似乎都比我大。而且我还注意到,最后边坐着的那个大个子,上嘴唇都有一层淡淡的黑毛了。后来得知,这个学生姓王,家在西洼王家,他的年龄竟然比我大六岁半。
戏楼角子上挂着半页生锈的铁铧,“当当当,当当当……”快急地敲时,是上课;“当当,当当……”缓慢一些敲时,是下课。
第一堂课我听得云里雾里。
好不容易挨到下课,尿却憋得厉害,正在地上打转,那个嘴唇上长了一层黑毛的同学走过来问:“是不是尿胀了?”我点点头。“黑毛”说:“跟我来。”朝旁边的同学挤挤眼。我那时竟没有识破他的诡计。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随。走到教室后面用两堵墙隔出来的厕所旁边,他站住了。两堵墙上都用白灰写着字,可我不认识。“黑毛”指指右边的那个说:“就那里,你进去吧,我在外面等你。”我急失慌忙进去,连看都没看就解开了裤带。这时听见拐角上“哇”地叫了一声,紧接着一个脸蛋红红的女生提着裤子跑了出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惴惴地尿完,惴惴地走出厕所,这时就见两个班级的同学都围过来看,边看边喊:“流氓,流氓。”我哪里见过这阵势,当时就吓得哇哇大哭起来。哭了几声,“黑毛”分开众人走过来,蹲下身子笑笑地盯着我的脸说:“别哭别哭,进了一趟女厕所有啥哭的。”随后,他又对我循循诱道:“是这样,你给大家说说,你究竟看见了什么,你要是说了,咱们就当啥也没有发生,你要是不说,我就让他们天天喊你流氓。”我说:“我尿憋,我啥也没看见。”“黑毛”说:“还嘴犟,人家谢红都哭着告老师了,还说没看见。”停停又说:“你给大家说说,多大,啥样子。”后面立即响起一片哄笑之声。我说:“啥多大?啥啥样子?”“黑毛”说:“你说啥多大,啥啥样子?”说着嘿嘿坏笑了两声,然后把地上的一片破瓦放肆地搁到我头顶上:“说不说?不说我就让大家喊你流氓了。”见我不说,他就朝后面挤了挤眼,这时大家像有人指挥了一样齐声喊道:“流氓,流氓……”
那天算是我此生最难熬的一天了。
也就是在那一天,我首先记住了这个嘴唇上长一层淡淡黑毛的同学的名字:王明山。
放学以后,我第一个冲出教室,头也不回地往家里跑。刚过水渠,就听见后面几个跟我一般大的孩子撵着喊:“流氓,流氓……”
我飞也似的逃回了家。
从那天起,我一连三天都没敢到学校。第三天中午,我刚从野地里溜进家门,就听见谢老师正和我爷爷在上房里说话。
谢老师说:“老人家,你那个孙子就来了一天,这几天连他的帽个子(意为头发)都没见。”
爷爷说:“你可能没注意,他去学校了,我早上把他送到大路上才回来。”
谢老师笑着说:“统共只有十来个学生嘛,我咋能注意不到?他可能看你回去了,就跑到野地里耍去了。是这,老人家,你明天费点心,一直把他送到教室门口再回去,我看他还能往哪搭跑。”大约是见我爷爷生了气,谢老师又缓和了语气说:“是这,老人家,你不要打他,也不要骂他,好话给他安顿,娃娃嘛。”
这天晚上,爷爷确实没有打我,也没骂我,而是给我讲了许多读书成才的大道理,末了说:“娃呀,不读书不行呀,不读书你到城里连个茅房都找不见。”
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但我立即又想起了王明山和那些喊我“流氓”的同学。
我说:“爷爷,你就让我跟着你放羊吧,放羊又不需要认字,而且山上又没有茅房。”
爷爷说:“娃呀,太多的道理我说不出来,就是说出来了你也听不懂,总而言之,你现在要上学认字呢,认的字多了,你就明白了。”
第二天早上,爷爷早早地起来给我装书、装馍馍,看他的架势,今天他是非要把我送到教室里去不可了。
走上大路,我对爷爷说:“爷爷,你回去吧,我认得路。”爷爷说:“你走你的,你不要管我。”见爷爷一副倔犟的样子,我心里彻底绝望了。我在前边走,爷爷在后边跟。走到操场那儿时,爷爷说:“我在这儿看着,你进去,你进去爷爷就回去了。”我低着头往前面走,走到戏楼口上时,才发现原来那里有个拐角,拐角上正好有个旯旮,我赶忙侧身进去,半个墙角正好隐住我的身子。藏了一会儿,我估计爷爷已经走远了,就赶忙探身出来,刚要脱身,爷爷却已到了我的眼前。爷爷这回是真生气了,他愤怒地举起拐棍,一边朝我屁股上打,一边骂:“你个没起色的货,我让你躲,我让你躲。”接连在我屁股上打了四五棍。
正在打,谢老师却已走出了教室。谢老师一把抓住爷爷的拐棍,笑着说:“老人家,这就对了,娃娃不能太惯,惯得太劲大就上头了。”爷爷说:“谢老师,今天我把狗日的就交给你了,这碎狗日的要是再不听话还跑,你就狠狠地打,就是打断了腿我也不埋怨你一声。”谢老师笑着说:“老人家,我知道,你先回去吧。”
爷爷回去后,谢老师就把我领进教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谢老师像戏台上的老爷过堂一样开始了对我的询问:“那谁谁谁,你给我说,你为啥不来学校上学,是学校不好吗?是老师不好吗?要不就是你人大心大,一个小小的教室装不下个你了?”见我一个劲儿地抹眼泪,谢老师又说:“如果这几样子都不是的话,那一定就是哪个坏蛋欺负你了,说,是哪个?”说到“哪个”时,谢老师陡然提高了声调,同时目光凌厉地在教室里逡巡了一圈,吓得同学们都迅速低下了头,仿佛一些怕见光的虫子一样。这时我偷偷瞄了王明山一眼,发现他脸色煞白,神色慌乱,头似乎要低到了裤裆里。谢老师继续说:“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大的欺负小的,强的欺负弱的,坏的欺负好的,如果我以后发现谁是这样的话,我就把他的头拧下来当尿罐子用。”训了几句,谢老师就把我领到座位上,“你在前面旷了几天课,老师可以原谅你,毛主席都说了嘛,要允许同学们犯错误,只要把错误改了,还是好同学。不过老师把丑话说在前头,下不为例,下次要是还无故旷课的话,老师可就真生气了。”
这天早上,我一直坐在教室里认真听讲,心里再没有了害怕的意思。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去撒尿,我也跟着去撒。我故意把尿撒得高高的,看他们的反应,他们一个个都低着头,半侧身子,同时以躲闪或掩饰的方式逃避着与我的目光的不期而遇。当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同学步调一致地喊我“流氓”了。
放学后,王明山加紧步子追上了我,说:“好样的,你今天没有当堂告老师,算你娃娃识相,以后你得听我的,要是不听我的话,我还有可能让大家喊你别的。”
我迅速调回头往教室里走。
王明山说:“干啥去?”
我说:“告老师去。老师说了,谁要是欺负小同学,他就把谁的头拧下来当尿罐子用。”
王明山赶忙挡到我前面,神色明显地有些慌乱了:“我是跟你说着耍呢,这娃咋还不识耍。”
我说:“谁跟你耍?”
见我语气强硬,王明山明显地软下来了,他不但对我不再蛮横,且把一只黑乎乎的手讨好地搭在了我的脖子上。我一扭脖子,态度绝决地甩掉了那只黑乎乎的手。
王明山神色有些茫然地转身走了。
正式上课以后,我对谢老师的好感与日俱增,不但恐惧感消失,而且对他的一举一动充满了好奇,产生了兴趣,好像他天生就是我的老师似的。
“当当当,当当当……”伴随着急促的上课钟声,谢老师昂首走进教室,把课本、教鞭,和半盒粉笔放到讲桌上。“同学们,前几天有个同学因故没来上课,我们等了他几天,现在这个同学来了,我们就开始正式上课,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一页。”谢老师说完,随手拿起旁边的课本。课本第一页上写着指头蛋大的三行黑字: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我们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谢老师把那三行字一笔一画写在一个用木架子支起的黑板上,然后回过身抓起那根用竹杆做成的教鞭,说:“同学们,大家跟着我读,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之后教室里便响起了那种震耳欲聋的诵读声,喊口号一样。在读的过程中,谢老师会把教鞭放在字的下面,读一个字,点一下,点一下,又读一声,这就使得教室里不时响起那种竹节敲打黑板发出的“笃笃”声。
读过数遍之后,谢老师就歇下来,他拍打拍打手上的粉笔末,把教鞭往桌子上一放,说:“现在你们自己读,我抽一棒旱烟。”
见我们都读起来,谢老师就慢慢地踱着步子,慢慢地卷旱烟。烟卷好后,走到戏楼角子上的那个铁炉子前,掀起炉盖,“轰”一下用纸条引出一团火来,然后偏过头对着火团点烟。吸了几口,坐了一会儿,谢老师又走到铁炉子前面。这时他顺手揭开炉子上熬药的药罐子,用一根竹棍搅一搅,药罐子里立即腾起篮球大的一团白汽来。白汽一腾,教室里就弥漫了那种浓浓的中草药味,格外香,格外醒鼻,这使正在大声朗读的我们不禁起了一阵轻轻的骚动。
早上课罢,爷爷早早地等在水渠那儿。他双手拄着拐棍,两眼不眨地朝着戏楼口张望,见我蹦蹦跳跳出来,他的脸上明显地绽开了笑容,像看到庄稼地里的好收成一样。爷爷拖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问:“早上上的啥课?听得懂听不懂?”我说:“认了几个字,都是些大白话。”听我叙述完内容,爷爷心有不甘,说:“你给我念一念,念一念。”我便大声地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我们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惊得在路边觅食的几只麻雀“啾啾”乱飞。爷爷捋着雪白的胡子,哈哈地笑了。
晚上睡觉时,爷爷说:“这是你上学的第一课,一定要上扎实,是这,我给你盯着,你再念一遍。”我说,“就那么几个字嘛,我都烂到肚子里了。”爷爷说,“小心没大岔,你不要怕麻烦。”爷爷掏出课本,指着上边的字说:“念。”我懒洋洋地念了一遍。爷爷说:“还有一种念法,不知你会不会?”他拿着烟锅,打乱了字的顺序,突然指着其中的一个字说:“念。”这往往要我考虑半天。尤其指到“共产党”的“党”字时,我要费半天工夫才能想起。就这样,我和爷爷折腾了半夜,直到我精疲力竭方才罢手。
上第二堂课时,谢老师照例拿着课本、教鞭,还有半盒子粉笔。他迅速地把昨天学过的那三行字写在黑板上,说:“今天上课之前,我们先温习一下昨天认过的生字,看你们记下了没有。”说完,顺手拿起桌边的那根竹杆教鞭。他从课本里抽出班级花名册,说:“下面我要点名了,我点到谁,谁要喊一声到,到字喊完,你就给我往下念黑板上的字。”
第一遍是按照顺序念,全班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念下来了;第二遍却是打乱顺序念,他拿着教鞭,就像昨天晚上爷爷的旱烟锅一样,东点一下,西点一下,点来点去,点得局面大乱,事先没有准备的同学不禁暗暗叫苦。这天早上,除我之外,班里其余的十二个同学几乎都没有顺利地认全生字。
临下课时,谢老师站在讲台上作总结性发言:“今天我算看出来了,我们全班十三个同学,有些长的是玻璃脑子,有些长的是猪脑子,有些还长的是石头脑子。有些人,你不要看他长得人高马大,胡子都黑茬茬的了,可智力还不如人家一个七岁的娃娃,啥原因嘛,啊?”
谢老师将这段话翻来覆去讲了大概有三遍。
下课之后,我发现王明山一直都躲避着我的目光,偶一相遇,也是迅速分开,就像有人用火悄悄烫了一下一样。
认字结束以后,就该到写字了。写字仍然写的是那几个字。上课以后,谢老师就让大家拿出作业本和铅笔,他在黑板上写,我们在底下学,他写一笔,回头招呼我们写一笔,一个字写完了,他就让我们连起来完整地写。我们写的时候,他走下讲台,一边前前后后巡视,一边就纠正着某个同学的某一种错误。如果哪个同学实在写不好,写不对,他就站在这个同学的背后,用手握住这个同学的小手,一横一竖,一撇一捺,直到这个同学写会为止。一般来说,大家都是不愿意让谢老师握手的,因为谢老师在握住你的小手的同时,他那浓烈呛人的旱烟味也会从身后忽忽而来。
看看大家都写得差不多了,谢老师就啪啪地拍着手上的粉笔末子,说:“今天就学到这儿吧,现在大家把书装上,把碳棒拿出来,到操场上去,一人占一块地方,一个字写20遍。”说完,就又到戏楼拐角子上抽旱烟或熬中药去了。
到了操场上,大家就呼啦一下散开来,就像古代的跑马圈地一样,大家迅速掏出碳棒,低下头,佝倒身子,然后用碳棒方方正正画出一块地来。这块地就是我们今天的作业。我们在操场上用碳棒画生字,谢老师则优哉游哉地坐在门口的木凳上,抽烟,想事情。我们那时的教室是个临时的简易教室,一边是一年级,一边是二年级,一边说话时另一边听得真真切切;一年级上语文课时,二年级上数学,反之亦然。由于两边互相串音,于是就有了一班上课,一班在操场上写生字这样的情形了。又由于教室在村子边上,靠近大路,且四周没有围墙,因而便经常有闲来无事的村民们在劳动之余蹲在水渠上看我们写生字,一边看一边在旁边品评。
“这个娃灵醒,教下的字一遍就会,随了人家先人了。”
“这个娃也不错,虽说字写的像狗牙一样,但细看笔画还对着呢。”
最后一个则就有些不客气了,“这是斜眼子老四家的娃吧,这个娃笨呀,跟他老子一样,一个毛主席的毛字写了半天最后那个一弯就是弯不过来嘛。”
之后便是一片哗笑之声。
每到这时,谢老师就慢慢地踱过来,一边和他们搭讪,一边就参与或纠正着他们的品评,于是,一个孩子的学习优劣就在他们这样光天化日之下的评说中分野出来了。
当然,每到这时,便是我最为得意也最为陶醉的时候了。
谢老师教学的特点在第一节课还看不出来,到第二节课时就显露无遗了。第一节课是教生字,老师教,学生写,谁都一样,再笨的人也会装得过去;可第二节课就不一样了。第二节课是写生字,是检验第一节课教学成果的时候。这时教室里就会充满了一股浓浓的肃杀之气,大家都屏住呼吸,眼睛盯着门口,连最顽皮的学生都不敢咳嗽一声。
谢老师进来后,把教本放在旁边,然后把一根长粉笔折成若干个小段,糖果一样摆开在桌边,说:“这堂课咱们温习上节课教的生字,我叫到谁,谁就到黑板前面来写,我说写啥字就写啥字。”
这就是有名的“考生字”了。
同学们被依次一个个叫上了讲台。
谢老师说:“大家先写一个毛主席的毛。”大家就用粉笔写一个“毛”字。
谢老师说:“大家再写一个毛主席的主。”大家就用粉笔写一个“主”字。
写过两个字后,谢老师会突然停顿下来,然后打乱句子的顺序,就像“认字”的时候一样,会“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那样从中间点出一个字来。如“共产党”的“党”字,“万岁”的“岁”字,只要这样一乱点,肯定就有许多同学写不下来了。
而在这些写不下来的同学中,每次肯定都有一个王明山。
王明山和那些写错字的同学在讲台边站成一溜摆。
谢老师背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指头乱点着训他们:“你亏了你们先人了,亏了你们大了,你们大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一天一褡子的给你背馍,为的是啥?啊?”
又骂:“你们这是偷的馍馍门背后吃呢,是自哄自呢。”
接着骂:“你们这样下去,我看和你们先人一样,还不是个戳牛尻子的货。”
被骂的同学像经了浓霜的菜头一样一个个低下了头。
谢老师骂一句,想一句,想半天,又骂一句,中间停顿的间歇很大。有时我们以为他骂完了,骂累了,没想不一会儿又接上了。他骂的时候,往往会把一些旱烟味很浓的唾沫星子喷溅到对方脸上,让对方有种双重受辱的不堪之感。
第二节的“考生字”课,往往就是在这种漫天的咒骂声中悄然过去了。
也就在这时,许多人都感觉日子无端地漫长起来。
谢老师尽管很“凶”,但对我却是最好的。我那时因为生性腼腆,又格外胆小,生怕一不小心“先人”受辱,便对写字格外用心。再加上爷爷睡觉前的悉心教导,渐渐地,我就成为谢老师课堂上的“红人”了。
谢老师常常表扬我。
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这样说:“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们。”
这时我往往就能感受到从王明山那儿传递过来的绝望的目光。
有一段时间,谢老师会把我悄悄叫到一边,低下头悉心叮嘱道:“这个写字是很重要的,不管你以后干啥,只要想干大、干好,字写得不好是万万不行的。”
又说:“人生识字糊涂始,字认得多了以后,人自然就不糊涂了。”
这期间还发生过许多故事,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的突然“蹿红”,爷爷便格外高兴起来。爷爷拄着拐棍,背着另一只手,有事没事就到我们学校附近转悠。一边走,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戏楼。见谢老师从戏楼里出来,他就步幅很大地迎上去,并迅速把玛瑙嘴子的烟锅掏出来,装上旱烟,双手递上。
谢老师点上火,“吧嗒”吸一口烟:“老人家,你这个孙子长大肯定是个有出息的,这个娃要是没出息,你把我的头割下来当尿罐子用。”
我爷爷便捋着胡子哈哈笑了。
一年之后,我们的学校就搬到村后的塬上了。塬上有一座古城,古城里有四四方方的城墙和五颜六色的庄稼地,在那里,我度过了自己童年中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
又一年后,谢老师竟被“精简”回家了。
得到消息的第二天,爷爷特地请谢老师在家里吃了一顿葱花面。吃着面,爷爷小心翼翼地问:“啥原因嘛?你又没犯错误。”
谢老师说:“是嫌咱们年龄大了,知识老化了。”
爷爷说:“这不是卸磨杀驴吗?知识还有老的、新的?把娃管住就成了嘛。”谢老师淡淡一笑,“这你老人家就不懂了,现在是知识年代,知识年代就要由有知识的人来管,咱也不能耽误人家娃娃——误人子弟,如杀人父兄也。再说了,我回去也还能劳动,横竖是挣工分嘛,到哪里都一样。”
谢老师说着,眼里竟汪了满满两包泪。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谢老师的面。
只是偶尔地,听赶集回来的爷爷说:“又碰见你们的谢老师了,谢老师还夸你呢,说你是个有出息的,说你要是没出息,他就把自己的头拧下来当尿罐子用。”这样说时,爷爷照例会哈哈大笑,笑过之后却又跟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我上大学那年,爷爷已经去世了。上学前夕,我特地去爷爷的坟头烧了一回纸,意在告慰爷爷在天之灵。奠完酒,磕罢头,正要扶膝站起时,忽然发现爷爷的坟头竟长了许多打碗碗花,一簇一簇,粉嘟嘟的,像一些小巧而精致的酒盅。
那天我一直坐到夜色罩住了爷爷的坟头。
进校之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给远在数百里之外的谢老师写信,信的内容业已忘记,只记得写了喜悦,写了艰辛,也写了十年寒窗苦读中对他的默默感念。那封信写得很长,很抒情,写着写着,竟把自己也搞得几欲落泪。信寄出去后,我隔几天就到班级的邮箱察看,却始终没有收到过谢老师对我的只言片语。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镇上工作。周末或节假日,我常常骑着自行车回家,就像当年在镇子里上学一样。这样,我便经常会碰到一些十几年未见的同学,这让我有了一个难得的旧梦重温的机会。渐渐得知,我小学时的那些同学,除几个在附近做点小本生意外,其他人基本上都在家务农。
也碰到了同学王明山。他那时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个子更高,更大,胡须也更其浓密,见了面,竟有些久别重逢的激动。
“谢老师说的没错,你到底是个有出息的。”王明山说,说时使劲摇着我的手。
我笑着说:“咱俩差不多,我不还是在咱这搭转?”
王明山说:“那可不一样,我戳牛尻子着呢,你却在凉房房里坐着呢。”
我顿时就有了些忐忑不安的感觉。
说起小时候上学的事,王明山竟还幽默了一把:“你那时把我们害惨了,害得我们天天都挨谢老师的骂,骂来骂去,就把我们骂到牛尻子后头了。”
我笑道,“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啊。”
问起谢老师的情况,王明山轻轻一叹,“日子过得还凑合,就是经常有病,好像是肺上的。”之后又说了些家长里短的客套话。
目送王明山远去,我心里竟泛上来一种说不出味道的酸涩,心想,哪天一定要抽空到村里去看一回谢老师。
这样想过不久,我就由乡里调到了城里,再辗转由市里调到区上。关于要看望谢老师的那个念想,终于在世俗的纠缠打磨中日渐淡去了。
一晃又是十余年。
今年春天,我正在老家盖房子,中间歇晌时,母亲突然进来说,“谢老师在咱们家门外站着,他说他要看看你。”我心头一紧,顺手拿了一盒烟,一溜小跑着出去。远远地,我就看到多年未见的谢老师了。谢老师仍戴着深蓝色的帽子,帽子四周向下塌着,蓝制服,蓝裤子,只是上衣和裤子都洗得有些发白了。他的身材依然高大,背略微有些佝偻,下巴上突兀地留出一撮花白的胡子。见我出来,他脸上立即露出了我所熟悉的那种笑容。这时我才发现,他满嘴的烟牙,竟已所剩无几了。
我赶忙上去抓住他的手,并立即拆开拿在手里的那盒烟,“谢老师,多年没见,你还好吧?”
“好,好。”他接过烟,慢慢点上,慢慢吸着,然后像打量一个陌生人那样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我只是路过这儿,听说你给家里盖房,就想过来看看,好,好。”说着,转过身就要离开。
我似乎有许多话要对他说,便用劲拉住他的胳膊,要他到屋里坐坐,喝口水。
他却扬了扬手里的木棒,“还有半截子路呢,你忙着,我回去了。”说完,他竟执拗地转过身去。这时我才意识到,原来他手里的那根木棒,是拿来当拐杖用的。
我急忙赶上一步,将那盒刚刚拆封的烟装进他的上衣口袋。
他慢慢地走着。
竟再也没有转身。
许久许久,我感觉有一种热辣辣的东西,竟一下子盈满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