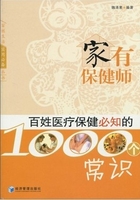一时间,我甚至有点嫉妒他。我多希望他能比现在年长十岁,或者是十二岁,而且不知为何依然单身,正想找一个合适的姑娘,带回家介绍给他温暖的家人。当然,这想法是挺傻的。不过,即便你十分热爱当前生活的其他方面,内心深处有时还是会本能地向往温暖的家庭生活,以及不会令人感到束缚的家庭纽带。
“也许下周吧。”我不该这么说的。不应该让他抱有希望。
“好的,”他有些迟疑地站在门口,似乎还有别的什么话想说,“好吧,不管怎么样,祝你周末愉快,周一见。”
“周一见,安德鲁。谢谢你带我适应新环境。我非常感激。”
“小意思,随时乐意效劳。没的说。”如果这孩子真想在这行得到认真对待,那就必须学会戒除使用“好的”“没的说”这一类的用词。愿上帝保佑他那脆弱的小心脏。
他走之后,我一时难以决定,是要继续搜索相关信息,还是收拾好资料,把工作带回家去。至少在自己家里,当我再次翻开《守护故事的人》时,不用再担心会被别人看见。
地板清扫机运作的声响从走廊那头的某个地方传来,正好帮我做了决定。随着毛刷高速旋转,传动带不时发出拉长的尖啸声。也许是《守护故事的人》令我产生了这种联想,我觉得这声音听来像是一头小猪的号哭,它的脚被人抓住,无情地从它妈妈身边拖走,成为任人宰割的乳猪肉。
我把所有东西都收进拉杆公文包里,因为周末要用的文件比较多,我特意把它带了过来。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最后一次认真考虑把违禁书稿带回家去的风险。
你可以现在溜过去,把东西还回废稿堆里,所有人几乎都已经走了……
可我知道自己不会这么做。还没等我打开抽屉,把信封从里面拿出来,我的心思便已经飞进了萨拉和兰德的世界里。我走进蓝岭山脉里——不是游客所钟爱的观光景点,而是灰蒙蒙的土路,与世隔绝的小村落,以及幽闭的山谷,那些地方在二十世纪初,也就是兰德·查普林造访时,还没能沐浴到文明的曙光,而且有些地方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我往外走去,从罗素和大型地板抛光机旁边走过。他已经停下机器,正在查看防护罩底下的状况。
“应该是皮带松了。”我说。
罗素抬起头,吃了一惊,“嗯,我想也是。”他顿了一下,直直地看了我一会儿,“今天回去得挺早啊?”
“嗯,没错。”我很好奇,除了乔治·蔚达,或者米琪以外,还有谁会注意到,我不是今晚最后一个离开编辑部大厅的人。鉴于上午会议上的失误,继续坚守工作岗位其实才是较为明智的选择,然而此时此刻,我压根没有心思去打安全牌,“我有点事情要回去处理。”
房间里灰朦昏暗,除了睡在临时狗窝的“星期五”所发出的呼噜声,一点别的动静也没有。“星期五”是我和布莱恩交往阶段的遗留产物。我们在吃完晚餐走路回家的路上,在一个垃圾桶里发现了它,一只又瘦又脏的混种吉娃娃,仍然对人怀有戒心。
是布莱恩提出把它带回我的公寓先养一两周,他还张贴启示,以防有人正在找它。布莱恩的生长环境优越,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有时过于天真。他万万不会想到,有人会故意抛弃一只活生生的小动物。
“你应该把它带回你住的地方去,”我们站在巷子口讨论下一步的安排时,我对他的意见提出了抗议,“比较而言,它更喜欢你一些。”
“嗯,这一点倒是相当明显。”布莱恩十分戒备地搂住小家伙的脖子。它的耳朵被压得紧贴脑袋,眼睛突出来,露出尖利的牙齿,看起来就像是某种外星生物,“可是我没时间照顾小狗,简。”
“难道我就有时间吗?”有些时候,布莱恩会忘记我们同在一家公司工作这个事实。他在发行部,我在编辑部,都是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职务。我们已经暗中交往了一年半,其间总是分分合合——暗中进行是因为公司有禁止办公室恋情的规定,而分分合合的原因,则是我们似乎都不确定,这段感情是否能够走下去,或者究竟能走多远。
小狗拼命晃动脑袋,小小的身躯大张着嘴巴,做出虚张声势的模样。我不由自主地,笑了出来。“幸好这小家伙不是条斗牛犬。”
同以往一样,我们的争执最终以我的屈服落下帷幕。布莱恩设法使它平静了下来,一人一狗脸贴着脸,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叫我如何能够说不。“好吧,不过我最多只能留它到下个星期五。”
谁知下个星期五逐渐演变成了三年。我和他终于正式分手,生活也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故。结果我养这条狗的时间反而超过了我们的感情以及上一份工作持续的时间。
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把“星期五”送走。或许因为在我看来,以它这样的性格和长相,很难再找到一个肯收留它的地方。或许只是因为,养它并不需要太费心思,而且它从不乱咬屋里的东西。反正这房子平时也没有别人在用,而且只需要几美元,就能让住在走道尽头那家的小孩带它出去散步。她们由单亲妈妈一人抚养,需要一点额外收入。
它打了个哈欠,转过视线看向我这边。我把公文包挨在主要充当书桌的两人用餐桌旁放好,将其他东西都搁在厨房操作台上,这里大部分时间也被我当成桌子来用。
“今天有没有在公园里教训别的小狗呀?”“星期五”因为常冲比它大好几倍的动物大吼大叫,在这一带颇负盛名,帮我遛狗的小女孩都觉得十分有趣。
它站起来,一条一条地伸展自己的小短腿,然后原地转圈嗅探了一阵,又扑通一声趴下,把屁股对着我,鼻子指向充作食盘的空奶油桶。同往常一样,它的沟通能力不说老练,至少也是十分出色的。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星期五’。今天的工作还顺利吗?”
它当然没有回话,不过我用它的口吻,完成了这个对话,“嗯,还算不赖,简。我在窗台边上坐了一会儿,又到沙发上躺了一阵。我把碗里的水全喝光了,又在公园里找了几个新对手。又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了。”
它打了个哈欠,呜咽了一声,跟着打了个喷嚏,像是在说:“拜托,这也太老套了吧。来点新鲜事吧,简·吉布斯。”
通常而言,如果要养一条狗,它至少得会摇尾巴或者用别的什么方式示好,不过对于“星期五”,我只能发动自己的想象力了。“我吗?多谢你的关心。今天还挺有意思的。有好有坏。我在部门会议上出错了,不过之后又发生了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实际上,几乎可以称得上诡异了。你觉得这东西像什么?”
我俯身拉开公文包的前袋拉链,把那个旧信封从里面取了出来,“它莫名其妙地就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了。我今天一大早过去就看见它了。而且,根据邮戳日期推断,它唯一可能的出处就只有……废稿堆了。”
我看向那边时,“星期五”正坐在它的床上,注视着我。接着,它把视线慢慢移开,停在了我肩膀上方的位置,好像看见了什么似的。接着,它又突然吠叫了一声,我立马感觉到全身发凉。
难道这里还有别人?我转过身,仔细打量这个开放式的房间。什么人也没有,也没有别的异常情况,只除了“星期五”刚才的怪异表现。
“你别这样。”我打开顶灯。灯泡闪烁起来,好像马上就会灭掉,房间里似乎也笼罩着一种似曾相识的诡异气氛。
突然之间,一切都恢复正常,灯泡亮了,“星期五”侧身趴到地上,楼下的街道传来悠长的警报声。我低头看着信封,借助头顶的荧光灯,几乎辨认出了邮戳上的其他内容。
我移到房间正中,将信封举到更为靠近光源的地方,眯着眼睛仔细查看起来。
我认出了两个字母:NC[13]。原来,这故事不只是发生在蓝岭山脉,就连书稿也是在那里写成的。北卡罗来纳州。我多年以前离开的故土。
寒意再次侵袭至我全身——混杂着恐惧、迷惑和不确定的心绪。这一切难道都是巧合?到底是谁把这信封放到我桌上的,又是出于什么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