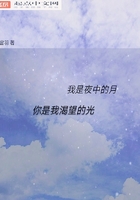“如果明天不方便的话,十六号是个大吉日,就约在十六号,你看怎么样?”
前几天幸子临出门时接到井谷的电话,无法推托,只得答应下来。然后费了整整两天的工夫,好不容易从雪子嘴里得到一句话:“那么,去见见也可以。”而且还附带一个条件,就是井谷按照原来的承诺,由她出面请双方吃顿便饭,尽量不使人产生相亲的感觉。时间定在那天下午六点钟,地点是东洋饭店。出席者请客一方是井谷老板娘及其在大阪的铁屋国分商店工作的二弟村上房次郎夫妇。——这位房次郎是男方濑越的旧友,这桩亲事就是他穿针引线的,自然是不可或缺的。——濑越这边,若只是他一人参加,未免孤单,但这种场合,又不宜特地请家乡的亲戚到场,幸好濑越一位同乡的先辈五十岚先生,在房次郎工作的国分商店任常务理事,便由房次郎邀请这位老绅士陪伴男方出席。女方这边是贞之助夫妇加上雪子三人。主客共计八人。
此前一日,幸子想要打理头发,便和雪子一起去了井谷的美容院。她只想修剪头发,便让雪子先做头发。幸子正在一边等着,井谷抽空走了过来。她弯下腰面对幸子小声说道:“有件事,我想拜托太太呢。”然后凑近幸子耳边说:“其实不说你当然也明白的,我想请太太明天尽量穿戴得素净一些。”
“好的,我知道了。”幸子回答。
井谷不容辩驳地接着说:“稍微素净一点还不行,一定要下狠心往朴素上打扮。你家小姐固然漂亮,不过,她的脸本来就瘦,又总是愁眉苦脸的,和太太站在一起,就显得逊色些个了。太太天生丽质,即使不特意化妆,也格外引人注目。所以请你明天尽可能少施脂粉,宁可打扮得看着老了十岁十五岁的,也要尽量让令妹更显得漂亮。不然的话,只因太太陪着,本来有望成功的姻缘也说不定吹了。”
井谷这种警告,幸子并非第一次听到。至今为止,她已经多次陪同雪子去相亲,经常听到有人说:“那位姐姐开朗而时尚,可妹妹看上去有点内向沉闷。”“姐姐容光焕发,光彩照人,相比之下,妹妹就黯然失色了。”甚至有人劝告:“只让本家的姐姐陪同相亲,分家的姐姐还是回避为好。”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幸子总认为那些人不会欣赏雪子这种类型的美,忍不住要为雪子辩解:“不错,也许我的相貌开朗而时尚,比较现代,但是这种外貌的人,如今到处都是,并不稀罕。赞美自己的妹妹虽然有些矫情,但要说昔日真正的千金小姐都是养在深闺的,看上去无不弱不禁风,楚楚动人,那不就是我家雪子这种美吗?只有真正懂得欣赏雪子的美,诚心诚意请求把雪子妹妹许配给他的人,才可以许婚……”
幸子虽然这样夸赞妹妹,内心仍有着难以抑制的优越感。只是在丈夫面前,她才会有些骄矜地说:“我陪雪子去相亲,反倒会妨碍她呢。”贞之助有时会说:“既然如此,我一个人陪她去好了,你还是回避吧。”有时说:“不行!这样打扮还是不行!你不打扮得再素朴一点,人家又会说你抢了妹妹的风头了。”敦促幸子注意衣着和化妆。不过幸子看得出,他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却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而沾沾自喜。
因为这事,幸子甚至有一两次没有陪雪子去。但是一般来说,都得由她代表本家大姐出面,而且雪子说,如果她不出席,就拒绝去相亲。所以,每次相亲,幸子都尽可能装扮得不那么惹眼,陪妹妹一起去。问题是,她的衣裳饰物大多很华丽,再怎么换也有限,结果相亲后还是屡屡被人说:“她那样穿戴还是不行。”
“……好的,好的,大家总是这样说,我知道了。不用多说了,我明天一定穿得朴素极了……”
休息室里只有幸子一人,谁也不会听到她们的对话。但是,与隔壁房间之间挂着的门帘此时是掀起来的,雪子就坐在那间屋子里,头上罩着个烘干筒,二人可以从她面前的镜中看见她的脸。井谷以为雪子罩着烘干筒,不会听见她们交谈,其实两人说话的情景,从雪子的角度也看得一清二楚。虽然听不见说什么,却可以看见她们俩一个人眼珠往上看,另一位则是两眼发直,幸子不禁担心起雪子会不会从她说话的口型推测出在说什么来。
这天下午从三点开始,姐妹们就给雪子梳妆打扮起来,贞之助也从事务所提早赶回,大家都聚在化妆间里,气氛颇有些紧张。贞之助对和服的花色、搭配,以及发式之类都颇有兴趣,喜欢站在一旁观赏女人们梳妆打扮。另一方面还因为,这三姐妹时间观念差,每每因此而吃苦头,为避免下午六点的约会迟到,他也必须在这里监督。
悦子从学校一回来,就把书包往会客室里一扔,兴冲冲地跑上楼来,问:“今天是阿姐去相女婿吗?”
幸子吓了一跳,看见镜中雪子的脸色变了,便装作若无其事地问:“你听谁说的?”
“今天早晨春儿说的呀!是吗,阿姐?”
“不是。”幸子说,“今天是井谷阿姨请妈妈和阿姐去东洋饭店吃晚饭。”
“是吗,爸爸也去吗?”
“也请了爸爸。”
“悦子,你下去吧!”雪子对着镜子里的悦子说,“下去叫春儿来一下,你就不用上来了。”
通常雪子让悦子走开,悦子也不会听话地走开,但是今天她察觉到雪子的语调不对劲,就“嗯”了一声,乖乖地走出去了。不一会儿,春儿惶恐地推开隔扇,匍匐在门槛上问道:“有事吗?”看来,她已从悦子那里听到了风声,脸色煞白。贞之助和妙子见形势不妙,早已悄悄溜走了。
“春儿,今天的事,你是怎么对小姐说的?”
今天相亲的事,幸子不记得对女佣们说过,可也没有小心提防不让她们知道,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幸子感到自己有责任当着雪子的面,追问春儿:“说呀,春儿……”
“……”春儿低着头,匍匐在地上,以这样惶恐的姿势表示“我错了”的意思。
“你是什么时候对小姐说的?”
“是今天早晨……”
“你为什么要说呢?”
“……”
春儿刚满十八岁,十五岁就来这里做女佣,如今在内宅侍候,大家对她视同家人。虽说不全是这个缘故,但唯独她与别的佣人不同,一开始就在她名字后面特别加了个“儿”字(悦子有时叫她“春儿”这个爱称,有时叫“阿春”)。悦子每天上下学,都得横穿经常发生交通事故的阪神国道,必须有人接送,一般都是春儿担任这个差使。
经过幸子的盘问,才知道春儿是在今天早晨送悦子上学途中对悦子说的。春儿虽然平素能说会道,可一旦受到主人训斥,就立刻害怕得哆嗦起来,看着可怜兮兮的,反而让人觉得好笑。
“……唉,都怪我不够小心,打电话时总是不避讳你们。不过,你既然听到了,就更不应该随便乱说呀。今天根本就不是什么相亲,只是小小的私人聚会,这个你应该知道的呀。即便是那么回事,不是也有该说和不该说之分吗?……你怎么能把还没准头的事情,随便告诉小孩子呢?……你来我家多长时间了?又不是初来乍到,这点儿道理也不懂吗?”
“还不光是这件事呢。”这时雪子开口了,“你一向喜欢多嘴多舌,不该说的也到处乱说,什么臭毛病……”
姐妹两个你一句我一句地数落着,不知她是否听进去了,一直低着头,一动也不动地趴着。直到幸子发话“好了,你可以走了”,她仍然像死人似的不动弹,幸子又说了两三遍“你可以走了”,她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道了歉,起身退了下去。
“平常老说她,可她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幸子一边窥视还在生气的雪子,一边说:“都怪我不小心。打电话时完全可以说得让她们听不懂的。可是,哪里想到她会对孩子说……”
“何止是电话。最近你们常常在春儿能听见的地方商量相亲什么的,我一直很担心。”
“有这种事吗?”
“好多次了……咱们正说话时,她进来了,虽然大家都不再说什么了,可是她刚走出屋子,人还在门外呢,大家又大声说起来,我想一定是那个时候被她听去的。”
这么说来,幸子想起几天前,好几次都是等悦子入睡后,夜晚十点左右,贞之助、幸子和雪子,有时还加上妙子,几个人聚集在会客室里议论今天相亲之事,春儿不时从餐室送饮料之类来会客室。餐室与会客室之间只隔着三张拉门,拉门与拉门的缝隙有手指粗,即使在餐室里,也能清楚地听见会客室里的谈话。何况又是夜深人静,交谈时应更加小声,这一点竟然谁都没有想到。如果说只有雪子注意到了,或许是这样,可她当时为何不提醒我们一下呢?雪子素来说话声音很小,所以当时谁都没有察觉她有意压低了嗓音,再说,她不说出来,别人又怎么知道呢?真是要命,像春儿那样嚼舌固然可恶,可是像雪子这样不爱说话也令人头疼。虽然幸子这么想,不过雪子刚才用敬语责备的“大声说话”显然是针对贞之助的,而且当时她没有提出这个意见,可能是顾忌到贞之助,那就不能埋怨她什么了。事实上,贞之助的声音确实特别洪亮,在那种场合最容易被人听见的。
“雪子,你既然意识到了,当时要是提醒我们一下就好了……”
“拜托你们以后不要当着她们的面说这些事了!我并不讨厌去相亲……可是我讨厌被她们那些下人知道这次又没成……”雪子突然鼻子发酸,幸子看见镜中雪子的脸上掉下了一滴晶莹的泪珠。
“话虽这么说,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次是被对方拒绝的呀……是吧,雪子,你是知道的,每次相亲后,对方总是积极求婚,是我们觉得不很满意,才没成的,对吧?”
“不过,她们那些人可不这样想。这次又不成的话,她们会认为又是被男方拒绝了,即使不是这样想的,也一定会说三道四……所以……”
“好了,好了,这事就不说了吧——都怪我们不好。往后一定照你说的那样做。可别把脸上的妆弄花了。”
幸子想过去给雪子补补妆,又担心马上这么做会引得雪子伤心流泪,便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