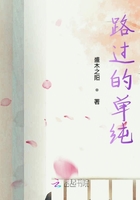和尚叹息良久,又说:“秦老弟,你的武功不过略胜玄天尊,但棋力么,胜了他可不止一筹。”秦伯符淡淡说:“不敢,晚辈自知武功浅薄,敌不过前辈的‘大金刚神力’,唯有在棋谱上狠下功夫。”和尚竖起拇指,笑道:“中,斗智不斗力,智者所为。”言讫落下一子。
秦伯符此刻胜券已握,只看怎样胜得潇洒利落。沉吟片刻,手一扬,黑子“嗖”地飞出,这一子乃是必杀之着,一旦落下,白子上方大龙遭屠,和尚非得弃子认负不可。不料黑子还在空中,和尚手中一子早已飞出,后发先至,撞上黑子。闷雷也似一声响,黑子跌落一旁,顿时错了方位。这么一来,白子大龙不仅长了出来,而且填死了右上角一片黑棋,秦伯符勃然大怒,厉声说:“大师这是什么意思?”
和尚光头摇晃,笑道:“秦老弟是智者,斗智不斗力;和尚是愚公,不会斗智,只会斗力。哈,秦老弟有能耐,也来撞我试试!”秦伯符不禁语塞。事到如今,棋局图穷匕现,二人任意一子,就能锁定乾坤,但此中胜负,已不在棋艺之上,而在武功高低。秦伯符只好硬起头皮掷出棋子,白棋立时又出,二棋相撞,石屑飞溅,双双四分五裂。
那和尚拍手大笑:“不错,如此下棋才有兴味!”梁萧一颗心随着二人落子怦怦直跳,他虽不懂下棋,却也看出这棋下到了紧要关头,二人不仅下棋斗智,还以绝顶内功驾驭棋子,抢占有利方位。一时间,空中棋子乱飞,越发迅急。初时相撞,各各碎裂,到后来,黑子撞上白子,白子分毫不损,黑子尽数粉碎,化作一团团轻烟。
梁萧武功虽低,也看出其中高下,心知这样下法,秦伯符是孔夫子搬家,全都是输。他心想:“要想个法子帮帮他才好。”一转眼,瞧见小和尚,顿生歹念,游目一瞧,身侧有一段荆棘,顿时计上心来。左手烧鸡在小和尚眼前一晃,遮住对方目光。右手偷偷伸出,从荆棘上折下几枚尖刺,作势吃鸡,将尖刺嵌入鸡腿,然后扯下鸡腿,笑着递到小和尚面前:“你还要吃么?”
小和尚两眼放光,急忙点头,抓起鸡腿,狠狠一口咬落。但只咬了一口,便张开大嘴,哇哇哭了起来。大和尚听到哭声,手中应付秦伯符,嘴里却忍不住问:“乖娃,你哭啥?”小和尚嘴里呜呜噜噜,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大和尚见状,连声叫他过去,小和尚只是张嘴号哭,哭得伤心伤意,完全不加理会。他离得又远,大和尚斗到紧要处,脱不得身,唯有大声叹气。
梁萧见那和尚心神大乱,暗自欢喜。忽然间,大和尚高叫:“罢了,输便输了!”袖袍一拂,长身而起,只一步,迈到小和尚身前。借着月光,梁萧隐约看清,大和尚身形伟岸,须眉皆白,显然年纪不轻。此时形势突变,秦伯符无所阻挡,一子落在枰上,奠定了胜局。他又惊又喜,心神松弛,一股气血直冲胸臆,禁不住咳得腰背蜷缩,状如一只虾米。
梁萧见他形容痛苦,暗自担心,抢上去攀住他说:“病老鬼,你怎么啦?”秦伯符举手连摆,嘴里却说不出话来,似要将心肺肝胆一股脑咳了出来。梁萧也感焦急,伸出小巴掌拍他背脊,给他舒缓气血。忽听老和尚冷笑一声,慢慢说:“秦伯符,和尚看走眼了,没瞧出你还有这种手段?明里与和尚下棋,暗里却藏了伏兵。”
秦伯符闻言愕然,竭力压住四处乱走的血气,抬头道:“大……大师,这话怎……咳咳……怎么说?”老和尚摊出大手,冷笑道:“你瞧瞧,这是什么?”秦伯符瞧他掌心里七八根尖利木刺,刺上还有血迹,更觉不解,茫然问:“这是什么?”老和尚道:“这是从我徒儿嘴里拔出来的,哼,鸡腿里面长出荆棘,倒是天下奇闻。”
秦伯符恍然大悟,怒视梁萧,眼内几乎喷出火来,梁萧心虚,后退两步。秦伯符忽地抬手,一个耳光重重抽在他脸上。这一掌含怒而发,虽已极力收敛,还是十分沉重。梁萧被刮得立地转了两个圆儿,“扑”的一声跌倒在地,和了血吐出两枚牙齿,左脸好似开了花的馒头,眼看着高肿起来。梁萧自幼被母亲捧着衔着,几曾遭过这样的毒手,呆了呆,才号叫起来:“臭老头,你打我……”话一出口,眼泪也流了下来。
秦伯符盛怒道:“臭小鬼,老子与人比斗,谁要你多管闲事?”梁萧叫道:“好啊,是我多管闲事了!我走了,你老病鬼是死是活,都不关我的事!”怒冲冲回头去抱狗儿。秦伯符一掌打过,瞧着梁萧小脸高肿,又觉出手太重了,一时怒愧交加,口中咳出血来。梁萧见他模样,怔了怔,又哼一声,抱着白痴儿,一溜烟跑了。
老和尚原想这小孩子想不出这等歹毒法子,一切出于秦伯符的授意。眼瞧二人争执,只当做戏,冷笑旁观。直到梁萧一怒而去,秦伯符情急下咳出血来,才悟出二人并无勾结,长眉一扬,说道:“你果真有病?”
秦伯符面如死灰,喘息道:“略……略有小恙!”老和尚目不转睛,瞧着他笑道:“只怕不是小恙,大概是强练‘巨灵玄功’所致吧。这样说来,你讨纯阳铁盒,是想治好内伤了?”秦伯符苦笑道:“大师神目如电。晚辈惧怕前辈厉害,是以练成了‘撼岳功’,还想再上层楼,修练‘无量功’。结果走火入魔,内劲反噬,‘恶华佗’吴先生瞧了,也是无计可施,他说……咳咳……他说……”
老和尚笑道:“老混球是否说,若非自废武功,不能痊愈。”秦伯符一怔,道:“前辈真是未卜先知,吴先生正是这般说的。”老和尚摇头道:“没有无量的气度,却来练无量的武功,好比抱干柴,引雷火,若不自焚己身,那才是奇了怪了!”
秦伯符听了这话,呆了呆,苦笑道:“大师说得是,这场比斗,晚辈输了。”一抬手便向小腹拍去,打算震散气海,自废武功。不料一支乌木棒横里伸出,搭上他双臂,秦伯符的手臂登时落不下去。只听老和尚笑道:“这一回算是打平,和尚不向玄天尊磕头,你也不用自废武功,等来日你练到‘无量功’,你我再斗不迟。”秦伯符听了这话,豪兴大动,扬眉叫道:“好,来日再斗!”
老和尚收棒笑道:“当年玄天尊凭借‘巨灵玄功’作恶多端,和尚也未脱金刚伏魔之性,故以这‘千钧棋’逼他自废武功。没想到他鸡肠小肚,耿耿于怀四十年!”他瞥了秦伯符一眼,“听说他为花家收留,那里桃源幽处,他该当晚年安宁,竟得善终吧!”秦伯符默然点头。
老和尚笑道:“玄天尊当年恃武行凶,即便不死于他人刀剑,只怕也被‘巨灵玄功’反噬,落得个功消人亡的下场。是以武功尽失,也未必不是好事。不过,你和你师父倒是全然不同,全然不同!哈哈,善哉善哉,驽马生得千里驹,野鸡抱出凤凰来!”他纵声长笑,伸出木棒一挑,将小和尚挑回肩上,大步流星,隐没在月色之中。
秦伯符瞧那和尚走远,心神松懈,又捂着口咳嗽起来,咳出一滩滩温热的鲜血。想到梁萧负气而去的神情,心中好不愧疚:“他一个孩子,我怎下了那种狠手,也不知那一巴掌,是不是将他打坏了?”支撑着直起身来,不料走出数步,忽觉头晕目眩,心头一惊:“糟糕,怎会伤成这样?”想着无奈坐下,盘膝运功疗伤。
梁萧奔出一程,脸上火烧刀割,左眼的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他又痛又气,回头扯起喉咙,老病鬼、臭乌龟、烂王八骂了一通,骂到后来,又痛得哭起来。哭了一会儿,忽觉一个柔软的舌头在脸上舔来舔去,将泪水舔干,心知是白痴儿。不由“噗哧”一声,又笑了起来,抱住小狗道:“还是你好,可惜你是条狗儿,要是变成人,那就好了。”想着扶起小狗的前腿,让它人立起来,连哄带拉,引它前行,但走了数丈,白痴儿支持不住,嗷嗷直叫。梁萧只好悻悻将它放下,心中气苦,抬眼望天,只见月正当空,群山幽白,山风徐来,带起林涛阵阵,有如人喊马嘶。
梁萧忽又想起白天的险事,不觉打个哆嗦,心想:“病老鬼又病又蠢,跟老和尚作对,必定要输。输了不打紧,只怕他口吐鲜血,浑身没力,被老和尚一顿拳头揍死。”摸着高肿脸颊,又觉快意,啐道:“我想他作什么?死了活该!”嘴里骂着,心中却有些莫名挂念,自语道,“我这阵子偷偷摸回去,任谁也猜想不到。且去瞧瞧,看他死了没有。”他犹豫再三,终又摸了回去,正离棋坳未远,忽听那边有人说话。梁萧拨开草丛一看,不由大吃一惊。
大小和尚不知去向,秦伯符气色灰败,盘膝坐着。身前站了一人,青衣小帽,满脸堆笑,正是那个何嵩阳。梁萧暗叫不好,却听何嵩阳呵呵笑道:“秦天王,别来无恙啊!”
秦伯符心中叫苦,却知此时此刻,决然不能示弱,竭力压住血气,冷冷说:“走狗就是走狗,鼻子灵,脚爪子也快。”何嵩阳目光如炬,在秦伯符脸上转了一转,呵呵笑道:“何某是做捕快的,讲的是眼明心亮,手脚利落。说到这追踪嘛,倒是略有心得。想当年采花贼秋满月轻功高妙,日行百里,踏雪无痕,何某自江南追到塞北,到底在和阗将他拿住;北邙盗容敬山,掳掠婴孩,险诈狠毒,擅长布设疑阵,他在南北六州与何某捉了三个月的迷藏,终究还是束手就缚……”他絮絮叨叨,说着往日的得意事儿,两只眼睛却死盯着秦伯符。秦伯符听他尽将自己与那些黑道宵小相提并论,虽然明知对方激将,仍是莫名惊怒。急咳数声,吐出一口血来,鲜血滴上身畔衰草,为月光洇染,显得触目惊心。
何嵩阳看这情形,笃定秦伯符身负重伤,神色一变,纵声笑道:“秦天王果然贵体不适么,呵,看来何某运气不坏。”秦伯符浓眉一沉,冷声道:“有能耐的,不妨拿我试试?”何嵩阳笑道:“恭敬不如从命。”手中哗啦作响,从腰间拽出铁索,七星索为秦伯符神功震断,丈八铁索只剩下了六尺。
何嵩阳手挽铁索,微笑道:“秦天王,你包庇案犯在前,屠杀官兵在后,罪行特大,何某也是无可奈何啊。”铁索迎风一抖,直奔秦伯符头颈。他索上钢锥已失,想要制住对手,唯有锁拿要害。
秦伯符瞧得铁索卷来,苦于下身麻痹,只得觑其来势,使巧一拨,正中铁索端头,那铁索“嗖”的一声,从他胸前荡开。何嵩阳一惊:“难道这厮诈伤……”心生忌惮,不敢上前,远远挥索进击,铁索化作一道青光,绕着秦伯符矫然纵横。秦伯符无力抵挡,唯有以手法拨开铁索,尽管这样,何嵩阳仓促间也无奈他何。
斗了十来招,何嵩阳瞧出秦伯符虚张声势,他心念电转,手中铁索挥出。秦伯符未及抵挡,何嵩阳忽地抬脚,将一枚石棋子向秦伯符挑去。秦伯符左手拨开铁索,沉喝一声,右拳挥出,将棋子荡开,这一拳他被迫使上内力,顿觉喉头微甜,胸口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