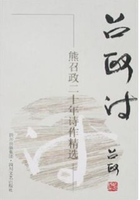爸爸一般每隔一年就会回来呆一个星期。他每次回来行李箱都塞满了他从市场里给我们买的礼物,像是闹钟收音机、皮夹、化妆品还有衣服。有一次他给我们每人带了一支侧面有个电子钟的笔。他给弟弟买了美国大兵的玩具模型和塑料枪,还从免税店给妈妈买了条温菲尔德蓝版的香烟。他住在勋熙区的布伦达姨妈家,几乎每天都会来看我们。
他会带我们去科驰曼或克拉伦登那样的高级餐厅吃饭,每次都用VISA、美国运通,要不就是大莱国际信用卡结账。我很喜欢鸡肝酱配热吐司。有时候他会跑去炸鱼薯条快餐店买上30几个布拉夫牡蛎,回家和我们一起一边坐在炉火前享受饕餮美味,一边看着外面风雨交加。
他喜欢呆到很晚,倒上一杯酒和妈妈聊天,而我继父则在一旁把电视机声音调小了看体育节目。我的房间紧贴着客厅,所以我能听见从墙的另一边传来爸爸的笑声。
大家都喜欢我爸爸。他是那么聪明幽默,慷慨大方,那么举足轻重。
在西德纳姆警察局,一个警察对我问话,想知道我为什么逃跑。对于他的问题我都以耸肩来回答,渐渐地他开始烦了。
“你想做个街头混混吗,黛博拉?”他说,“你再这么下去就是这个下场。”
“去你的吧。”我答道。
我听见爸爸吸了口气。
“我很抱歉。”他对警察说。
接着他带我回到我妈妈那里,好像一切都圆满结束了。
我到了以后发现所有人都在生我的气。我姐姐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气冲冲地跑去男朋友家了。
“这下你高兴了吧,”我妈妈说,“看看你闯了多少祸。”
继父离得远远地在那里忙活,忙着给大家添咖啡。
客厅里,我的弟弟若无其事地一边吃着烤芝士,一边看着《天龙特工队》。
当天晚上我准备再次出走。但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我又试图打开窗户。但是不管我怎么拉怎么推,它都纹丝不动。我这才发现他们用钉子把窗户钉死了。我跑过去想开门,但是他们把门也锁上了。他们把我当成动物一样关了起来。
第二天爸爸开着布伦达姨妈的福特安格利亚带我去普劳兜风。他很多年没在新西兰开车所以连交规都忘了。他变道也不打转向灯,一个司机经过我们的时候对他竖起了中指。
我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开车出去兜风是在斐济,我们从南迪开到苏瓦。那天雨下得很大,透过挡风玻璃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我们只好靠边停了下来。我们在一间小小的餐厅吃了块辣味披萨,我还看见墙上有只壁虎在往上爬。晚上他手里拿着他那瓶伏特加坐在阳台上,伴着阳台下面青草之间的蛙鸣,给我讲起哈维·克鲁和珍妮特·克鲁夫妇的双重谋杀案[1]。
再后来我们飞去旧金山。我们去了渔人码头,玩游戏还赢了奖品。那可是真正的奖品,比如绒毛玩具、掌上游戏机什么的,而不像“坎特伯雷农牧博览会[2]”,那里只有傻不拉几的转头小丑,你要是能赢到个卷笔刀或是吸管就算走运了。
爸爸从普劳的某个小店给我买了个肉饼。我们一起坐在沙滩上的半块木头上。潮已经退了,在沙泥里留下一个个小洞。
“我们都担心你出事了。”他说。
天开始下雨。
“如果我真的死了呢?”
我把肉饼丢在沙滩上转身向车子走去。
第二天爸爸对我说——
“我们觉得你应该找个人谈谈。”
“我可以去见特伦特吗?”
“不行,他是个蠢货。”
不一会儿我已经坐在我继父那辆宽敞的老福特车的后座上,被爸爸和妈妈夹在中间。他们告诉我说我们这是要去见一个心理咨询师,看看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心理咨询师的办公室似乎很远。但是这么坐着车倒也不坏。我继父时不时从后视镜看几眼坐在后排的我们几个。
我坐得浑身都要散架了,眼睛也很痛。在我快睡着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机场的入口,这才意识到我被耍了。我朝妈妈大声吼叫起来。
“别把我送走!”
但他们根本不理我。妈妈紧紧抓着我的胳膊,爸爸从后备箱拿出一个行李箱。我使劲想从妈妈的手里挣脱出来,随时准备逃跑,但她的指甲深深嵌入我的手臂里。
“求你了,”我央求道,“我再也不敢了。”
“你只是去奥克兰住几天,这样你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不是去香港吗?”
“不是啊,只是去奥克兰。”
于是我跟着爸爸走了。我回头看时,继父正拉着妈妈走远。
注释:
[1]住在新西兰一农场上的这对夫妇于1970年6月17日前后双双被谋杀,因为证物中存在很多疑点,成为新西兰轰动一时的犯罪案件。——译者注
[2]新西兰最大的农牧博览会,至今已有150多年历史,博览会将农业和娱乐结合在一起,平均每次能吸引11万人参加。——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