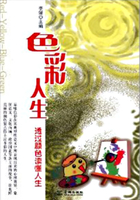“如果你敢报道关于这件事的任何消息,就别想活着离开希腊。”名叫雅尼斯的男人此刻正手托一杯茴香酒,慵懒地卧在躺椅上。他的口气是那么温柔无害,仿佛在说“再不快点,你就要错过渡船了”这样一句稀松平常的话。
阿吉不安地扭过头,椅子在石板地上摇来晃去,暗自思忖到底哪儿来的愚蠢冲动,让自己脱口而出“我是记者”这句话。但是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无法挽回。
“噢,我从来不报道那种事情的,”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声音,“我都是报道名人婚礼啦,困在树上的小猫啦……”说着她不自然地干笑一声,算是结束。
可是别人没笑,雅尼斯就这么瞪着她,很明显,他一个字都不信。有很多苍蝇——传说中跟小鸟差不多大的希腊苍蝇,围着雅尼斯身边户外桌上的茴香酒瓶、冰水、一大盘凉菜嗡嗡嗡地飞来飞去,但他自己身上却一只也没有。
“我在山路上开车时,会对你多加小心的,”他缓缓说道,“希腊司机有时很粗心的。”
“你这是在威胁我,是吧?”她这几周遭遇过好几匹驴子,它们受到惊吓时的叫声都比自己此刻的声音好听。
“当然不是,那可不是我的待客之道。”阿吉觉得他很享受眼下的一切。
她知道应该放下杯子起身离开,但毕竟是自己搞砸了一切,现在想走也走不掉了。视野尽头那两棵橄榄树之间,立着阿吉的帐篷,虽然脏兮兮的,但所幸没有塌掉。
自行车篮袋就那么敞开着,行李散落在四周。她甚至抽空把洗好的衣服晾在了两棵树之间临时拉起来的晾衣绳上。
她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了,全身而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以客人的身份留下来跟这凶恶的暴徒共处一室也好过现在离开。虽然她还是无法肯定雅尼斯是不是个暴徒,但刚才那句关于悬崖顶上的粗心司机的话,算是一条佐证,除此之外,他那两个同伴死水一般的沉默也让阿吉很不放心。
阿吉偷瞄了一眼自己的帐篷,只是眼球稍稍斜了一下,都没能逃过雅尼斯的眼睛。“希望你在我们的橄榄林里度过愉快的一晚,”他客气地说道,此刻,这客套的寒暄听着却更像是威胁。
“谢谢你!”她歇斯底里地叫道。
他笑了,就在一个小时前,这副微笑还显得那么完美、迷人,而现在,却让她不寒而栗。事实上,关于雅尼斯的一切,都叫她不寒而栗。
6个多月前,她的上司托尼冲她喊道:“你要去干嘛?”阿吉没指望他会为此高兴,果然不出所料。
“我准备骑行环游希腊,在营地露营,用防风炉具自己做饭。”她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你会骑自行车,你是疯了吧!”托尼说道,“你之前去过希腊吗?”她之前是没去过,但好几年前就想去了,甚至一直在死磕希腊语这门难到极致的语言。
“你知道希腊有多少山吗?”托尼继续说道,“你就没发现没有‘环希腊自行车赛’吗?你有没有听说过哪个著名的希腊车手?你听说过有谁骑行环游过希腊?原因很简单,只有疯子才会骑行环游希腊!对了,你想过野狗的问题吗?”
托尼刚40出头,作为一名日报主编算是年轻有为。眼下,他们正在他那间位于报社尽头,堆满了纸张、文件、照片的办公室里。他还在不停的强调自己的重点,“在希腊会有成群的野狗把人撕成碎片,你打算怎么办?”
这是个贱招,她怕狗:“用驱狗剂?”
他鼻子里发出一声轻哼,轻蔑地朝她摇了摇手。
于是,在一个仲夏清晨,阿格尼斯·琼斯向希腊进发了,陪伴她的只有一辆不知该怎么骑上去的自行车:车上挂着沉重的马鞍袋,好像一间露营商店似的,里面乱七八糟装满了露营用品,有些她甚至还不会用。当然,还有一罐最重要的驱狗剂。阿吉感觉自己像个冒险家,没有摄像机拍摄自己“出征”的画面简直可惜了。来送她的只有妹妹艾伦、托尼,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同事,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她神志是否清醒产生了怀疑。
她舟车劳顿地来到第一站,伊古迈尼察。这是一座位于希腊西北部的城市,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在那里跟一位穿着寒酸的人办理了事先预约好的服务以后,她深吸一口气,开始朝南方骑去。她不是个新手,但也不算经验丰富。托尼说对了:希腊境内山峦密布,陡峭难行,一旦失手肯定会摔个粉身碎骨。不过,有自行车意味着她不用自己扛行李,这就像匹能堪重负的机械坐骑一样,不用每半小时就停下来休息、喂食。
两个月后,阿吉到达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此时她已经收获了不少在希腊骑行、露营、野炊,以及在没有厕所的乡下解决内急的经验。也是这个时候,她才发现之前在皇后公园舒适的小套间里反复摆弄、查看的希腊地图其实跟真实的希腊有着天壤之别——平坦的纸张太具有误导性了,而且还用令人愉悦的明黄色帐篷图案标注散落各处的露营地——真实的希腊几乎没有一条路是平坦的,陡坡更是一处比一处险峻;露营地之间实际相隔遥远,气温也直逼40度大关。
这天,阿吉在黎明时分收了帐篷,真是美好的一天,天气只是暖和,还不算炎热。她沿着陡峭的沿海公路一路骑行,老鹰在头顶盘旋,耳畔只有在山坡上漫步的山羊脖子上的铃铛在叮当作响。这一刻,她觉得整个希腊都属于自己,若有人问及现在的感受,她一定会说“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然而世事难料,谁也想不到,阿吉在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开心无忧了。
如今看来,漏气的轮胎嘶嘶作响应该算是坏事降临的前兆。没一会儿,它就像块儿煎饼似的摊在地上了,车轮钢圈直接压在了轮胎皮上。阿吉只得停下来,沮丧地盯着它。
“去你妈的!”阿吉对一只山羊骂道,这家伙稳稳站在30英尺[1]高的山崖上,仿佛对这个人类的处境很好奇。
阿吉的包里有个补胎工具箱,这是在伦敦的自行车行里,那个管她叫“吕四”的口齿不清的小伙子倾力推荐的。之前她对补胎没什么概念,只在看到一名乐于助人又帅气的补胎工时才简单幻想过那个场景,人家能用技巧自信地掌控全局,而她只能钦佩地远远看着。
可这荒山野岭的,根本没有补胎工,更妄论帅气的补胎工了;这儿只有焦虑的阿格尼斯·琼斯和一只享受着平静生活的山羊。
补胎工具箱是跟一瓶止咳含片差不多大小的金属小盒子,里面没有说明书,只有一堆奇奇怪怪的小部件。阿吉禁不住再次爆了粗口。她依稀记得,补胎这事儿跟水啊,泡泡什么的有关——她意识到自己怕是得牺牲宝贵的饮用水来修补轮胎了。
整个过程真是麻烦重重:先要把轮胎卸下来,然后还要搞清楚水、粉笔、补丁皮、胶水、小撬棍的使用方法。把车胎补好,再把轮胎装回去,仿佛用了一辈子这么长时间。等她修好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时分了。汗不停地从鼻尖上滴下,整个人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T恤短裤都黏在了身上。最糟糕的是:她的饮用水全都用完了。
离今晚的目的地还有12英里[2]之遥,那里有个很令人向往的名字:露营天堂。可去往那里的路却崎岖不平,要不停地上山下坡,比之前更加险要。
阿吉查看了一下地图,发现了救星:在她目前的位置和露营天堂之间,有个非常小的村庄,叫埃克索拉,这是希腊语“村庄”的意思,也是希腊最常见的村庄名称。但如果周围有两个以上叫这个名字的村庄就会让人很困扰,幸好这里只有一个埃克索拉。它的位置就在海边,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而建,活像一条愤怒的蛇。
她步履维艰地走着,一转弯却发现埃克索拉就在离她几百英尺[3]远的前方,整个村庄风景如画,美丽得不真实。走过岔路口以后,她骑上了这条只比铁轨宽一点的羊肠小道,一路上全是近乎直角的转弯,逼得她不停刹车。
地图显示,这个村庄没有露营地,所以她得开间客房过夜。那得是间海景房,站在阳台上可以眺望大海,最好还有一副桌椅供人休息放松,要是桌上有一大壶冰水就完美了。
如果有一个地方其实是看似美好的海市蜃楼,那肯定是埃克索拉。不仅唯一一家破旧的咖啡馆兼餐馆关门了,就连村里那间身兼肉店、面包店、蜡烛店数职的全能小店也关门了。为了抵御热浪,这里所有的房屋都大门紧闭,一派闭门谢客,很不友好的景象。
就好像所有人都逃走了,所有人都瞒着她海啸将近,或者耶稣再次降临这样的消息似的。
现在是午休时间,当然啦,她怎么把午休给忘了。要几个小时之后,村民们才会纷纷走出屋子,让整个埃克索拉复苏生机。这会儿,阿吉的喉咙渴得像火烧似的,她骑着车在村里仅有的四五条古老的鹅卵石路上颠来晃去,想看看有没有空房出租,顺便看看有没有哪位好心人赏她一口水喝。可是不仅找不到房子,连个人也见不着,好心的不好心的都没有。而且她觉得客栈里也不会有空房——因为根本没有客栈。
心力交瘁的阿吉朝码头骑去,接着她骑上了海边的一条石头路,这条路绵延几百码[4],前面被岩石挡住了视线。也许这条路的尽头是间农舍;也许那儿会有些清醒的人;也许他们会给她水喝……
绕过那岩石,是另一片小海湾。那儿没有农舍,却立着一栋大别墅,金碧辉煌的造型在这片土地上显得鹤立鸡群。别墅周围像老母鸡护崽似的围了一圈护栏,上面还挂着若干块画着醒目骷颅头标志的电击警示牌。如果这还不够震慑人,瞧瞧从旁边狗窝里跑出来的那只凶恶的猎犬,它的脸上满是被从午休中吵醒的不爽表情。
这是只土黄色的猎犬,看不出什么品种,不过是多种恶犬杂交的产物罢了。迎接阿吉的,是一张特写的狗脸:它瞪着黄色的眼睛,张着满是口水沫的嘴,龇着发黄的獠牙,狂怒地搭在栏杆上。它没有高声狂叫,可那低吠的架势更叫人害怕。
“会咬人的狗不叫,你要当心。”出发前夜,托尼曾幸灾乐祸地对她说,“叫的狗都没什么可怕的,反而是那些一声不响的,他们的利爪是在为更重要的事做准备呢。”
“多谢提醒,”她说道,“那到时候我爬上树就好。”
“那边没树可爬!”他用更加幸灾乐祸的口气补了一刀。
唯恐看起来安全的护栏反而拦不住狗,阿吉迅速爬上车,一溜烟跑了。别墅不远处是一片橄榄林,外面同样围着护栏,不过往前50码[5]左右的地方,大铁门开了条缝,露出门后的林间车道。在巨大的树荫下面,停着一辆房车,不是日常旅行的那种,而是电影里那种跟房子差不多大小的房车。阿吉简直无法想象这车怎么开下山来的。
户外桌边的三张躺椅上分别躺着两男一女,桌上放着满满一盘凉菜,一瓶茴香酒,还有一大壶冰水。此刻,她的嘴干得就像但丁笔下的地狱,恨不得立刻冲上去喝几口。
年长的那个男人率先注意到了她,看到了门口的一副奇异景象: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红发陌生人,正垂涎三尺地看着他们桌上的水。他停下谈话,吃惊地看着她,然后朝她挥了挥手,用希腊语喊了句话。
“不好意思,我没听懂你说什么,”她回过神来,用英语回答道,眼睛却仍然紧盯着他们手里的杯子和杯中浮着冰块的水。
“英语!”已过中年的男人惊呼道,他肚子大得像个枕头,“那你肯定是英国人了,只有英国人才会发疯到顶着这样的大太阳骑车。”
“是啊,只有我跟一条疯狗,”阿吉表示同意,关于国籍的说辞,她也懒得分辨,“我的车胎在山里被扎破了,我已经连续好几个小时断水了,快要渴死了。”此刻已经顾不上矜持了。
“过来,”那人立刻说道,起身往旁边稍微挪了挪,“过来,跟我们一起吃。”
那人话还没说完,阿吉就走上了那条车道,“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他说自己叫乔吉奥斯,阿吉猜他60出头。大概是一直坐在橄榄树下喝茴香酒,他的脸颊上露出微醺的神色。只见他猛地撑开靠在房车上的第四张躺椅,然后用希腊语对那个女人吼道:“再拿个杯子来,玛丽亚。”
那个女人很年轻,也就20出头,长得安静甜美,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梳成一根马尾辫伏在脑后。她有着橄榄色的皮肤和一双黑色的眸子,只是鼻子在这张小脸上显得太大了。她的举动像被谁恐吓了似的:微微弯着腰,仿佛在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似的故意佝偻着身子。
乔吉奥斯介绍说,那位年轻人是他的儿子,叫雅尼斯,是玛丽亚的丈夫。雅尼斯一副典型城里小开的模样:梳着个大背头,头上的发胶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身上的金饰品多得快赶上一间珠宝店了。他穿着黑色牛仔裤和紧身T恤,紧得就像画上去的一样。他看上去很像阿吉本来以为自己会在雅典著名景点遇到的那种痛宰肥羊的小混混。只是眼下的他非常安静、警觉;点了个头算是打招呼,不苟言笑,一言不发。
乔吉奥斯弥补了儿子沉默的空白,一个劲儿地说,很快阿吉就对乔吉奥斯了解得相当透彻了。他说自己这辈子都在比雷埃夫斯的渔船上工作,现在退休了,便回到了生养自己的故乡。他自己住在村子里,房车是雅尼斯和玛丽亚的。他边比划边说道:“他们正在盖自己的房子,就在这条路往前走一点的地方。等房子盖好了,就从房车里搬出来。”
“这房车真不错。”阿吉礼貌地喃喃说道,她不太关心玛丽亚跟雅尼斯的生活,因为现在她满脑子都在想那杯冰水到底他妈的在哪儿?
仿佛过了三辈子,玛丽亚终于回来了。她手里拿着一杯新的冰水,杯壁外面挂着水珠。这水看着太诱人了,阿吉只能勉强忍住从玛丽亚手里一把抢过来的冲动。在她一口气喝完水以后,玛丽亚紧张地笑着为她又添了一杯,然后拿起桌上的酒瓶,倒了一杯茴香酒。
现在乔吉奥斯想了解了解阿吉——她是谁,从哪儿来,骑车来他们村子里干嘛。“你是从伊古迈尼察一路骑行过来的?”他不禁挑高眉毛,“我从来没听过有人干过这件事,你很勇敢,不是吗?”
“您过奖了。我只是喜欢这个——除了遇到像今天这种不顺心的事情,但是我发现这里的人真好。我正赶往下一个露营地,却被困在这儿了,谢谢你们的款待。”
“荣幸之至,”雅尼斯第一次开口说话了。那讽刺的语气让阿吉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但他寡淡的表情又让阿吉觉得可能是自己多心了。
“欢迎你今晚在我们的橄榄林里宿营,”乔吉奥斯热情万分地邀请道,尽管这根本不是他家,“这里是很简陋,但有树荫。而且,你留下来的话,雅尼斯跟玛丽亚也乐意让你用他们房车里的浴室。”
她没看出来雅尼斯跟玛丽亚有多愿意,但她又能如何呢?乔吉奥斯已经确定村里无房可租了。如果她拒绝了这份邀请,就意味着要翻山越岭地往回走。但她不想往回走,绝不,至少今天不可能,就算要睡在沙滩上她也认了。
“来嘛,”乔吉奥斯完全无视饭桌上突然弥漫起来的紧张气氛,“我给你找个好地方。”
乔吉奥斯在前带路,有点踉跄地走到了橄榄林中间一根竖在地上的水龙头前。“就这儿!”他宣布道,“阴凉又湿润。”他坚持要拿上她的帐篷,还要亲自帮她撑起来。趁着乔吉奥斯骂骂咧咧地忙得一团糟的时候,阿吉在水龙头下面洗了点衣服,然后晾在了两棵树之间拉起的绳子上。最终帐篷还是立起来了,只是歪歪倒倒得像个醉汉,就跟乔吉奥斯自己似的。
“真棒,”她言不由衷地说道,“谢啦!”
回到桌边,雅尼斯跟玛丽亚依然相对无言地坐在那儿,很明显,两人之间有些不对劲。阿吉试着询问玛丽亚她从哪儿来、做什么工作的时候,却见她低着头目光躲闪,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声算是回答。
“玛丽亚不怎么会说英语,”雅尼斯居高临下地说道。
“好吧,不过你的英语很棒,”阿吉朗声说道,开始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过了一会儿,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她开始问雅尼斯的工作。
众人的反应却好像阿吉在问他是不是恐怖分子,最近有没有搞爆炸袭击这样的问题。停顿了好一会儿后,他才缓缓说道:“打打鱼,做点保安工作。”
听到“保安工作”这个词的时候,乔吉奥斯大声地用鼻子哼了一声,满是轻蔑;而玛丽亚的脑袋都快要埋到地里去了。她今晚一直这样,脸颊涨红得像个熟苹果。也许她不怎么会说英语,但很明显她听得懂。
阿吉靠在椅子上,乔吉奥斯给自己斟酒斟到一半,又帮她把杯子添满水。“保安工作?真想不到这个地方还需要保安,这里很平静啊……有什么要看管的吗?”
“你肯定会惊讶的,小姐,非常惊讶,”乔吉奥斯像在炫耀什么似地低吼道,甩给坐在对面的儿子一个鄙视的表情。他现在就像一个进入倒计时的定时炸弹,满脸醉意地急着跟别人掏心窝子。
相反,雅尼斯看上去一点都不想让他父亲跟别人袒露心声,他严厉地说了一句希腊语,语速太快,阿吉没听懂。但是那语气错不了,肯定是类似“你再敢说一句试试”这样的话。但那句警告似乎起了反作用,喝醉了的乔吉奥斯誓要揭开家丑。
“我儿子啊,”他说道,“身居看管女孩子们的要职。”
“你的意思是?”
乔吉奥斯没回答,只是一个劲地点头,等着她自己领悟。
“啊,你是说……妓女?”
“对!”他咆哮着用拳头砸向桌面,“妓女!”
雅尼斯的脸都气白了,玛丽亚则仍然在“研究”地上的土石,能看得出她整个身子都紧绷了起来,像要准备挨打似的。看来阿吉一不小心捅了这家的马蜂窝。
“村里有妓院吗?”阿吉尽量保持着平静的语调,“我猜应该不是政府登记许可的那种吧……?”不用问也知道肯定不是。在希腊,卖淫是合法的,但也有很多法规限制。相比那些政府登记许可的合法妓院、妓女,未登记的非法妓院数不胜数。
听到这个问题,乔吉奥斯哈哈大笑。雅尼斯气得咬牙切齿,就像刚才路边那只狗。
“那些女孩子们,她们是从哪儿来的?”
乔吉奥斯不笑了,他儿子的一腔怒火让他清醒了一些,“她们是外国人。”
“外国女人会心甘情愿来希腊当妓女?”阿吉挑了挑眉,“我觉得外国女人不太可能来希腊做‘生意’啊。事实上,我觉得除非走投无路,没哪个明智的外国妓女愿意来希腊。”
“别理我父亲,”雅尼斯猛地打断了她的话头,“他喝醉了说胡话呢。”
“我没喝醉,”乔吉奥斯醉意十足地说道,“也没说胡话。”
雅尼斯再一次用希腊语警告了他。
乔吉奥斯连人带椅子整个转了过来,背对着儿子,直接看着阿吉说:“那些女孩子们是被迫来这里的。”
“噢,我明白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带来一阵沉默。
“那警察不管吗?”阿吉的余光瞄到雅尼斯正愤怒地坐在那儿,于是她便把目光集中在乔吉奥斯身上,“在这种小地方,流言传得飞快,大家肯定很快就知道这件事了,也包括警察,对吧?”
“这帮警察,”乔吉奥斯轻蔑地哼了一声,“哈!既然有——这话你们怎么说来着——免费的‘试用品’跟大把的贿赂送上门,他们为什么要管这事?”
“你问题可真多啊,”雅尼斯插了进来,把注意力从乔吉奥斯那儿转移到了阿吉身上,“所以你是干嘛的?记者?”
“对,”她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是记者。”
一切陷入一片死寂。乔吉奥斯的酒一下子就醒了;玛丽亚赶紧看向雅尼斯,像只受惊的小兔子,但他看也不看她。雅尼斯开始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重新打量着阿吉。
后来他就说出了之前那些关于粗心的希腊司机的话,而阿吉则开始胡扯困在树上的小猫。
注释:
[1]约9.14米。
[2]约19.3公里。
[3]1英尺约合0.3米。
[4]1码约合0.9米。
[5]约45.7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