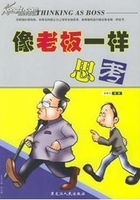张凤山知道了宋铁军在抗日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他是主张抗日的,这对自己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这次他从延安带回来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虽然这个指示尚未对外公布,但主要精神已经内部传达,这个指示对取消苏维埃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变红军番号和加强党的组织与群众工作等作了原则说明,要求红军和游击队中较大的部队与就近的国民党驻军或地方政府进行合作谈判。上级还强调:“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上述这种改变的必要。但同时应该指出,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的工作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他想如果宋铁军不是对共产党人赶尽杀绝,自己很有可能亮明身份,说服文城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与他合作抗日,但是在目前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还是小心为妙,尤其要对宋铁军时时抱有提防之心,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暴露真实身份。“冯先生爱国之举感人肺腑,我只能用‘热血沸腾’四个字表达自己的感受。”
宋铁军鼓起掌来,说:“我亦与张先生有同感,看来我这趟是不虚此行了。最后我还有一言相告,徐医生是刘成龙师长的外甥女,医术精湛,平时我也敬她三分,而且她对你有救命之恩,不指望你涌泉相报,只是请你不要为难于她。”
张凤山这下吃惊不小,没想到徐语晴所说的舅舅竟然是刘成龙,也怪自己太粗心大意了。刘成龙手下有五个团驻守在文城,是本地最大的一股武装力量,虽说是由一些杂牌军组成,但手里有真家伙,比起游击队和保安团的装备来,不知好上多少倍。“凤山有恙在身,加上自小娇生惯养,处事有些任性,今后我会努力克服。”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等着你早日康复归来。”
宋铁军告辞走了。张凤山仔细回忆与他谈话的每个细节,生怕言语失当而引起宋铁军的警觉。他想一个谎言要靠很多的谎言来掩盖,要想不被识破,只有做到假痴不颠才有可能。张凤山喜欢读《三国演义》,里面就有许多这样的经典故事,比如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早已有夺取天下的抱负,只是当时力量太弱,根本无法与曹操抗衡,而且还处在曹操控制之下。刘备装作每日只是饮酒种菜,不问世事。一日曹操请他喝酒,席上曹操问刘备谁是天下英雄,刘备列了几个名字,都被曹操否定了。忽然,曹操说道:“天下的英雄,只有我和你两个人!”一句话说得刘备惊慌失措,深怕曹操了解自己的政治抱负,吓得手中的筷子掉在地下。幸好此时一阵炸雷,刘备急忙遮掩,说自己被雷声吓掉了筷子。曹操见状,大笑不止,认为刘备连打雷都害怕,成不了大事,对刘备放松了警觉。后来刘备摆脱了曹操的控制,终于在中国历史上干出了一番事业。
“该打针吃药了。”徐语晴端着药盒进来。
“我脑袋受伤,最近有些胡言乱语,你别计较啊。”张凤山想起今后还要借助徐语晴,便主动缓和一下关系。
徐语晴一边给他打针一边说:“我要是计较,早丢下你不管了。”
“我今后要是再对你发脾气,你就把我捆起来,等我冷静下来就会好的。”
“你是病人,我是医生,我不会这样做的。”
“我不会怪你的。”
徐语晴有些看不懂张凤山,他一会疯癫、好歹不分,一会又通情达理,让人哭笑不得,难道真的是他脑部受了损伤所致?要不然就是受了严重刺激造成的,想到这,她问:“他们真的逼你杀了人?”
“你偷听了我们之间的谈话?”
“什么偷听?你那么大声,我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
张凤山见徐语晴提到“他们”,似乎与她无关,便问:“你刚才说他们,你难道不是县党部的人?”
徐语晴说:“我是啊,可我不是特务。我们医院是公立医院,主要为政府和军队服务,所以县党部安排的工作任务,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
原来是这样。但张凤山仍然不敢相信她的话,因为她如果不是特务,又怎么会有枪?“既然你已经听到了,还问这个干什么?我不想再提这事。”
徐语晴说:“你别忘了我是医生,现在你告诉我杀了什么人,或许我可以帮助你解除精神痛苦,使你不再做噩梦。”
张凤山见徐语晴打破砂锅问到底,知道她并不晓得此事,看来她刚才所说有些可信,便想再试她一试,便说:“他们逼我杀了一个共产党。”
徐语晴闻言手抖了一下,小药瓶掉在地上,里面的药撒了一地,她掩饰说:“手上有汗,没抓紧,我重新给你弄。你刚才说他们逼你杀了一个共产党,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动手,而让你去做?”
“我要是知道原因就好了,现在每天晚上我都会梦见那个共产党向我索命。”
徐语晴安慰说:“你精神太紧张了,一定要放松,如果是他们逼你干的,这不是你的本意,你要忘掉这件事。”
张凤山点了点头,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不管怎样我都要谢谢你!”
当晚,张凤山又大呼小叫起来。
徐语晴连忙过去,看见他四肢颤抖,嘴里絮絮叨叨:“你别过来,不是我害死你的,要找你去找宋铁军索命。”
徐语晴过去抱住他的头,问:“又做噩梦了?”
张凤山点了点头。
徐语晴见他满头大汗,便掏出手绢替他擦汗,说:“你受了刺激,加上脑部受了损伤,发生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初期症状较轻,越到后来会越重,明天我给你开点精神类的药物辅助治疗。”
张凤山心里偷着乐,他想只要徐语晴相信就好了,她是专业人士,由她向宋铁军说明自己的病情效果会好得多,他不想被宋铁军过于关注,如果被他盯得死死的,自己纵有天大本事,也难以施展拳脚。
可是吃药的事又很让他犯难,是药三分毒,更别说这种刺激神经的药品了,不但副作用很大,而且不是对症下药,这样吃下去的危害会更大。
所以当徐语晴给他服药的时候,张凤山问明是什么药,有什么作用?徐语晴一一说了。张凤山将抗菌消炎的药吃了,将神经类药品放在一边,说:“刚吃了许多药,胃里不舒服,这药等会我自己吃就行。”
待徐语晴离开后,张凤山快速地下床,将药品扔进了厕所里面的下水道里。
下午,张福海突然来了,看到儿子能下地行走了,十分高兴,对徐语晴表示感谢。
徐语晴称这是她的职责,然后推托有事,让他们父子俩聊。
张凤山见她善解人意,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其实他心里有许多疑问要请父亲解答。他关上房门,然后请父亲在沙发上坐下,便忙着泡茶。
张福海并没有说话,他默默看着儿子,直到张凤山将一杯茶放在他面前的时候,突然说:“孽子,给我跪下!”
张凤山犹豫了一下,还是跪在了父亲面前。
“你对我老实说,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张福海阴沉着脸问。
张凤山自到文城以后,一直在圆这个谎,在敌人面前当然不能承认了,现在当着亲人的面,他内心里感到十分纠结,他从来没有在父亲面前撒过谎,这次就当是一次例外,也算是一种善意的谎言。“我不是。”
“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我看你是在撒谎?”
“爹,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这几年你到哪里去了?”
“我是遵照爹爹之命,一直在日本留学,直到日本政府驱逐留日中国学生,才不得已回来的。”
“你回来之前为什么不拍个电报告知行程?”
“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张福海见儿子对答如流,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起来,如果你是共产党,我宁愿你死了,权当没有你这个儿子。”
张凤山起来,直视着父亲,问道:“爹,你为什么说我是共产党?”
张福海叹了一口气,“是县党部的宋书记长说的。”
“他这是栽脏陷害,这点您都看不出来吗?”
“我也不愿意相信,所以要你亲口说出来。”
张凤山见父亲的眼神里有一丝疑虑,知道他并没有完全相信自己,便说:“爹,那个宋铁军昨天晚上来过,亲口向儿子道歉,承认他们抓错了人。我再也不想在这里呆了,我要跟你回去养伤。”
张福海摇了摇头,说:“孩子,我和你娘也想你马上回家,可是现在不行,你必须把伤养好才能回去。”
“为什么?”
“世道险恶,等你伤养好后,还是跟爹后面做生意吧。”
张凤山见父亲不愿意说,心想他肯定有难言之隐,一定又是那个宋铁军捣的鬼。便激将说:“爹爹心里有什么事瞒着孩儿?”
张福海说:“告诉你一件事,叶明义死了,在你被他们抓起来的第二天中午,官方说是心脏病突发死的,民间传言他是被县党部的特务暗杀的。”
张凤山大吃一惊,叶明义是自己的恩师,是一个正直善良、追求民主的进步人士,如果按照父亲的说法,他确实死得蹊跷。张凤山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本来这次回来他打算拜访恩师,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发展进步力量,没想到残酷的现实再一次摆在了他的面前。
这时,徐语晴敲门进来要给张凤山换药,张福海见状称家里还有事,表示过几天再来看他,临走再一次向徐语晴表达了谢意。
张凤山观察到徐语晴脚上换了双布鞋,而不是以往常穿的皮鞋,怪不得敲门的时候没听见她走路的声音,看来她一定又是偷听了他们的谈话。
晚上临睡前,徐语晴又过来给张凤山服药,张凤山故伎重演,表示要分开吃。
徐语晴不依,说:“我要看着你把药吃完。”
张凤山知道蒙混不过去,只好当着徐语晴的面把药吃下去了,然后张开嘴说:“你看,全部吃下去了。”
徐语晴想要说些什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张凤山怕她打开话匣子收不住,连忙说:“我要睡了。”
徐语晴只好说:“那你休息,晚安。”
张凤山听见隔壁关门的声音,连忙起床跑到厕所里,用手抠喉咙,将吃下的药全部吐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