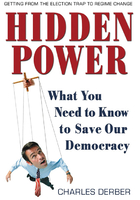陈友亮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打着呵欠说:“要去你去,我不去。”
“你怕什么?”
“那个张福海还好说话,听说他的家人扬言不放过我,现在他们一家子都在医院守着,我去了岂不是自讨苦吃么?”
“那我替你去打探消息,你能不能再多分我一成?”
陈友亮不耐烦地说:“你这个婆娘,口口声声离不开钱,你现在一辈子吃穿不愁,要许多钱做什么?”
菊仙反驳说:“钱多了还能扎手啊?我可比不了你老婆,跟着你吃香喝辣、穿金戴银,我是无名无份,如果不捞点实惠,否则人老珠黄的时候被你一脚踹开,你让我喝西北风去?”说完,眼角挤出几滴眼泪,一副含冤受屈的样子。
陈友亮说:“老婆那是父母之命娶的,没什么过错我又不能休了她。再说我的心不还是在你身上吗,你要那个名份干什么?去吧,再给你加一成。”
菊仙欢天喜地去了,她来到医院假装找人,打听到张凤山所在的病房,正要进去察看时,被徐语晴拦住了,问她做什么?菊仙说受人之托来看张凤山。
徐语晴见她打扮得十分妖艳,便有些反感,没好气地说:“他还在昏迷之中,连他的家人都不准探视,更别说外人了。”
菊仙将信将疑,但她心有不甘,想亲眼见证一下。菊仙趁医生查房之际,偷偷从一间办公室里拿了一件白大褂穿上,然后趁徐语晴上洗手间的时候,溜进了张凤山的病房,只见一个人整个头部缠满了绷带,要不是眼、耳、鼻、嘴在外面,还真像个木乃伊。
菊仙靠近张凤山,用力推了他一下,只见他两眼紧闭,一动不动,便不再怀疑徐语晴的话,放心地回去向陈友亮报信。
宋铁军一觉醒来已是午饭时间,他匆匆吃了点,就来到县党部上班。
马彪向他汇报行刑的地点,并把将要处决犯人的档案放在他的面前。
“坑挖好了吗?”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您下命令了。”
“记住,不准用枪,用铁锤敲击脑袋,然后埋了。日后共党倘若发现了,我们也可以推个干净。”
“好。张凤山怎么办?”
“现在他一家人在医院守着,咱们不好动手。这样,我让徐语晴在药里做点手脚,保准他活不过今天晚上。”
马彪离开了,宋铁军打开面前的档案,这里面都是一些铁骨铮铮的共党分子,他们或多或少地经历了严刑拷打,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至于在党内做什么工作或者知道党内哪些机密却只字不提,虽然他们有名字,宋铁军甚至怀疑这些名字都不一定是真的。
一个人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放弃名字、身份,甚至生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宋铁军看着这些名字,想像他们在经历酷刑时大义凛然的样子,不禁从心底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太可怕了,如果这样的人一多,他们势必如洪水猛兽一样无法阻挡,党国的大业将毁于一旦。所以,他要拼命的阻止这种情况发生,虽然精神上不能消灭他们,至少可以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宋铁军翻看着这些档案,发现一个人从体型上与张凤山很相像,年龄也相差不大,只是长相不同。这就是他要找的人,宋铁军松了一口气,昨晚上的计划就差这个人了,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宋铁军打开留声机,放起了轻音乐。
这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是钱院长打来的,向他报告张凤山醒了。宋铁军说了句“我知道了”挂断了电话,心想徐语晴这小丫头还真有两下子,她说病人今天下午能醒,现在果然醒了。
宋铁军急忙驱车赶往医院,他要和张福海见面,让他配合自己下一步的行动。现在张福海也成了他手中的一颗棋子,要摆布他很容易,毕竟这关系到他儿子的生命。
夜幕降临了,一辆轿车行驶在弯曲的山道上,驾车的人正是宋铁军。他驱车来到行刑的地点,这里是一个僻静的小山沟,没有人家,到处是荒坟乱冢。
宋铁军在树丛里停好汽车,从车上拿出一把铁锹,来到一处撒满杂草的地方,拨开这些杂草,下面就是松动的黄土。
宋铁军没费多大功夫就刨出了他需要的那具尸体,他将一切复原之后,扛起那具尸体来到汽车旁,将尸体和铁锹放进后备箱,然后驾车来到了华盛医院。
宋铁军没有走大门,直接驶向后门,钱院长和徐语晴正推着病床在门口等候。
尸体被放在了病床上,宋铁军说:“小徐,现在就看你的了,我给你一个小时时间。”
宋铁军重新回到县党部,他要等候医院的电话,然后再兴师动众前去。
马彪看见了他,跟着宋铁军进了办公室,向他汇报行刑的情况。
宋铁军故作满意地点头,然后说:“你现在把这些档案销毁掉。”
马彪将他桌上那些档案当着他的面一份份投入到火盆中。最后只剩下张凤山的了,他问:“书记长,张凤山的也烧吗?”
宋铁军说:“烧!刚才我已命令徐语晴动手,他活不过今晚。”
马彪将张凤山的档案投入火中,很快化成了一堆灰烬。
宋铁军打开一盒烟,递了一支给马彪,自己也叨了一支,马彪连忙替他点着。
宋铁军吸了一口烟,说:“最近怎么没看见陈友亮来啊?”
马彪说:“这老家伙,被那个聚仙楼的老板娘迷得神魂颠倒的,这会儿,肯定在她那里快活呢。”
“今天下午我去医院,张福海向我反映了一件事情,说陈友亮想讹诈他。”
“这老贼爱财如命,这种机会他肯定不会放过的。他娘的,如果上面同意放他,这种好事再怎么着也轮不到他呀。”
宋铁军点了点头,说:“是啊,当初我也有这个打算,为兄弟们将来的出路考虑。没想到张凤山突然畏罪自杀,这事就算黄了。正好上面要他的命,干脆咱们就成人之美了,弄成个术后并发症死亡,让张福海欲哭无泪,他要怪就只能怪陈友亮,人是他抓的,又没看好,造成这种结果,两人必定要掐起来,咱们正好坐收渔利。”
马彪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书记长这着实在是高。”
宋铁军说:“你跟在我后面慢慢揣摩吧,现在,你让人去把陈友亮找来,等会我要让他去收拾残局。”
陈友亮确实是在菊仙那里,他见宋铁军找自己,以为是让他去拿这笔钱,连忙屁颠屁颠赶过去了。
宋铁军正面对着墙壁上的那幅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出神,见陈友亮进来,笑着说:“陈局长,最近是乐不思蜀啊。”
陈友亮摸了摸秃了半边的头,不好意思地说:“哪里,让书记长见笑了。贱内身体不好,兄弟最近肝火有些旺,就到外边找人灭火去了。”
宋铁军拉下脸,说:“你闯下的祸不管不问,让我给你擦屁股屎啊。我问你,这两天你可去医院探望过张凤山?”
“书记长,我不是有苦衷嘛,张会长还算通情达理,就怕他家里人不好说话,我若到医院去,那不是自己送上门去自讨没趣吗?”
“那我活该替你去挨骂呀?”
俩人正在斗嘴,突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宋铁军抓起话筒:“喂,我是宋铁军。”
电话那头传来钱院长焦急的声音:“书记长,不好了,张凤山死了。”
“什么?死了?你们不是说脱离生命危险了吗?怎么又死了呢?你们等着,我马上到。”
陈友亮和马彪都听见了,两人面面相觑。
宋铁军说:“陈局长,你打电话多派人手,防止张家闹事。咱们一道过去。”
在特护病房门口,张福海和家人还在静静地等候,他看见宋铁军领着一大班人过来,连忙过来说:“宋书记长,您来得正好,这两天我要求见见儿子,可医院说是您规定的,在他没醒过来之前谁也不让见。我现在就想见见他,哪怕看一眼也行。”
宋铁军说:“张老,你现在可以见了。我刚刚接到电话,你的儿子已经过世了,请你老节哀顺变吧。”
张福海身体摇晃了一下,指着宋铁军说:“你胡说,我的山儿不会死的。山儿呀…”说完,捶胸顿足大哭起来。
徐语晴听到外面动静,将病房的门打开,只见病床上躺着一个人,白色的床单覆盖在他的身上。
张福海和家人发了疯似地扑了过去,哭得天昏地暗。
方香桂边哭边掀开床单,“山儿,让我看看你伤在哪里?都是那天杀的陈友亮害的,不然你不会死的,为娘一定替你报仇。”
陈友亮如芒在背,暗暗叫苦,心想这下惨了,在这里还不是等着挨打吗?找个机会溜掉吧,怎奈宋铁军还在场,如果他被打了,就要责怪自己保护不力,事情同样小不了。
在场的人都看见了死者的面容,只见他眼睛紧闭着,面如白纸,头部被厚厚的绷带裹着。
突然,方香桂惊叫一声,然后指着尸体说:“这不是我的山儿,他爹,孩子们,这不是山儿。我的山儿右手掌心有一颗朱砂志,是从胎里带的,这个人手里却没有。”
张福海和儿子、女儿停止了哭泣,过来一看,果然没有。
众人这一惊非同小可,宋铁军问道:“大姐,你确认不会错吧?”
方香桂肯定地说:“不会错,我的儿子我还不认识吗?不过,这个人长得确实很像我的山儿。”
张福海怒气冲冲地说:“我的山儿在日本留学,你们却说他是延安来的共党分子,把他抓起来。今天上午,聚仙楼一个叫菊仙的老鸨跑到我家,说她是代表陈局长来的,跟我开口要10根金条保山儿的命。哼,我要告你们拿一个冒牌货来敲诈勒索。”
宋铁军怒视着陈友亮,厉声问道:“陈局长,你做何解释?”
陈友亮吓得面如土色,结结巴巴地说:“这个我也不清楚,不清楚…他说他叫张…张凤山。”
“那金条是怎么回事?”
“是菊仙干的,我真的不知道。”陈友亮两腿直打颤,都怪菊仙这个贪心的女人,她一定是瞒着自己去了张福海家,胆子不小,居然开口要10根金条,这女人想发财想得发疯了,回头一定找她算账。
宋铁军对马彪说:“马科长,给我把这两个人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