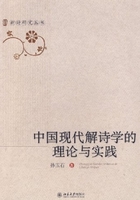旧中国盛行帮会,就是各式各类的民间组织。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青帮”和“洪帮”。黄金荣和杜月笙,就是有名的青帮头子。石城虽小,也一样有青帮组织。民间称为“海袍哥”,“海”读阴平声,是动词,“加入”的意思。作形容词时,是“很大”的意思,“他脑袋特别海”。类似北京话的“海去了!”袍哥在民间颇有势力,尤其在发生纠纷争斗时,在帮的人总要占些起手。关于袍哥势力的传闻,又超过它实际的势力。有个笑话,说是有个庄稼人进城卖柴,路过一家面馆,看见一个顾客走出来,店小二追上来要钱,顾客怫然道:“海了的!”小二连声道歉而退。农夫心里道:听说海了袍哥的吃得开,果不其然,连进馆子都不用开钱。第二天换了做客衣服,大着胆子进面馆要了碗鸡丁干粉,吃完抹抹嘴就走。店伙追出来要账,他学昨天那人怫然道:“海了的!”小二不相信又不敢反驳,悻悻而退。他得了甜头,隔一日又去吃,吃完就走。小二早已监视在侧,一把抓住他讨钱。他生气道:“跟你说海了的!”小二冷笑道:“昨天你说开了的,把我哄了,今天还想再哄我!”他道:“前天我明明听见那个客人说‘海’了的,你就不收钱,我也海了的,怎么就要开钱?”小二说:“那位先生说的是他‘开’了账,什么‘海’了的!”逼着他脱了做客衫作抵押,才放了他。
我有一些店员大朋友。关于袍哥的真假知识,就是从他们那听来的。帮里没有二爷,龙头大爷以下就是三爷。关公关云长才是二爷,谁也不敢僭越。帮会内分许多香堂,许多等级,许多规矩,绝对的小服大、下服上,以小犯大以下犯上是不赦之罪。如此等等,跟武侠小说里写的一样。“海”了的人有个标志:不论穿什么褂子(当然西服不在比例),袖口要翻出一道宽宽的白边。如果翻成马蹄袖形状,就是帮内有身份者,或是帮内要议论什么重大事情了。但我见店员大朋友们的长衫袖子,都翻出雪白的宽边,未必个个都是“海”了的。或许是像那个吃面不开钱的庄稼人,含含糊糊地给人以“海”了的印象(石城话叫“打麻画眉”)?有一次来了个气宇轩昂、说话非常圆通的人,走后有个店员说:“他是袍哥大爷哩。”另一个说:“他是袍哥大爷?总共有几个袍哥大爷哟!”对方就不吭声了。但显然反驳者也不知道共有几个。有一位年轻单纯,整天唱着歌做皮鞋的柏大哥,入了帮会做小老幺,兴奋万分。一次为了表示义气,勇敢地从一辆开行着的货车顶上往下跳,去为帮兄捡拾被风刮掉的呢帽,当场摔死在公路上。柏家悲痛万分,却不敢有一句埋怨的话。总之,帮会的若明若暗的存在,有关的种种描写和传闻,使它显得朦胧神秘,非常刺激想象力。
我有位长辈,喜欢热闹,什么新鲜玩什么。忽然想海袍哥,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且立刻行动起来,最后是正式“海”了或是在外围,我就不知道了。只见同事拿这个话题挑逗他,他脸红红的,笑扯扯的,莫测高深的表情。忽一日,他说有一个帮里小兄弟犯了事,闹大了,要在金钟山上开堂追究,到时候带我去玩。似乎是调戏了帮嫂或是对帮兄出言不逊之类的事。母亲听了坚决不让我去,这位长辈又轻描淡写地化解,极言无事。母亲便不言语。在我,是巴不得跟着去。我已经看过不少武侠书里的描写,知道这种开堂非同小可,犯事者总是残肢断手,挖眼割舌,甚至“自行了断”,还要慷慨陈词,声泪俱下,那场面悲壮得很。
到时候真的跟着去了。我小时候最欢喜放风筝,凡出城必带了去。这次自不例外。谁知金钟山高树蓊郁,浓阴迎天,这只“钟”裹满了铜绿。沿着弯弯曲曲的林间小石级,从山脚直到山顶,根本没有能容风筝飞上去的空隙,只好一直扛在肩上。
金钟山我上过多次。好像都是逢年过节,山顶的庙子里永远有许多人在办酒席、打围鼓(清唱川戏),热闹非凡。虽是很庄严的庙宇,办的筵席总是荤的。石城人除了持斋吃“二六九”的女居士,没有人喜欢吃素席。我第一次吃素席,发现鸡丁、盐菜肉、红烧肉全是假的,非常愤慨,觉得受了骗。这次开堂,可能为了肃穆氛围吧,没有人打围鼓。但酒席正在照办,鼻子耳朵都能知道消息。
我一个人在变得冷清清的大殿里玩,看那些讪讪地寂寞着的菩萨,幻想着从屋檐垂到地面的血红帘帷里藏着狐狸和鬼,想到寒毛奓起来,就逃到石院阳光下去。大人们在临市的厅堂里议事,讲话声音若有若无,一句听不明白。我微带战栗地期待着的厉声大骂、痛哭陈词,总也不见发生,更不用说下残酷的命令了。这样无味无道地挨了很久,大人们蜂拥而出。我暗暗观察谁最像当事人,只见有的若有所思,有的若无其事,有的满面春风,有的说说笑笑,仿佛都是局外人。但我还是选中了一位脸色红得有点失度的年轻人,用他填补好奇的空白。随即就热热闹闹开席了。
我见过这么一次帮会开堂。它有点像《红楼梦》中凤姐讲的那个笑话:一个极大的炮仗,引来许多人观看,忽然无声无息就走人了。不是没放,这个凑热闹人是聋子。
后来经历多了,觉得这个堂开得好。和为贵,不必上纲上线往死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