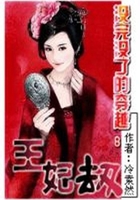萨玉儿带着匕首离开紫轩宫后,翌日便谴人将匕首和一纸书信送往韦孝宽的府邸。她早就知道,韦孝宽这个人不爱金钱名利,更不爱美酒美人,唯独钟爱古玩物件,对古剑兵刃更是颇有研究心得。
接到萨玉儿秘密送来的东西,韦孝宽自然是格外惶恐惊愕。这个平日里养在深宫之中的女人,在他眼中不过是个格外受宠的妃子而已,除了同各位大臣家眷交好之外,倒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如今,堂堂贵妃竟暗地给他送来这么名贵的一把匕首,着实叫他心底不安。
烛火映照下,韦孝宽仔细端看着青铜匕首,扭成一团的眉头在接到这个盒子之后就没舒展开过。他将自己关在书房三个时辰之久,只是反复摩挲着匕首,反复读着萨玉儿的信。
惊愕,不解,困惑,为难……各种复杂的情绪紧紧围绕着他。这个深宫里的女人,究竟要干什么?女人不得干政难道她不知道吗?如今竟这般堂而皇之地给自己送来这样厚重的礼物,信上所言虽然句句切中政治要害,字字掷地有声,如响雷般警醒着他,叫他这个朝中第一谋士也不得不对她的想法称赞。可他若如此,此事一旦败露,可是外臣勾结后宫干扰朝政,是诛九族之大罪。可是,他真的想不出比这个更好的法子来扳倒燕都,打击突厥要害了。
“玉贵妃啊玉贵妃……你究竟为何如此?这叫老夫,如何是好啊?”他叹息幽幽自言道。
手中的信笺突然滑落,飘飘忽忽地落在案几之上,烛光下的娟秀小字愈发清晰明了。
“韦大人,见信如晤,谅身份差异无法亲自登门拜访。自邙山战败,吾皇终日郁郁寡欢,玉惶惶不安。玉深知牝鸡司晨不可为,可玉更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今我大周外有突厥虎视眈眈,内有奸佞搅乱朝纲,大周社稷漂浮不定,如今情形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玉深谙韦大人治国之才,更知韦大人报国之忠,遂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修书一封,还望大人听玉一言。虽突厥远在万里之外,却牵我朝如病中之犬,突厥人凶残无义,想必大人早有耳闻。且突厥可汗燕都早有背信弃义之前举,必定不会信守成偌与我朝永久交好。为今之计,只有纵横捭阖,暗中怂恿可汗之弟他钵谋夺汗位,燕都之子必定群起而反之,扰乱其内,其则无暇攘外。有朝一日,他钵夺取可汗之位,则势必需要我朝鼎立相助抚平内乱,大周便可伺机夺取齐国之地,待平息战乱之后,突厥则因内乱而大伤元气,吾已日渐强盛,突厥何所惧?玉之陋见,愿大人思之虑之。萨玉儿亲笔。”
“借刀杀人,精之妙之啊!”他感叹道。
红烛再爆出一个烛花,快到元日了,韦孝宽眉头渐舒已心下已有决定,此事若做,则必定要一举成功!
弘圣宫中萨玉儿正欲宽衣入睡,宇文邕的龙撵便停在了宫门口。只见他满身落雪走进屋,本想顺手握住萨玉儿,刚伸出的手却又停了下来,苦笑道:“我身上的寒气还未退去,怕冻着你。”
她的心底瞬间温暖,微笑走到他面前亲手解下他身上的斗篷交给秀娘,然后拉着他的手走到暖炉旁坐下:“可用晚膳了?”
他眉目含笑嗯了一声:“你今日都做什么了?”
“外面雪下得大,躲在宫里看书了。”她一边摆弄着宇文邕的手指有一搭无一搭地说道。
“无聊了?”他轻声询问,眼中尽是宠溺的笑意。
萨玉儿皱皱鼻子微笑点头。
“过完年天气暖和一些,我带你出宫去转转。”
她没有应答,起身走到桌边斟满一杯热茶,似是无意间问道:“你什么时候出兵打齐国?”
他走到她的背后,冷不丁地将她抱在怀里耳语问:“怎么问起这个?”
“随口问问。”她转过身,将手中的茶盏递给紧贴着自己的宇文邕,他垂下眼瞧了瞧她手里的茶盏,虽是不大情愿可还是放开搂着她腰肢的手,接过茶低头细细品了起来。
萨玉儿故作漫不经心又试探问:“若是将来你打下齐国,然后准备做什么?”
“你想问我,是否会攻打突厥?”他斜眼望着他,眉宇间似是发现秘密的孩提般戏谑的笑意。
萨玉儿的脸登时变得通红,还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殊不知自己这点小算盘早就被宇文邕看穿。她放下脸上的笑意,努嘴低头看着脚尖。
宇文邕放下茶盏,弯下腰从下朝上望着她通红的脸,她心底有些慌乱急忙说:“我不是想干政,就是,好奇。”
“哦?是吗?”他故意拉长声音反问道:“你是不是很希望我会出兵攻打突厥?”
萨玉儿沉了沉气抬起头,他也站直了身子,嘴角饶有玩味地望着她,等待她的答案,她目光凌冽如冬日雪山上的冰柱,声音是从未有过的霸气:“没错,我希望你攻打突厥,恨不得灭了突厥才好。”
“玉儿……”因为她的坦然相告,反倒叫本想戏弄她一下的宇文邕感到心底微慌,他突然想起为何她会这样说,李娥姿的死她一定是知道了其中缘由。
“好了,你不必解释,我真的只是随口说说的。”叹口气后,目光黯然下来,萨玉儿欲转身离开,却被宇文邕一把拉入怀中。
“玉儿你听我说。”
“不必说了,将来的事情,谁都说不准的。”她抢着说道,脸上有些无奈。
“你……真的不想听?”眼里尽是询问戏谑地望着她。
萨玉儿淡淡一笑,牵起他的右手仔细摩挲观察道:“很多事情,是我想太多了,你的心我该明白的,你的难处我也该了解的。所以你不必再说什么,我都清楚。”说着,她低头微蹙着眉自言道:“这只手本是拿惯了刀枪剑戟的,如今却握着一支朱笔,看似轻松,实则那支笔却是一个江山的重量,这些年你可累了?”
宇文邕听闻此话,心底瞬间波涛汹涌,她竟这般知他懂他,他缓慢地将她拥进怀中,动作极轻极温柔,仿佛此刻他拥抱的是一件绝世瑰宝,“朱笔虽重,却不及你一二。”
“其实,我怨过你。”她伏在他的胸口,听着他有力的心跳低声道。
“我知道。”
“你将姐姐关在静心斋的时候怨过,娶阿史那玉儿的时候怨过,留在她那里几个月的时候怨过,姐姐病逝时怨过,赐死薛嫔的时候也怨过,这么多的怨早就该变成恨了,可是我却没有办法恨你,却是越来越多的心疼,越来越多的不忍。为什么会这样?”她低声垂问,似是在问他,又似是在问自己。
“对不起,我让你受委屈了。”
“你会替姐姐报仇,是吗?”她哭声问,抱着他腰际的手更用力了。
“一定会。”他的语气中有着不可置疑的坚定。
她的心才微微放下,有了这句话她才会安心,她是女人,即便宇文邕对自己再怎样钟情,她也无法坚信他不会对阿史那玉儿动心,不会对她手下留情。
那晚,她看着他熟睡的侧脸,伸出食指在他的眉毛上轻轻抚摸,不直接将除掉燕都的计划告诉他是碍于自己的身份,若此事是她所说,便是后宫干政。若是韦孝宽说出来,则是忠臣良策,是绝佳的立功机会。况且韦孝宽为人忠厚,值得信任。
白驹过隙,时如流水,转眼又是元日。今年的元日因李娥姿病逝,故而不得大举庆贺,各宫死气沉沉。得知萨玉儿突然失踪的消息,宇文邕发疯一般冲出麟趾宫,他命奴才挖地三尺也要找到萨玉儿。直到日落西山,富贵才在静心斋找到她。
佛堂里烛光昏暗,宇文邕不知她究竟在佛前跪了多久,那样虔诚认真。寒风从窗缝门缝中钻进来,屋内并未燃起炉火,萨玉儿的双手已经冻得通红,可还是执着地捻着佛珠。
发觉身旁有人后她停下转动的佛珠,睁开眼满目疮痍地望着蹲在自己面前的宇文邕。
“过了年,你便要强制推行灭佛一事,我想赶在此前替姐姐多念些经。”她幽幽道,眼角眉梢尽是让人怜惜心疼的愁思。
“先起来吧。”他叹息着搀扶起萨玉儿,因跪得久了双腿酸麻不听使唤,险些倒在宇文邕怀中。他揽着她的肩膀走向桌边坐下道:“灭佛一事并非我无情,只是如今出家者竟占了国家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不仅无需纳税,还要国家每年拨出一定的粮银补给,而且现在有不少出家之人为青壮年,他们不去参军报效国家,却要躲避世俗纷争,如此一来国家的负担极重。若想振兴社稷,灭佛势在必行。”
萨玉儿垂眸思索,并不搭腔,她知道宇文邕的决定不会因为她而改变,即便她不同意可是她却没有理由去反驳他。因为她是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看待此事,而他却是帝王,他心中所想的是江山社稷。
“他会如何处置那些人?会杀了他们吗?若是那样,他又和齐国昏君有何区别呢?”她在心底思忖着。
见她垂目面上尽是愁容,宇文邕紧了紧手臂道:“你放心,我只是希望他们可以回归平常人的生活,绝不会伤及他们的性命。”
他这样轻而易举地便看清了她的心思,叫她有些诧异更多的是感动,如此一来倒叫她对自己刚才的想法觉得惭愧,她怎能这样想他?萨玉儿深情款款地望着他如秋水般宁静的双眸真挚道:“我替周国的百姓谢谢你,将来他们一定会理解你的良苦用心,一定会感激你,更会知道你是个难得的明君圣主。”
“你这样说我会很得意的。”他挑挑眉毛毫不谦虚笑道。
萨玉儿忍俊不禁,转瞬却又无比认真地对他说:“利而无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予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此爱民之法也。”
他的眼色微敛,若有所思说:“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
萨玉儿愈发沉沦于他深入潭水的眼眸之中,见她痴迷而又含情脉脉地望着自己,宇文邕扬扬嘴角笑问:“你什么时候看的六韬,竟记得这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