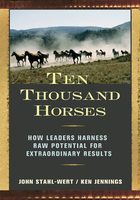家里充满了女人的气息。六个女仆很能干,在巧珍的带领下,把每座屋子都摆设得井井有条,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每个窗户还贴上了一对红色的喜鹊或鸳鸯。巧珍还吩咐怀英带领那些男仆在屋前和回廊的两边都栽上花草和树木,院子后面的山坡上种上了蔬菜,院子靠东墙旮旯里和西墙根下砌起了猪圈和鸡窝。十年后,正是巧珍的努力,赵家的家禽和猪羊充满了整个蓝镇的前山后岭,它们是那样的气势雄壮,以至于那些虎狼犲豹见了也恐惧地怀疑是不是上天一下子派下来这么多的家禽牲畜,是来把它们当作食物。赵俊生皱着眉头,半信半疑,心里却高兴,任由她们去搞。赵俊杰则高兴得像个孩子,在人们的眼里他和儿媳妇的关系就好像是姐弟。文清在家里没有干过一点重活儿,但她有一手好针线活儿,她舞弄的绣针就好像是燕子掠过水面那样轻巧,她还主动地担负起两个孩子的抚养。在孩子一周岁的时候,就已经误以为她是他们的妈妈。她教他们唱歌,还教他们礼节。两个小家伙活泼可爱,麻烦的是他们争强好动的性格。老大比老二身体瘦小一些,可吃亏的总是老二。每天傍晚,巧珍和文清都会端着盆子将一家人换下来的衣裤端到河边捶洗,那里的水清澈得就快赶上文清的眼睛了。直到这时赵怀礼才会透过河边的柳林仔细端详女人的长相。女人长得丰满而匀称,文静而又不失严肃,他心里打鼓,好像有未卜先知的预感——这个女人要么是自己的对头,要么就是自己最得力的助手。一天晚上,这种判断就得到了验证。女人把陪嫁来的箱子钥匙交给了他,他打开又不露声色地关上,然后把钥匙扔给女人。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一点用也没有,要你来不是要得到这些金子,是要你生孩子和操持家务。”
几天后,女人把钥匙又扔给了他。这次他没有拒绝,第二天趁女人去河边的时候,他依靠他超人的力量把箱子搬到父亲的房中。
父亲依然给朱成文赶车,但他很久没有看见这个老朋友的影子了。他对朱家灯红酒绿的生活抱着和儿子一样的态度,不闻不问不参与。好几次朱成文的弟弟朱成武出于热情给他准备了女人,但他在酒后的情况下压住火山喷发般的欲望,挫败了引诱。
“你可真是个怪人,”朱成武调侃他,“都像你这样,天下的女人还怎么活?”与他相反,弟弟赵俊杰在一次又一次的宴会中着了朱成武的道儿,并从此堕落了。他好说好笑好动的性格成了女人的焦点,他也因此寻找到了乐趣。哥哥对弟弟的所作所为不予理睬,只是当弟弟去和女人们寻欢的时候,他会独自坐在秀子的坟前,坦然平静地拔掉坟头上的蒿草,这时他的内心就会涌起独占女人的念头。直到有一天晚上,当怀礼说出要给他和弟弟提亲的事,他才惊诧不已,就是弟弟也因此终止了因荷尔蒙泛滥引起的游戏。
赵俊生在后山洼的松树下,端着烟袋坚决反对儿子给自己续弦的建议,因为他觉得巧珍的未婚先孕已经够离谱的了,现在要是再做出有悖于这里风俗的事,势必会成为这里的笑谈。但儿子的决定不容改变,儿子杀死老虎的目光使他屈服了。此时,他感觉到自己的位置与儿子互换了,好像站在自己面前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自己的父亲或者更为有尊严的长辈。他真的不能再等了,时间的流逝灼焦了他的灵魂,痛苦无时无刻不充斥着他的回忆,复仇的愿望随着儿子的长大膨胀得撑破了他的胸膛。夜里的月光与他叙述的语调一样愁惨,他说出了家族的悲惨遭遇。
怀礼坐了下来,静静地听着,即使父亲流下了眼泪,他也没有安慰父亲,就好像是他早已知道了这件事一样,与父亲共同感受侮辱与伤痛。
文清满月前三天的晚上,赵怀礼走进了丈人家。这与他第一次来丈人家的感觉完全不同,他感到丈人家阔气的住宅充满压抑和苦涩的气氛。虽然这里有高大的院墙,迂回的长廊,盛开的花卉,就连门廊上最微小的位置也雕饰着讲究的花草树木,但内院的深幽让他感到生活在这里的几十个人脸上泛着绿光,身上散发着腐烂的气味。这种死气沉沉的气氛被他归结为岳父没有人可以承接家业的缘故。岳父的三个儿子在他期待家族兴旺的关键时刻相继夭折,武松林和陈婆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没有使他再拥有一个儿子,他只得在哀叹命运的不济中接受现实。
岳父正陪着他的三个夫人打麻将,见他到来把位置让给了他,并吩咐仆人给他沏茶。他只玩了一把,就让给了旁边的仆人,然后退到屋子里和岳父谈来此的目的。当说起要买下蓝镇所有磨坊的时候,岳父沉默了片刻并提出了异议。
“那些磨坊可是朱家的呀!”岳父从棕色的椅子中挺了挺身子,站起来,来回踱着步子,“这些东西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呀!”
“他们和我已经谈过了,我也不想买,是他们找上门来的,他们无心经营,我没办法只得买下来。”
“需要多少钱?你说。”岳父还认为女儿的那一箱子金子没有告诉女婿,直接切入正题。
他从岳父家拿走了和文清陪嫁时一样多的金子,他的胆子那样大,只用半箱就把朱家所有的磨坊自作主张地卖给了自己。磨坊所有的管理人员一律不变,只是每月的月底他会亲自收取一个月的租金,然后把租金扔进自家的仓库。年底,清明道长做主褒奖了他。他得到了自家门前从大门口开始至蓝江边的五十亩贫瘠土地的耕种权,他拒绝了他自称没有名目的奖赏。他拿出了当年磨坊的收入,买下了另五十亩肥沃的土地。这个买卖差点成为泡影,朱家第一个反对的是朱建昌,因为朱家还没有卖过土地的先例,朱家永远享有土地的所有权的规矩是比蓝镇建立时还要古老。那阵子,他是那样的焦躁与和蔼。他回家睡不着觉,在地上蹲着学会了抽烟,跑到后山上喝酒,站在蓝江边上呆呆地看着流水。然而,第二天当他出现在朱家大院的时候,他的和蔼几乎令那些以往见了他就害怕的家丁们哭出来。他的笑容比六十岁老人积攒一生的笑容还充满温情,他的话语比叫春的狐狸还有诱惑力,以至于在半个月后他参加朱家的宴会并满怀真诚对曾经反对卖土地的朱家长辈宣布取消自己的荒唐计划时,那些人也站到他的一边共同反对朱建昌。他们不仅同意卖给他,而且价钱低得出奇,就像是在抛售急于出手的旧货。那时,在没有任何正式交接的情况下,便很自然地完成了他与父亲的交接,他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叔叔有什么事都愿意和他商量,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和这个侄子说,有一次他差一点就忘乎所以地把他和哥哥共用秀子的事说了出来。
“你花钱买那些东西干什么?”叔叔满脸忧郁地说,“怀明还在逍遥楼里呢。”
怀明是那样的不着调,他已经在逍遥楼住了有大半年之久。自两位哥哥成亲以后,家里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他借口为了工作方便搬到了朱家。凭着伯父和朱家的良好关系,他在朱家谋到了撰写菜谱这一轻松而实惠的工作。每天晚上那个罗锅儿管家把第二天的菜谱拿给他,他只需半个时辰即可完成和那些挥舞着大勺的厨师们一样多的工钱的工作。罗锅儿见了他毕恭毕敬,就像所有人见了怀礼一样。他的性格和怀礼完全相反,但长相却又出奇地相似。只是哥哥的眼睛冷静中充满威严,面部表情也显得冷峻,而他充满幼稚和不安分的眼睛即使他在以后生活的漫长岁月中也还是和现在一样没有改变。他的长相给人的感觉与一个记账先生没有一点相符。他继承了父亲的基因,是那样的好奇和随意。他粗手大脚,体格健壮,说话粗鲁,两颊长满了络腮胡子,头发支棱着像头顶趴着一只刺猬,冷眼一看就像一个下山打劫的土匪。他整天嘻嘻哈哈东游西逛,像是和所有的人都相处了比他岁数更久远的时光。他与认识和不认识的女人打招呼,然后油嘴滑舌地奉承女人,即使是长相比巧珍还丑陋十倍的女人在他的嘴里也会变成杨贵妃,而他却不觉得自己是违心和脸红。他给她们朗读赞美诗,这是他在写完菜谱的寂寞中想象出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诗的诗。没有一个女人不喜欢他,她们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看,给他糕点和糖果吃,给他自己都舍不得喝的冰镇草莓汁,给他量鞋码做鞋,甚至偷偷地塞钱给他,可他对钱没有兴趣。那些年轻的夫人和小姐把他当成活宝,教他跳舞,他领会舞步的要义比她们教的还快,而他又别出心裁的创造总能使舞步更加神奇。他狮子一样雄健的步伐,海豹一样滑溜挑逗的舞姿,鹰一样注视的眼睛,把那些跳舞的和不跳舞的年轻夫人和小姐弄得神魂颠倒面红耳赤。
“这小子是谁?”一天晚上他在舞会上大出风头,朱家的长辈问。
“是俊杰的二小子。”身旁的人说。
也就是在这个晚上,清明道长认识了他。道长高兴极了,他发现怀礼的这个弟弟比怀礼好玩多了。他要给怀明换个更轻快的工作,可怀明拒绝了,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够轻快了,没有必要再换。其实,他是舍不得对门罗锅儿的小妾。小妾比他大一岁,除了有一双流波的眼睛外其他方面并不出众,但这个女人在某一段时间里填补了怀明因盲动而空虚的胸怀。一天晚上,怀明喝醉了,女人扶着并引诱了他。他们一直折腾到天亮他酒醒,他才知道人为什么要分男与女。第二天晚上,他来到了罗锅儿家,女人正在给罗锅儿捶腿,他妒火中烧却不敢看罗锅儿。回到屋子后,他掀翻了账桌,发誓永远不理这个女人。可两天后女人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把自己发过的誓言全忘记了。一天,他趁着罗锅儿去工作的当口儿走进了小妾的房间。一个时辰后,他怀着愉悦的心情走出了女人的房间,这时他才发现罗锅儿抱着头坐在屋檐下的台阶上。他一下子就斩断了与这个女人的来往。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寂寞。他像蝴蝶一样穿梭在花丛之间,今天与管家的夫人睡一次,明天与家丁的老婆睡一宿,他甚至与朱成文的第二十八个夫人接上了头,但他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直到他遇见了朱建昌的贴身丫鬟幼儿,他才终止了这种危险的游戏。幼儿拥有着令人恼火的柔曼身材,唯一不足的是她的脸上长满了雀斑。他们是在舞会上认识的,与以前不同的,这次是他引诱了她。他们经常在库房里、院墙的角落里、花园的花丛中、阴暗的祠堂中乃至他的床上幽会,他们是那样的痴迷,以至于在热吻中被朱建昌带领的家丁包围还没觉察。幼儿羞愧难当,当天夜里就投井而死。朱建昌愤怒地要处死他,可他一点也不在乎。怀礼赶来的时候,朱建昌正吩咐手下把他绑在庭前的石柱子上。怀礼知道这个消息后,怒气冲破了他强健的胸大肌直至将蓝江的水面也激起了波涛。“进去的时候什么也不说。”他摸了一下腰刀暗想,“一刀斩下去,要他永远都干不成这样的事儿。”但当他踏进朱建昌的院落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也没看弟弟一眼,直接进屋坐在朱建昌的对面,静静地看着,那模样就像告诉所有的人——看你们谁敢轻举妄动。
建昌低着头,用眼睛的余光扫视着怀礼,好像做错事的不是怀明而是他自己。但他还是解释:“你知道,要是不杀了他,这样的丑事还会发生。遇上这样的事儿,你也会这样办。”
怀礼掏出烟袋点上,深深抽了一口,含在嘴里,烟便从鼻孔中冒了出来:“伙计,那丫鬟已经死了,杀了他也于事无补,不如把他交给我,我有更好的办法。”
“就在这里,”朱建昌嘿嘿地笑了起来,“这样我也可以学学你的好办法。”
怀礼从厅堂走出来,从刽子手里拿过大刀,挥手就要向弟弟的裤裆斩去。
怀明喊:“哥,你还不如杀了我。”
院子里挤满了人,那些闻讯赶来的女人个个面如土色。怀礼强硬的表情和他的心理完全一样,那一刻,他不是后悔自己的鲁莽来到这个是非之地,而是这里的气氛激发了他蓄含已久的能量。只是这种能量释放的对象不是弟弟,而是朱建昌,要不是建昌的母亲及时赶到,他会因为弟弟而牺牲赵朱两家的友谊。建昌的母亲在丫鬟的簇拥下走进庭院,所有的女人都跪下为怀明求情。
二十九夫人命令给怀明松绑,然后以极其严厉的口吻命令家丁用木棍将怀明赶出朱家大院,并声称怀明永远不得踏进朱家大院。
怀明遵守了诺言,但他是那样地怀念朱家大院的女人们,不得不在逍遥楼满足自己的愿望。不久,他的愿望得以实现,一些朱家大院的丫鬟和女仆们也因怀着和他同样的愿望来到了逍遥楼。
逍遥楼名声大震,不得不扩建,越来越多的女人们像鲫鱼一样从遥远的地方游来。余平以一个商人敏锐的目光抓住了商机,要兴建另一个逍遥楼,并决定聘请怀明去那里坐堂招揽生意,可怀明拒绝了他的聘请。武松林的药铺生意好得不得了,一天的收入是原来一个月的收入还拐弯。私塾的学生爆满,张先生那里的学生都坐到院子里了,他只得在露天里讲授课程。赵怀礼这时才意识到蓝镇已经大得没有边际了,而这里只是巨大蓝镇的一个中心点。怀明整天给她们唱歌,朗诵诗,谦和地教她们跳舞,他激情的宣泄激发得整个蓝镇都在发抖。赵俊杰痛苦得要死掉了,他为家里有这么个浪荡公子而没有颜面见蓝镇上的人。他冲进逍遥楼,还没见到怀明就被那里的女人抬出去扔在街上,他坐在地上不顾颜面号啕大哭,可怀明让里面的人送给了他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是跟你学的。他停住哭声,愧疚地在秀子的坟前默默地祈求地下的灵魂去劝说儿子能够回心转意。
怀礼走进逍遥楼,没有一个人敢阻挡,他与生俱来的威严把那些女人吓坏了,她们跪在地上不敢抬头,那时怀明正和几个女人在调情。怀礼把和自己一样高大的弟弟举了起来,目空一切地走出了逍遥楼,走出了蓝镇,直到蓝江边才放了下来。那里早已停留了两匹马,然后他命令弟弟上马。弟弟问他去哪儿。他回答:回家。
那是一条几乎没有希望到达的回家路程,可他们最终到达了。他们凭着父亲二十年中只凭着简单的记忆和卓越的想象以及对家乡的无限怀念和对家族强烈复仇的愿望绘制的一张没有把握的地图,踏上了父亲无法实现的征程。他们靠着这张后来证明是蓝镇通往家乡最捷径道路的地图的指引,以顽强的毅力和严肃的使命感一直向北穿越。沿途的女人们早已听说怀明的到来,在路边准备好了热茶和米酒,可他们看见了怀礼就再也没有女人出现过。
一路上两个人谁也不说话,怀明恨哥哥。他不看哥哥一眼,哥哥也没有向他妥协的意思。二十天后,他们的面前没有了官道,面临的是充满荆棘和乱石嶙峋的原始森林,怀礼杀死了比他们还消瘦的坐骑,割下了两条马腿在火堆上烘烤。就在这个晚上,他们喝了毫无言欢的闷酒,在森林边上的小溪旁宿营。半夜里怀明被一只觅食的老虎惊醒。怀礼在他还没醒悟过来时,便以惊天的吼声闪电的速度将老虎举到空中,轻轻一抛老虎便掠过树梢重新回到了森林中。早晨,怀礼把所有的东西挂在马身上,拔出腰刀在前面开路。他裸露着上身,砍那些丛林就像机器在割草一样。怀明跟在他的身后,思念着逍遥楼,就在昨天晚上哥哥赶走老虎后,他还在梦中与逍遥楼姿色最出众的小翠相会。一个月前,他答应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子去蓝江边钓鱼。女子已经向他很多次表露爱慕,要与他一生相伴,可他拒绝了。现在,他决定只要自己还能回到蓝镇,他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女子的请求,家就安在蓝江边上他们要去钓鱼的地方。一整天,他都迷迷糊糊,直到哥哥把吊床挂在树上,他才从梦中醒来,急忙卸下马背上的棉袄、棉被、咸菜和最后的一点大米,并把锅吊在两树之间点着了火准备煮些粥。
哥哥很疲劳,躺在即将衰败的荒草上,嘴里叼着烟袋,眼睛凝望浩瀚的天空,嘴里嘟囔着说,明天要下雨了。他碗口一样粗的手臂被树枝和荆棘划得血肉模糊,恼人的秋风把他本来就很凌乱的头发吹得像有一片原始森林在他头顶舞动。这天晚上,一只豹子企图趁他们熟睡的时候进行偷袭,可哥哥在酣睡中扭断了豹子的脖子。第二天,果然下雨了,他用眼神乞求哥哥是不是休息一天,可哥哥装作没看见。一周后,雨停下来,可他病倒了。这段时间,他是在火炉和冰窟中度过,心里比森林深处还阴暗。他梦见了他的伯母秀子,伯母坐在一辆马车上,穿着黑色的棉袄,用冰冷的手摸着他的脸,用温存的话语一次次地说:“哦,我的孩子。哦,我的孩子。”他叫着伯母,可伯母却让他喊妈妈。他的身体暖洋洋的,恳求伯母把他带走,要上伯母的马车,可伯母惊恐地把他推了下来,他就在呼唤妈妈的惊叫中醒来。他已不能行走,只得让哥哥背着他。一个月后,那匹马死去了,他看见了那匹马弥留之际渴望早些死去的眼神和哥哥忧郁的表情,那一刻他知道哥哥并不是铁石心肠。傍晚,哥哥从草丛中捡回几个鸟蛋煮熟,然后喂了他。他很奇怪,像哥哥这样粗大的手剥起鸟蛋来竟是这样的灵巧。
他终于和哥哥说话了,他告诉哥哥他冷。哥哥把所有的棉被全捂在他的身上,还在他身边拢起了一堆火。他出了一身大汗,做了一宿的梦,可一件也记不住。第二天早上,他认为他死了,可从地上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已经痊愈了。
哥哥把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只留下两双鞋和两把腰刀。哥哥扔东西的时候好像在表明一种态度,把那些棉袄棉被和铁锅抛得又高又远,末了还冲他笑了笑。两个人从此有了说笑,甚至哥哥和他还谈起了女人,他反倒觉得哥哥说话粗鲁。他给哥哥做饭,还跟着哥哥学起了武功。他很惊讶哥哥怎么就能把三尺多长的腰刀舞动得像缠在身上的银链,连人影也消失了。哥哥一招一式地教他,他进步很快,哥哥甚至夸奖了他的聪明。他要教哥哥舞蹈,反被哥哥臭骂了一顿,说他是不学无术,整天就玩些绣花枕头的玩意儿。这时他才知道,当初自己不与哥哥说话不是赌气,而是惧怕。一天中午,他们正在将一头刚刚猎获的獐子放在火上烘烤,突然听见远方传来的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他还认为是雷声,可哥哥说咱们就要走出这片林子了。
又经过了两天跋涉,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原呈现在他们面前。因为即将进入冬季,草原上的野草全枯黄了,那些奔腾在草原上的野马和野牛在狼群的驱赶下发出像闷雷似的轰鸣声。两只老虎正趴伏在那里啃食着一匹野马。三只豹子、一群狼和几只老虎从他们身前经过,它们不把他们当人,也没把他们当作猎物。只有一只巨大的黑熊站起来好奇地向他们望了望,然后向他们走来。怀明很紧张,可怀礼却笑了笑,迎着黑熊走去。人与兽在相隔十几米的地方站定,怀礼突然一声大喝,震天的吼声激荡得整个草原一片混乱,那些觅食的野兽迅速地逃进了森林,就像狂风驱赶着乌云那样迅速。怀明要逮住一匹野马当作坐骑,可是他失败了,因为他跑得没有它们快。怀礼看着弟弟失望的样子,被逗笑了,说不急,还有比马更好的坐骑。两天后,他驯服了一只老虎。他把老虎的嘴用树枝编制的笼子套住,这样弟弟就可以安稳地骑着它了。怀明高兴坏了,说世界上能骑老虎的人只有他们了。怀礼没有反驳,最近他发现他越来越喜欢这个弟弟了。第二天他又逮住了一只老虎射杀了一只山羊。他把羊皮剥下来扔给弟弟,因为天已经冷了。
两天后,他们在风雪中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期而遇。那些人见了两个骑着老虎的人,误以为是天神下凡。把他们让进帐篷,让他们喝酒御寒。那些人长着扁平的面庞,宽阔的肩膀,还拥有豪爽的性格。怀礼好像很了解这些人,用家乡的话和他们交谈,与他们大碗大碗地喝酒,还和他们比试了力气,最后他把两只老虎作为礼物赠给了头人的孙子。怀明与这里的男人和女人跳舞,这次他甘拜下风。这里的人跳起舞来,就像骤风从草原的草尖上掠过一样急促,而又那样的自然轻快。他们不得不留下来,因为雪一直下。兄弟俩每天骑马和那些牧民们一起吆喝着看管着牛羊,怀明还给他们唱歌。一个月后,怀礼和头人的二女儿柳眉结了婚。自他进入帐篷的那一瞬间,头人就以在大漠中赖以生存的直觉感到,这是一个自女儿出生以来就已经约定好了的婚姻。怀礼如实相告自己已经有了婚配,而且自己在此不能久留。头人满不在乎的劲头就好像是给母马找驹给公鸡配对那样平常。春天的一个早晨,当阳光普照大地雪水横流在草原的时候,怀礼携着怀孕征兆的妻子走进了头人的帐篷,如实相告了自己的家史。头人低头沉思片刻,便走出帐篷,一会儿头人的儿子柳成率领着十八个彪形大汉进入帐篷。柳成瞪着眼睛大喊大叫,声称要是不杀了妹夫的仇人,他就不回草原。要不是妹妹嫌他粗鲁,用眼神制止了哥哥的喊叫,他还会吵闹下去。
“你把他们都带上,”岳父说,“他们是我这里最好的勇士。”
秋天,他站在山顶看见了父亲生活过的房屋。那是一个破破烂烂的不能说是村庄的村庄,那些用泥土和茅草堆砌起来的房屋与蓝镇那些红砖绿瓦简直就是乞丐与豪富相比。那一刻,他皱起了眉头,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复仇的恶念顿时化作拯救的念头。
他独自打扮成乞丐徒步进入了村子。那是一个比山上看见的还要破败的村子,那里人的穿戴,即使他打扮成乞丐的模样也还是比他们风光,他不得不和那里真正的乞丐对换了衣裳。他披着麻袋片子赤着脚在人们的呵斥中观察这里的一切。他来到了一个牲畜交易市场,这里到处都是畜群的臭气,到处都是苍蝇蚊子,到处都是闹哄哄地粗鲁的吆喝和戏谑的笑骂声,唯一让人愉悦的是四周的参天古树和碧绿的野草。他挨了一个骑着马从人群中横冲过去穿着讲究人的马鞭,挨了一个女人的一顿臭骂,还挨了一个脸上长着横肉的卖马人的一脚。不过,他从这里得到了很多信息,这里依然是赵家掌握的,抽他马鞭的那个人就是赵家的大公子赵怀成。这个花花公子,他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赵怀斌。他们的爷爷就是杀死他爷爷和赶走他父亲的堂兄,可他们的爷爷在十年前就已经死掉了。他来到了赵家大院的门口,这里和他父亲描述的一点没有变,高高的围墙,褪漆的红色大门,门上带着两个大铜环,那对父亲曾经骑过的石狮子还是老样子,装饰几乎和蓝镇的家没什么两样,只是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好像并没有父亲说的那样兴旺。
两天后,他得到一个消息,家族因和相邻的李家村为争夺一座山的所属权发生了械斗,所有的男人都去了三十里外的飞龙山。天正下着雨,他返回山里,怀明用腰刀给他理了发,他蹲在山溪旁马马虎虎地修饰了胡须,骑上马便进入了镇子。在闪电中他把马拴在大门外的石柱子上,把蓑衣挂在大门上,手按着腰刀大踏步地走进了父亲曾经玩耍过的大厅,把一张家谱和一张画像拍在一个满脸忧愁的老者身前的桌子上。
他望着老者,一字一句地说:“我是赵家的子孙赵怀礼,我要见当家的。”
“你是俊生的儿子?”老者看了家谱,抬头审视着他,举起画像,“你回来晚了,他死了,现在我是当家的。”
他沉思一下问:“你是?”
“我比你爹大五岁,以前的当家人是我的父亲。我知道有一天你们会回来的。现在,你回不回来都没有用了,就在上午怀成和怀斌在和李家村争夺飞龙山的时候,战死了。”怀礼脑海里立即闪现出那个拿着马鞭抽在自己的花花公子,却想象自己要是在飞龙山的话,一定会征服对手。
“他们在家的话,你是进不来这个院子的。”老者说,“他们都是好汉。”
怀礼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没有任何表情地一招手,那些勇士手执弯刀片刻间将老者捆绑起来,然后把所有的女人和孩子都驱赶到院子里。
老者昂着头,但当重新审视怀礼时,开口说:“怀礼,你来做当家的,这是天意。”他说,“这不是因为我惧怕你,而是愧疚。”他加重语气说,“话说回来,当初要是我们不赶走你们,你们也会赶走我们,可能今天回来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他又审视一番怀礼后说,“你长得太像咱们的祖太爷。不过,你要当家必须遵守三个条件,一是保证我们家人的安全,二是保证我们祖坟的安宁,三是永世不得再提我们过去的恩怨,包括你后世的子孙都不能对我们复仇。这三个条件有一个不答应,我不会把整个家族的权力给你,我们将抵抗到底,我的家人只要有一个活着,即使是一个女人,也要你们这一枝人灭亡。”
怀礼走到大门口,一伸手把一只石狮子从深泥里拔起,举过头顶扔在地上。“我怕了你?”他说。但他还是答应了这三个条件,发了毒誓,并在几天后带领族人击败了李家村的敌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以极其强悍的身体和族人一起征服了凡是在这个地区能到达的地方所有山头、村庄和草原,这个结果是他父亲赵俊生没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