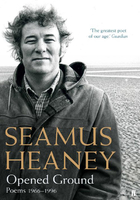墨珽不是第一次见瞿良邪着盛装,那时琏王兄才去世,所有人都沉浸在悲伤中,唯有她没有丝毫的情绪,就是这样一袭大红的制服端坐高位,那双眼直视前方若无物,正同她此刻昂首阔步朝自己行来一般,似乎没什么能阻止她的。
他眉眼一转,视线落在瞿良邪身边的男子身上,唇畔勾出一丝嘲讽的笑意,“眼看大钊江山易主,夫人却已经找好了退路,但真不辱没了才女一名。”
满目全副武装的士兵在瞿良邪眼中如若无物,墨珽这句嘲讽,落在她耳中也不过几个字,实在不足以在她心中泛起丝毫涟漪。一路行到营帐前,被账前刀斧兵拦了去路,方才眉眼稍抬看向账前将帅,“隆关风寒,到底寒不过饮血的冷兵,淳王是打算如此同妾身说话不成?”
墨珽挥了挥手,刀斧落下,瞿良邪向前一步,身后沁儿、珍珠及尘诺便被拦下。
“小姐……”沁儿急的惊呼一声。
瞿良邪回头看了三人一眼,又看墨珽,“没想到淳王是如此小心之人。”
墨珽冷哼一声,“同夫人一处,小王自当小心谨慎些,否则什么时候被你算计了去,滋味不大好受。”语毕,撩了披风侧身一让,朗声道:“夫人请!”
瞿良邪什么大阵仗没有见过,稍作停顿,便阔步入营,只看的沁儿三人一阵着急。
尤其是沁儿,淳王一直想杀了小姐的事她是知道的,此刻身在敌营,不得不万分小心。她悄悄拉了拉珍珠的衣服,低声道:“小姐若是出事,你我都不能活,等下无论发生什么事,你千万带着小姐离开,莫要管我。”
沁儿会说出这样的话在珍珠的意料之中,她却没有应话。她习得江湖套路,对付军中普通士兵,以一挡百不再话下,要护小姐安全也简单。但架不住明枪暗箭,何况眼下主子还在他们手上,分明是任由摆布的局势,实在有心无力。
尘诺也将沁儿的话听得真切,便料到一旦事发,这妮子必定要舍了自己性命,为她主子谋一条生路。不觉盯着沁儿细看,眉眼清淡,着的男装,束的发带,若说唯一一点有女儿家姿态的,是那张同她主子一般不饶人的粉唇。
似察觉到尘诺的视线,沁儿一转头,水灵灵的眼珠子转了转,竟不似往常一般对他怒目相对,反而柔了声色道:“王子既然愿意跟来,也定会助小姐脱困境的罢?”
她说话这般温和,尘诺反倒觉着不适,双手一怀胸,懒懒道:“你家主子一向本事极高,哪里用得着小王帮衬?”
明知他这话是故意呕自己,沁儿此刻却无力反驳,咬了咬牙,道:“你能跟来,也是同小姐约定了的,小姐若出事,你也出不了这里去。”
尘诺一挑眉,这妮子竟然也学聪明了,因有人来带三人去别的营帐,便暂时不与她计较,却也收敛几分玩闹心性,暗中加了小心。
瞿良邪心无旁骛入了营帐,只见帐中几名武将皆身穿铠甲,腰配利剑,神色复杂地盯着她看。
她在门口顿了顿,忽的回首看身后的墨珽,莞尔一笑,“妾身何德何能,等得淳王如此重视?”心下暗衬,墨珽做事向来敢作敢当,看这样子,他是打算将自己留下来,甚至连个马虎眼都没打算掩饰。
墨珽未答,径直入营帐就坐,叫了众将士都出去,方才凉凉说道:“你本是蜀地的夫人,本王自当送你回去的。”
瞿良邪行了过去,浓妆掩不了她眼中浅浅笑意,凉凉的语气却渗人的很,“你既认我是蜀地的夫人,是否也该尊称一声嫂子?”
墨珽嘴角歪了歪,这个女人面对千军万马不曾胆怯,还有心玩笑,真不知该说她是有勇气还是太蠢了。大战在即,他也无心与瞿良邪多费口舌,又凉凉道:“你既然来了,也就不用回了,若安分守己也就罢了。不知琏王兄有没有和你说过,我这个人一向怕麻烦,遇到麻烦的事,会用最直接的方法解决。”
瞿良邪抬首看了看营中的沙盘,款步落座,笑道:“我若是你,就不会将一个祸害留在身边。蜀地与殷都已经历了大劫,你这千军万马,委实不够我祸害的。”
她这话说的如此理直气壮,好像她是祸害一事,是什么值得为人道的。墨珽也不气,倚在摊着白狐皮毛的大椅上,眼眸微微合上,漫不经心道:“营中有何乱,随你来的三人性命不保。”
他知道这个女人不怕死,但她怕有人为她而死,所以她这一生才活的这么痛苦纠结。
瞿良邪淡淡一笑,环视四周,问道:“淳王连口茶都不让喝吗?”
墨珽气的乐了,好看眉眼蹙了蹙,嘴角却抿的更紧,没好气道:“没有。”微顿,又道:“瞿良邪,你入蜀是为自己,入都是为蜀地,那你来这里,又是为了谁?”
瞿良邪仰起头想了想,“入蜀也好,入都也罢,就算此刻站在这里,我同你心。”她起身,灼灼视线落在墨珽清俊面庞上,那一身银白的铠甲刺的她双眼生疼,声音却无比的坚定,“你杀我是为琏哥哥,救我也是为了琏哥哥,如今举兵造反亦不过是为他。墨珽,你说是也不是?”
墨珽眼中唯一一丝柔情被她问的消失无踪,面罩寒霜,连声音也冷了几分,“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他这一生没在意过多少事,唯有墨琏是他底线。
瞿良邪想了一肚子的话,要同墨珽讲,可此刻见他如此清冽的眼神,竟不知该从何说起?
若说自己对墨琏哥哥情深,那皇室中难能可贵的兄弟之情,又何等的弥足珍贵?
半晌,她忽的凄然一笑,迎着乍破的天光,那如凝脂一般的脸颊上,一寸寸地绽开了笑意。只是那笑如同瑟瑟秋风中独自飘零的落叶,飘的再高远,最终也归于尘土,收敛在嘴角处。
她说:“我大抵是没资格同你说那些话的,我们都是同样自私自利的人,我们没有一个让琏哥哥省心的。”
她这句话,却叫墨珽原本冷冽的眼神怔了怔,她说的如此无奈,如此伤感,与那身鲜艳浴血的制服格格不入,却偏偏入了他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