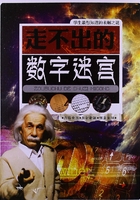“再讲一个吧,爹爹。”明儿靠着父亲的膝,两臂略略推动,父亲的身躯也轻轻地摇摆了。他那红润丰满的两颐,各有个浅浅的涡儿,在灯光里越显得美,覆额而剪齐的头发又含有可爱的潜力,使坐在旁边的母亲和祖母只是看着他微笑。假若父亲母亲祖母三个的心可以比作车轮的辐,那么明儿就是中心的轴了。
“再讲什么呢?”
父亲抚摩着明儿的头发,又托着他的后脑使更靠近一点儿;明儿的面孔就贴在父亲的膝上了。他的明净的眼睛从眼角里注视着父亲的嘴,好似父亲的嘴里有个可喜的世界就要涌现了。他说:“就讲地动吧。”
他还牢记着昨晚的事:那时候一家人同今夜一样,什么小鱼小虾是父亲嘴里的故事,又温和又甜美的是祖母和母亲脸上的笑,宁静得几乎什么都忘了的是明儿听讲故事的心。最先是母亲觉察,怎么身子有点儿摇动,桌上的花瓶也晃动了。随后便听得窗外有哗……的声响,房屋的骨骼也叽叽咯咯地响起来了。母亲才想到这是地震,悄悄地颤抖地说:“地动了!”于是父亲的讲说中止了。明儿的眼珠突出,瞪着不转动,虽然他并不知道地动是怎样恐怖的事。室内全然静默,只听得狂风似的声响在窗外的远空掠过;又觉得身体动荡,仿佛在惊涛骇浪的小船里。“我们下楼去吧,到场上去吧,危险呀!”父亲轻轻地说,但是他坐着不动,祖母干枯的脸上显出青色,似乎要说话的样子,上下唇动了几回,可是没有说出什么来。大概经过四十多秒的时间,地动才停止了。“什么呀。”明儿这一声打破了室内的沉默。大家才谈起地动来。恐怕它再动,不免引起忧虑。但是也没有法子;只得凭独断来互相安慰,以为绝不会再动了。祖母就讲她早年的经历:哪一年地动,招来了“长毛”;哪一年地动,入秋大雨四十天,田中颗粒无收。这时候明儿处在暂时被忘却的地位,静静地听着,也满足了爱好故事的欲望;并且学得了“地动”这个名词,体会了什么是“地动”。
“我就讲地动。”父亲执着明儿柔美的小手说。明儿注视的眼睛放出希望的光,似乎要将父亲所讲的故事立刻整个儿摄引出来。父亲开始讲了:“那一天地动,动得很厉害,比昨晚还厉害。一处地方有个塔,很高很高,几乎矗入云中。”
“比我们这里的方塔,谁高?”明儿曾经由父亲抱上方塔的最高层,父亲指着地面的行人叫他看时,他只是看不见,后来说看见几个苍蝇在那里慢慢地走。他因此认识了方塔。
“高得多呢,四个方塔那样高,四个。地面动个不了,那个塔便向四面乱晃,像个将要滚倒的陀螺。后来它实在站不住了,倒下来断成六段。塔就此坏了。来了个匠人,看见塔断了很可惜,愿意修好它。便去取一桶糨糊来,涂在每一段的断处,一段段粘起来。他做了半天的工,那个塔复原了,同先前一样的一个塔横躺在地上。太阳还没有回去的时候,他已将那个塔竖在原地方了。”
祖母同母亲都笑了。明儿听得出了神,身体一动也不动;听到这里,才咂着上下唇,像吃了好吃的东西似的,问道:“还有吗?”
“完了,没有了,塔已经竖在原地方了。”
“那么再讲一个吧,爹爹。”明儿说着,将上体竖起;小手从父亲手里褪出,拉着父亲的衣襟,表示恳求的意思。母亲顺着他的恳求说道:“再讲一个吧,讲地动时候的一个小孩子吧。”
这是他们的惯例,随便想几句话编成个故事,只挑明儿能够了解的或曾经经历的。明儿从去年秋间,他出生了三十多个月的时候起,就尝到听故事的好滋味,到今已有一年了。
明儿得到母亲的帮助,知道必能如愿,拉着衣襟的手就放下,他走到母亲跟前,背心贴住她的双膝,表示依恋的情态,仿佛给她的一种报酬。
室内充满了妙美的静默。父亲又开始讲故事了:“那一天也是地动,也比昨晚还厉害。桌子上的花瓶、水盂,墙脚边的痰盂,树上的鸟卵,宝宝的皮球,全都在地面滚个不停,好像活起来了。有一个孩子,他本来站在场上。地动了,他似乎脚下一滑,就跌倒了。不好了!他自己做不得主,身体只是一仰一俯地滚。他滚过了昆山,滚过了上海,再滚过去就是大海了。海面又平又滑,他滚得格外快,只觉得面孔刻刻着水又刻刻朝天。”
明儿的眼睛睁得比平时大了,似乎还在那里放大。他悄然说:“怎样呢?”
“他滚过了海面,又在外国的地面只是滚。好了,有一垛髙墙在那里!他给墙脚挡住,停了,不滚了。”
明儿的头点了几点,小嘴里呼出一口深长的气;同时他的背心贴得更紧,差不多全身的重量都支在母亲的两膝上。
“他躺在墙下,也不起来,像睡在床上一样。那边有碧绿的树,树下种些青菜,他以为就躺在自家的场上。一个人来了,来了。走近时,看见一个孩子躺在那里,就把他捡了起来。那个人有个口袋,很大的口袋,在他的衣服上。他把孩子放进口袋里,像捡得一个苹果一样。
“那个人到了家,吃过晚饭,看他的报。”
“还要写信呢,看书呢。”明儿提示他父亲。
“他看完了报,是的,写他的信。写完了信,看他的书。时候不早了,月亮快回去了,他解开衣服想睡。忽然口袋里的孩子叫唤起来。”
明儿好像进了恐怖的洞窟,脸上突然紧张,仰起来看一看母亲的脸。
“那个人才想起口袋里有个捡来的孩子,便取出来,问他道:‘你为什么要叫唤?’‘我没有吃晚饭。我要母亲。’”
明儿的小嘴抿着,下唇渐渐突出;眼眶里潮润了。可是父亲没有留意到他,还是往下讲:“那个人说:‘你就要回家是办不到的,你的家离得远呢!晚饭我给你吃。母亲呢,只好过几时再见了。’”
“呀”的一声,打断了父亲的讲说,明儿哭了。他的身躯尽往后退缩,似乎要逃出这最初的悲哀的包围以外。母亲便抱他起来。让他依贴在怀里,并且亲他的面孔。柔语道:“你的母亲在这里呢,你的母亲在这里呢。”
祖母也唱催眠歌似的安慰他道:“你的母亲在这里呢,你的母亲在这里呢。”
可是没有用,他哭得至于呜咽了。父亲急忙续讲道:“小孩说,‘多谢你,今夜送我回去吧!’那个人说:‘可以的,你先唱一支歌谢我。’小孩便唱了一支《种田牛》,唱得真好听。那个人听完了,取一张邮票,贴在小孩额上,把他交给邮政局。邮差当夜把他送到家里。他母亲正等着呢。他母亲抱起他,说:‘你来了,抱抱吧!’娘儿两个都快活得要酥了。”
“好了,他在娘的怀里了。”母亲催他止住哭,轻轻拍他的背心,这么说。祖母顺着说:“明儿,他已经快活得要酥了,你还哭什么?”
明儿的哭声停顿了;隔一会儿,又哭一声。眼泪滴在母亲手上,又滴在母亲的衣襟上,湿了一大摊。他的身躯还在抽搐,呼吸又粗又急,好似这最初的悲哀也就是永久的,已深深潜入他的心里了。
(1921年12月9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