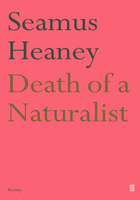1
奶奶夹起凉席爬上了平房顶,我抱着小枕头跟在后面。她铺开凉席,我扔下枕头赶忙躺下,背上却像火烤一样。
“奶奶,烫死我了。”我跳起来说。
“这丫头,房顶晒了一天,当然烫了,先坐一会,等下了露水就凉快了。”奶奶望着天空说。天空浑浊,像一片刚灌完溉、等待播种的田地。我们脚下是一片地,头顶还是一片。天空翻腾着蓝灰的云彩,几粒星星显现出来。它们像是播在云彩里的种子。
“你爷爷就在云彩里面看我们呢。”奶奶说。
“怎么会呢?爷爷又不是云彩。天上没有一块云彩长得像他。”我指着天空说。
“你爷爷火化时,我看到一阵白烟在烟囱口晃动几下,飞到了天上。他肯定变成了云什么的?”奶奶严肃地说。
“老奶,你是不是要疯了,人死了怎么会变成云呢?”我说。奶奶拍手大笑起来,“老奶是要糊涂了。”
“依儿,你想妈妈吗?”奶奶突然问。我看着远边的稻田里徐徐升起雾气,雾气很快掩去了远去的视线。雾一重,露水就要来了。
“不想。”我说。奶奶假装不在乎我的回答。
“你这丫头也是的,那回你爸妈要走,让你跟我去送送,你都不去。”奶奶有点责怪我了。我看着远边茫茫的雾气不说话。“你爸妈在外地确实也不容易……”我不愿意再听下去,打断说:“我知道。”
风带着水汽吹来,肩头湿湿的。凉席也冷下来。我轻轻躺下,背脊上很凉爽,像刚抹了一身爽身粉。等风大了起来,屋后的大榆树叶开始拍巴掌,哗啦哗啦的,像在说话。
“奶奶确实老了,前几天,我把你爷爷的照片随手一放,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了。”奶奶说。
以后的两天,奶奶时常念叨着爷爷的照片。我放学回来,堂屋里的柜子、箱子摆放的乱七八糟,奶奶蹲在大堆旧家俱里翻找爷爷的相片。她不管我了,我写完作业,脑子里刮一阵风似地想起屋后小树林里的铁罐子,那是我上星期埋下的,里面装着我最重要的东西。我想取出来,再看一看。我走到小树林里,站在草垛旁向太阳落下的地方走了五步,脚下踩到一块花岗石。就是它了。我双手扒开土,露出生了锈的圆盖子。
“簌簌!”草垛里传出动静,极细微的,但那是在草垛里,草垛是不会发出声音的。我走近侧着耳朵细细听,里面像是在啃苹果。我蹲在地上,头伸进草垛下面:一只肥大的刺猬蜷缩着,正在咬坚果,但并没有咬开,他感觉到有动静,眨着米粒大的眼睛看我,丢下坚果四爪后退几步。我伸手抓起那颗坚果,举起旁边的小石头块砸开。我捧着坚果仁摆在他面前,他伸长小鼻子嗅嗅,我把坚果仁丢给他,他慌忙地吞下去。看来,他肯定是饿坏了,所以没有逃走。我把口袋里的饼干屑翻出来撒给他,他伸出长舌头,在地上来回滚一圈,饼干屑就吃进肚子里了。
他爬出草垛,快速向大榆树窜去。我跟在他后面,他跑到榆树根下,回头看我一眼,窜进树根里,树根空隙里藏着树洞。他是窜进了树洞里。我拨开树根周围的狗尾草,洞口能伸进一条腿。我跪下好奇地伸手进去,膝盖一阵落空,狗尾草和土塌陷下去,整个身体像悬了空。
“啊!”我大叫一声摔了进去。重重摔在一个木槽里,我坐起身想看个究竟,可头顶上一个木盖砸下来,“啪。”木槽封闭起来,我蜷曲在木槽里,木槽中间空间大,两边越渐狭隘,像是桃核。桃核正坠落,我什么都看不到。我这是怎么了?我明明在屋后的树林里。等不及我思考,桃核渗进冷水,降落的速度也慢了,难道它掉进了水了。我要淹死了。我想。这时,桃核两边漏进少许的光线,我从裂缝处看到我正漂在水面上,水岸并不远,一个人站在河边,穿着湿漉漉的旧衣服。我用力推开头顶的木盖,竟推开了,我看清楚这里像是个阴暗的山洞,河两边是石壁我。掀掉木盖,对着岸上的人大喊。
“打扰一下,请问您能救救我吗?”
他转过身,平静地说:“这么快就过来了?”
“你认识我吗?”我问。他笑笑,我细看他的脸,和人的脸并不一样,鼻子弯而长,鼻尖是黑黑的一点。“你把手捧起来,用力划水,往这边划就能过来了。”我按他说的做了,等划到了岸边,他扶我上了岸,我看到他手臂上毛粗黑、刚硬,像刺一样。“你真像一只刺猬,身上的汗毛都硬硬的,对了,我刚才还追一只刺猬来着……”他反复看手臂上的汗毛,用手指戳戳它们甚至流出了血。
“我刚才追一只刺猬来着,怎么就到这里了?”我重复刚才的话。
“我就是那只刺猬。”他说。我吓得长大嘴巴看着他。
“不可能,你骗我。”我怀疑道。他瞪圆眼睛,全身用力,脸涨得通红,“叭叭叭”,他身上的汗毛根根直立起来,把衣服刺破了。这次,我相信他真是刺猬。
“刺猬先生,这里是哪儿?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恭敬地问。
“是我带你来的,这里是大树底下。”
“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
“你让我吃饱了饭,我要感谢你,所以想带你来见见我的主人,确切地说,是这棵树的主人。”
他走在前面,我小心地跟着,脚踩滑一颗石子,石子滚进水里,“扑通”声回荡在洞穴里响亮地怕人。走了半分钟,洞穴越来越小,走到尽头刚好有一人高。他推开石壁走进去。石壁相当于一扇小门。门内呼呼地漏出冷风,我站在门口犹豫不决。里面会不会有怪物,会不会吃掉我?奶奶说过,不要去陌生的地方,不要和陌生的人说话。刺猬先生回头看我,往洞穴里歪歪头。两条腿不听使唤地走了进去,里面沉睡着巨大的怪物,全身白色,他呼出一口气,迎面打在脸上。原来,刚才的冷风就是他的呼吸。他的身体占据洞穴一大半的面积,原本宽敞的洞穴显得窄小。
“主人?”刺猬先生低声说。怪物吸了一口气,一阵大风吹起我的头发,他的鼻息快把我的头发吸过去。他睁开眼睛,看看我。他的眼睛有我的头那么大,他用力地眨了一眼,又闭眼睡去。刺猬先生对我笑笑:“他就是这样,不要介意。”
“我想回去。”我说。怪物动了动鼻子翻过身,露出短短的尾巴,他伸出大手摸摸自己的尾巴,赶忙又把身体转过来,不让我看到他的短尾巴。
“回去?”刺猬先生说。
“我要回去见奶奶。”我补充说。
“难道你不知道吗?来到这里,你就回不去了?得一辈子待在这里。”
要一辈子待在这里?那我就不能上学、不能见到奶奶、不能……反正,我不能待在这里,想到伤心的地方,我就哭起来。刺猬先生把尖尖的手指放在嘴边,示意我不要发出太大声音,否则会吵醒怪物。但已经晚了,怪物轻轻睁开眼睛,坐立起来,我被这情景吓坏了,但是我一哭开,短时间内停不下来。他“哼”了一声,一步一步走近我,洞穴在微微颤抖。他站在我的面前,蹲下来,我正好能看到他大屁股后面垂下的短尾巴,他用手摸了摸短尾巴,挪了两步,直到我看不到他的短尾巴,才低头看我,两只和我头一样大小的眼睛一眨一眨的。他的眼睛里像藏有一潭河水,河里有贝壳、龙虾、还有几条小鱼。
他的眼睛更加靠近我,我担心里面的河水会流出来,要是流出来,那些贝壳、龙虾什么的就得倒在我头上,我紧张地缩回身子,他忽然张大嘴巴,像要一口吞掉我。
“啊!”
……
2
“这孩子怎么趴在树底下就睡着了?”外婆说。
我朦胧地醒过来,一揉眼睛,眼眶里溢满泪水。我睁开眼:树林还是树林、草垛还是草垛。洞穴、刺猬先生、怪物统统不见了。外婆两手叉着腰、板住脸,活像一只正在量角度的大圆规。“全身都弄脏了,又要洗啊涝的。”
“外婆,你快看,这下面有个树洞。”我打断她,指着树根,我快速掸开上面的树叶。可树叶下面却是一层湿漉漉的泥土。
“乱说什么?树根下面怎么会有树洞呢?”外婆说。
“有,土下面就是树洞。”我弯起手指刨土。外婆一把拽开我,“脏不脏?你看看你的手。”指甲缝里塞满泥土,甩也甩不掉。
“快跟我回去洗一洗。”外婆说。外婆拉我回家洗了手。我抹了肥皂,手上冒出七彩的小泡泡。
“外婆,我真的没有骗你,下面真有树洞,洞里还有很大的怪物,打个哈欠就能把人吹跑。”我洗去泡泡说。外婆根本不理会我,拿来干净的衣服命令我穿上。
“外婆,他跟我说话了,他还有自己的名字。”为了引起外婆的兴趣,我撒了谎。
“名字?说来听听。”外婆果然中计了。
“名字……名字叫哇咕噜。哇咕噜、哇咕噜。”我随口说。
“哇咕噜?还真是奇怪的名字。他没问你的名字?他没问你上几年级?”外婆不怀好意地问。我错了,外婆压根没有相信我,而是嘲笑我。“哼!以大欺小。”我掉过头不愿理她。
“外婆的好依儿,走!咱们去看看你的树洞。”外婆扛起墙边的铁锹鼓足力气说。
“外婆,你要做什么?”我忙问。外婆不出声地走向屋后,我跑着跟上她,她乐呵呵地站在大树底下等我。
“外婆,你这腿上是不是安了火箭了,走得那么快。你忘了你是老年人了吗?”外婆不在意我的话,扶住铁锹仰天看着大树,树足有三层楼房高,树叶浓密,宛如在空中支起一张大锅盖。外婆扔下铁锹,绕树走了两圈。
“这棵树35岁了,今年。和你妈一个年纪。这是一颗榆树、老榆树了。”外婆摸着长满皱纹的树皮说,“我怀你妈妈时,还是去村东老铁头家要来的树苗。”
“Hello,树妈妈。”我神气地说。外婆逗笑了,“来吧,看看这里有没有树洞?”外婆挥起铁锨铲下去,几锨以后,还是湿泥块。“你看,我说的,没有吧。”
“怎么会呢?我明明看到这里有的?”我说。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要是在梦里,看到的就是梦里的东西。”外婆的话简直像脑筋急转弯。我“嗯”了一声,跟她回去了。
外婆把凌乱的家具挪回原位,没有找到外公的照片,她失落落地坐在电视机旁。“这死老头子不想见我了。”外婆嘴里嘟囔一句,摁遥控器调了几个台。电视屏幕上雪花花的,看不清人的轮廓。
“这电视是不是坏了?”外婆说。
“没有,外婆,你看别的台看,这个台不清楚。”
“别的台?我要看中央台,中央台都收不到,电视还不是坏了?”
吃完午饭,外婆骑上她的专用三轮车,上街修电视去了。等我一鼓作气把周末所有作业写完,窗外的光线稀薄了,能透进屋里的很少。眼前昏昏的,外婆还没有回来吗?都这么久了,她是不是掉进路边的河里了?我想着害怕起来。一定是车子冲进了河里,她及时跳下车,但又看到自己的宝贝电视掉进河里,于是跳下水救电视,河面上“咕咕”冒了几个泡泡,最后平静了。我心慌了。
我锁上门,沿着上街的路寻外婆。走到村东头,四个男孩子在草堆旁放鞭炮,他们把啤酒瓶戳进草里,点着了炮仗塞入瓶子。“咚!”一声,瓶子没有坏,瓶口徐徐冒着白烟。接着,他们塞进两个、三个炮仗。我的心思全在外婆身上,我躲过他们,往街上跑。路尽头,外婆推着小三轮,大摇大摆地走回来。
外婆还活着。我跑上前去。“外婆,你是不是疯了,这么晚才回来,你不要我啦?”我问。
“要、要的,路上遇王奶,叫我去看牌了。今个手气不错,还赢了五块钱,走,给依儿买辣条吃。”外婆说。我爬上三轮车,抓住外婆的肩膀,“驾!外婆,快骑、快骑!”我抬头大声喊道。不远处,亮起一团火。
“哪家电灯那么亮,都照到路上了。”外婆蹬着脚踏板说。
“不是,外婆,是草堆着火了。”外婆猛劲蹬了几脚,三轮车急急地往村头草堆赶去。草堆旁散落着啤酒瓶的玻璃碎片,三个男孩吓得跑掉了。外婆下了车跑去村里喊人。火苗吞咽着干草,爬到了草堆顶部,风一吹,它借势跳起,舔舐着草堆旁腰细的树苗。树皮发黑了。村里的人还没有来。
远边高挑的树枝上蹲着巨大的黑影。黑影跳上细长的枝丫,巨大的身体竟没有压弯它,黑影纵身跳上另一个树枝,树枝随风摆了摆,黑影也跟着摆动。黑影连跳了六个枝头,往这边飞来。我终于看清了。
“哇咕噜?”我说出声。他轻轻飘在空中,笨重的身体随风浮动,他瞪圆了眼睛,笨笨地站在我身旁。他斜着眼珠看了我一眼,又惊慌地转过头。他张开巨大无比的嘴巴打了个哈欠,揉揉眼睛,眼睛里的河水汹涌翻腾,河底的龙虾连翻几个滚。他注意到我在看他,他抿住嘴、正经地看前方,小鼻子噏噏喘着热气。
“你能救火吗?”我问。火几乎包围了树苗。他用力眨了一下眼睛伸手捧起我的手,举到他的肚子,他闭上眼,动了动鼻子。一颗苹果大小的眼泪从眼眶里流下来,正好滴到我的手里,重重的,热热的。眼泪里还游着一条小青鲤鱼苗。他睁开眼睛,嗅嗅鼻子。看到我手里还有一条鲤鱼苗,惊讶地张开大嘴,眼睛直愣愣地看着那条青鲤鱼,鲤鱼苗翻了白眼,像是死了。他小心地蹲下来,用两个手指尖夹住鲤鱼苗,高高扬起头,像滴眼药水一样把鲤鱼苗放进眼里。青鲤鱼一翻身醒了过来。
他看着我,指指天空。“你是让我把眼泪扔到天上吗?”我问。他又眨了大眼。我把眼泪抛出去,他仰天举高长臂,眼泪沿着手臂方向飞向空中消失了。火还是很旺,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哇咕噜,火还很大。”我说。他打了个哈欠,晃晃大脑袋。
空气里飘起雨雾,肩头湿漉漉的。水雾打湿了哇咕噜全身的软毛,他张大嘴巴大喊一声,雨雾变得稠密而强烈,像扬起的冷沙。火渐渐收回了触角,火花匍匐在草堆上。
“呜哇。”哇咕噜又大喊一声,雨雾交织在一起,像蚕茧,网罗住整个草堆。
“灭了!”我说。
哇咕噜瘫坐在地上,喘着粗气。他索性闭上眼睛,躺在地上静静地睡着了,他身上的蓝色逐渐萎暗,变成淡蓝。我抱住他的头,他头上的软毛褪去颜色透明了,紧跟着全身也透明了。雨水穿过他透明的身体。
“哇咕噜。”我低声说。村子里的人赶过来,他早已溶化进空气里,就像水溶化进水里。雨停了。
3
外婆插好电源,打开电视。银幕上还是满眼雪花,电视没修好,外婆瞅了瞅。“啪。”她拍打电视顶,里面“吱吱”一响,画面就清晰了。人的鼻子是鼻子、脸是脸。
“看外婆真厉害。刚才还真奇怪,怎么就下雨了呢?还是太阳雨,下得那么巧。”
“外婆,那是哇咕噜的眼泪。”我解释说。
“这丫头尽瞎说。”外婆说。
“就是,就是,我亲眼看到的。他眼里还有几条鲤鱼。”
“谁眼里长鲤鱼啊?”
“就是,好几条呢。”外婆不理我了,两眼盯着电视机。电视正中间站着手拿话筒的人,他带着安全帽,站在工地上。
“有什么好看的?我要看动画片。”我说。
“你听,是说工地上死人了,从脚手架摔下来的,还是两个三十多岁的少年人。”
“外婆,三十多岁还叫少年人吗?”我问。
“三十岁的人对我来说,就是少年人,我都活七十多年了。还不能管他们叫少年人?嗯?这是哪里的工地?”外婆扒在电视上看字幕。
“外婆都是老瞎子了,下面那么大的字,苏州。”我说。
“对了,是苏州。看我老太婆这眼。”外婆重复道:“苏州?”她回过脸严肃地看我,我脑子里闪电一般想起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苏州?妈妈她们就在苏州工地上。”我说。外婆呆住了,两秒钟的瞬间,她从脸上挤出一点笑容说:“没事,前天我还给你妈打过电话,她还说工地老板管吃管住。肯定不是她们那个工地,你想苏州是大地方,不得有十来个工地。”我心里紧成的绳子松弛了一些。
“可是新闻上说是今天啊。”我转念一想。“走,我有办法。”外婆走到电话旁,揭开巴掌大小的电话薄拨了电话。“嗯?怎么是姑娘的声音?你妈号码变了?”外婆说。
“我听听。”我接过话筒,里面说:“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打不通。这是怎么了?”我说。之后又打了两遍,同样的结果。外婆安慰我说是手机没电了。我心里空荡荡的,不敢有什么不好的念头。睡觉前,我打开田字格本子,在上面写了很多话,我最想说的话。写完后,外婆睡着了,我轻轻撕下那两页纸,取了手电筒,推开房门,摸黑走到屋后,蹲在草垛旁五步远的地方,那里藏着我的铁盒子。我挖出铁盒子,抠开盖子,把纸折好放进去。
大榆树旁站着一个黑影,我并不感到害怕。“哇咕噜,是你吗?”我问。我打开手电筒,照过去。哇咕噜倚在树上打着哈欠,但是他的个头像缩了水。只有原来三分之二的大小。我抱着铁盒子跑向他,他呆呆地看我的铁盒子,又看我。他大眼睛里的鲤鱼也在看我。
“你怎么了?怎么变小了?”我问。他抬头看看天,又指指眼睛,张开嘴磕了一下整齐的牙齿。“我明白了,是不是下午降雨了,你累了才这样?”我问。他眼里的小鲤鱼跳出水面连连点头。我走近他,握住他的毛茸茸的大手,他低头蹭蹭我的头。脚下裂开一个树洞,哇咕噜抱起我,我把头埋进他茂密的软毛里,他的软毛像是晒了一天太阳的棉被,暖烘烘的。我睁开眼睛时,我竟站在他的洞穴里。他的洞穴里简陋地只留有一小堆干草。我放下铁盒子,坐在干草上。他挨我坐下,身体正经地直挺着。
“你知道吗?我担心爸爸、妈妈。”我说。他转身看看我,摇摇头。他并不知道爸爸、妈妈是什么。
“爸爸、妈妈就是生你养你的两个人,你有爸妈吗?他们在哪里。”我问。他遥遥头,眼睛里的河面又泛起波涛。他停住了,猛地睁大眼睛,指指眼睛里的河水。
“河水怎么是你的爸妈呢?”我问。他指指自己,比划出桃核大小的圆圈,又指指眼睛。我基本明白了:他还是一颗种子的时候,是在河里长大的。等他长大一些,自己有了法力便把那条小河藏进自己的眼睛里。时刻可以看着它。
我大胆地把手伸进他的眼睛,在河水里摸了摸,一只龙虾扫弄着长须挠我的掌心,痒痒的。我缩回手。他搓搓眼睛,指着我的铁盒子。我打开铁盖,拿出里面所有的纸。
“这些都是我写给妈妈的信,我把心里话都写在纸上,我想寄给她,可是外婆说他们经常搬家,没有固定的地址,信寄出去也收不到的。我写好了,就埋在铁盒子里,没有人会知道。”我说。他指着我的信。
“你想知道我写的信吗?”我问。他点点头,我把信一封封打开放好。我读了两封,眼睛湿漉漉的,我扬起头眼泪倒流了回去。我深呼吸一下,继续读后面的信,读着、读着,我情绪激动了,眼泪忍不住漫到脸上,我抱住哇咕噜,把头埋进他的软毛里。
“我想妈妈。我好担心他们,电视上说苏州那里的工地上出事故了,也许、也许,他们会死掉……”我小声说。
“哇!”一声。我听到一阵瀑布般的轰响。我抬起头,哇咕噜长大嘴巴,正大哭起来,他眼睛里源源不断地往外淌水,一泻而下,三个喘息的功夫,洞穴里积了三厘米深的水。小鲤鱼、龙虾都倒进了水里,他们在水中欢快地游泳。我摇摇哇咕噜的大手,他收住了哭声惊奇地望着那汪水。他从干草里站起来,淌进水里,鲤鱼苗围着他的大脚游来游去,龙虾用两只大钳子夹住腿上的长毛往上爬。我擦干眼泪看到他身后的小尾巴耷拉在水里,游摆着。
“哇咕噜?”我说。他站在水里没有回头,像在思索什么。我踩进水里靠近他,他的双手正用力地揉肚子。我侧身看他的肚子,他注意到我,也跟着转身不让我看到。
“你肚子痛吗?”我问。他回过头,兴奋地指肚子。他的蓝肚子上多出了一个空袋子,就像袋鼠的育儿袋。“是你变出来的?”我问。他点点头。他抱起我放进袋子里。里面暖暖的,像个烘房。我踮起脚尖只能把头露出来。他低头看我,他的眼睛清澈透明,河水没有了、鱼也没有了,只有一粒黑瞳仁在里面晃荡。
他的软毛变长覆盖了整个袋子,身子一缩,飞跳起来,穿过了洞穴,跳出土壤,飞到半空。从软毛里窜出头,我惊呆了,他飞升到榆树顶端,脚尖稳稳地踩着一片嫩榆树叶。他大喊一身,大风从地面刮起,筛着树木的枝枝叶叶。一卷风没头没脑地撞到大榆树上,掐断了哇咕噜脚下的叶子。他踩着叶子乘风飞起,又是一卷劲风,把他吹到风浪的尖头。
“你要去哪里?”我大喊道。他摸摸我的头,指向南方。“你要去找我的爸爸妈妈吗?”我追问道。他使劲点点头。风摩擦着耳朵,仿佛要生出火花来,他越飞越高,眼前飘过薄薄、凉凉的雾霭,眼底下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星星的灯火,有时一簇一簇、有时一点一点,像在地上看漫天的繁星似的。不远处,一架民航飞机引擎“轰隆隆”地往西飞去。“哇咕噜会知道我爸妈在哪里吗?”我透过软毛间隙看他,他神情紧张,要做最后的加速。
风扑抢着呼吸,我喘不过气来,只好把头缩回袋子。我抱着腿蜷缩起来,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睡着了。刺耳的轰鸣声吵醒我,我爬出袋子,哇咕噜站在工地旁的树阴里,塔吊正吊起数十根钢筋往移动机身。轰鸣声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工地东面搭起两排帆布棚子,他们一定在里面。
四周没人,我踩着满地沙子走到帐篷前,借着微光从缝隙里看进去。走近第五个棚子,我看到了他们。他们身底下只铺了两层报纸,身上盖一条旧毛毯,鼻息很轻,外面的噪音竟然没有吵醒他们。三角形的帐篷里只容得下他们两人,没有桌子、没见椅子,他们的衣服、安全帽、打饭的瓷碗放在腿边。我多么想摸一摸他们的脸或者干脆躺在他们中间抱住他们,可是我不能。哇咕噜站到我身后,用大手抱住我,我屏住哭泣声,眼泪在脸上肆意地流淌。
“哇咕噜,他们没事,我们该回去了,我们……”我哽咽着,说不出话。
“哇咕噜,你能不能,”我深呼吸,“你能不能帮帮他们?”我看着他清澈的眼睛,“他们,”我抽泣了,“他们太……太苦了。”哇咕噜摇摇头。
“对不起,我,我不应该,”我擦去眼泪,“不应该这样要求你。他们是大人了。”我哽咽住,喉咙里像卡了水糖果。哇咕噜把我抱进袋子里,飞升起来。我哭着昏睡过去。
4
外婆叫醒我。整个枕巾都湿透了,我的半边脸垫着冷冷的枕巾睁开眼,外婆端来米粥放在我面前说:“今天早上,你妈打电话过来了,她说到了国庆节就回来。她说昨晚手机没电了才没接到。”我下了床大口喝完米粥,赤脚跑到屋后。大榆树上的绿叶像掉头发似的纷纷落下,一些较细的枝干也“嘎嘣”一声,随风摔下来。我站在大榆树底下,树根里阔开一口树洞,刺猬正努力往外爬。
“刺猬先生?”我说。他爬上来,带我走进地洞。“刺猬先生,你刚才要干什么?”
“我要离开这里了,”他遥遥头说,“这里就要倒塌了。我得搬走去寻我二叔,他那里还有一个窝。”
“为什么要搬走?这里不好吗?哇咕噜对你不好吗?”我说。
“哇咕噜?哦!我明白了,这倒是个好名字。主人对我当然好了,是他收留我,我才能在这里搭窝的。”
“那为什么还有走?”
“你还不知道吧?主人是这颗大榆树的精灵,他帮助过很多的小动物。可是,主人永远睡着了。我想他这一次是真的累坏了。”
“他睡觉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刺猬先生推开石门,河水带着小鱼、小虾流出来,等到河水流完,我们走进去,里面空空荡荡。
“哇咕噜呢?”我问。刺猬先生指着干草堆,草堆上有一颗发亮的树种子。“早上,我看过了。主人……”
“那种子就是哇咕噜?”我飞跑过去,拿起那粒种子。
“主人每次消耗一点法力,身体就会变小一点,要是法力用过了头,他就会死掉。”刺猬先生说。
“哇咕噜是为了帮我才这样的。”我说。我心里酸疼,想到昨晚在空中飞翔的哇咕噜,他明知道自己会死的,为什么还要答应我?为我这样的小女孩牺牲自己值得吗?我那渺小的愿望值得他去牺牲吗?我的眼泪又来了。
“刺猬先生,我该怎么办?”
“我也没办法,咱们快出去吧,这里就快塌了。”刺猬先生说。我把种子装进口袋和刺猬先生道了别。
榆树一天天老朽了,主树杆一截一截往下掉,枝头原本翠绿的叶子一夜之间枯黄了,外婆找来砍树的人,他们用锯条锯断树根,开来卡车装走了。村东老铁头来找外婆谈了柴火的事,他扛起一把长柄斧头,一下一下把树桩砍成木片,塞进蛇皮口袋里,背回家引炭炉。地上留下一个很大的坑。
有一天,不知道是谁打开了天上的水龙头,雨降了一天也没有停歇,外婆又翻箱倒柜,突然,她叫我的名字,她手里攥着一张爬上霉点的旧照片。照片上是她跟外公结婚时的合影。她欣喜地想要找地方,把照片藏起来。就在那一刻,就在外婆转身的那一刻,我抱起大把长铁锨,疯跑进雨里,在院子墙边挖开一个小坑,我从湿透的衬衣口袋里掏出那颗种子摊开手,种子滚进坑里。我用一层松土把种子埋起来。
夜里,亮堂的月光滑进窗户照醒我,我抬头看窗外,雨已经停了,院墙边长出一人高的嫩芽,我看到嫩芽底下站着一个黑影。我穿上拖鞋跑出门,那个黑影傻傻地对我笑。
“哇咕噜!”我大喊着,扑上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