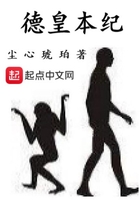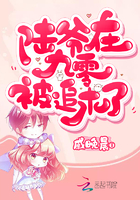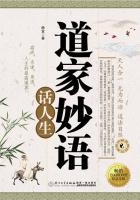很久以前有一个关于园艺的民间故事,它把野草定义为“长在错误地方的植物”。这对于我们理解儿童为何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特别引人注意带来了启发。具体而言,儿童要不就是处于早就规定好的空间,即被放置在如幼儿园或学校,要不就是由于不恰当地或过于早熟地侵入成人领域而显得引人注目:父母的房间,爸爸的椅子,酒吧,甚或是穿过一条拥挤的马路。
我们可以大胆地作出这样的定义,即童年就总是处于错误空间的人生阶段。
尽管任何社会中的任何人都会受到地理和空间的限制,不管这种限制是通过慎重的计划、隐秘的控制还是政治性的禁令施行的,但我们认为,儿童对于这些限制的体验都是特别矛盾的、通常无规则的,更是不稳定的。从社会空间而言,儿童是被定位、被隔离、被疏远的,他们在广阔的成人空间的偶然出现,也只是作为一种奖励或特权,或是渐进主义者所说的成长仪式的一部分。
正如阿查德(Archard,1993,第29页)在讨论现代西方童年的文化“隔离”时所说:
阿里耶斯至少发现,现代观察童年的方式的最重要特征是把它与成人世界分开看待。儿童的本质是独特的;它明显清楚地把儿童和成人区别开来。儿童既不和成人一起工作,也不一起玩耍;他们不参与成人的法律和政治世界。
维崔普(Qvortrup,1995a,第191页)也同意这一观点,对他而言,现代童年的矛盾之一就是当“成人一方面认为儿童和成人在一起很好,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成人却把儿童排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之外”。尽管如此,本章将要揭示,儿童遭到成人生活中的规则特别是政治的无情的约束,使得他们被牢牢地限定在他们的特性之中。
这确实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它的存在就建立于冒犯之上,它的基本的学习就是通过对它的约束而实现的。但是这是一种通过考察儿童参与社会空间而获得的对童年的理解,一种通过空间关系的权力实证主义创造出的可恶的行为主义者视角。根据第一部分中所讨论的前社会学童年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在弗洛伊德式的回忆故事中人格是如何被创伤所歪曲,儿童出现在未经许可的地方如何发生令人震惊的事。我们被告知,如果父母在不可冒犯的成人场所发现了儿童,他们很可能会变得歇斯底里,并出于保护儿童的需要而禁止他们再次进入。
这种对禁止的强调和前社会学对儿童的另一种观点似乎相反:在启蒙时代的观点中,儿童生来是自由的,充满了一种探险者的先天的主动性。正如卢梭建议的,以及20世纪晚期自由主义所鼓励的,如果儿童的能力是天生的,那么他们应该被允许获得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的自由,他们的开创精神必须得到鼓励。当然,这里仍然潜存着禁止。身体的、观念的、道德的界限限制着儿童漫游的程度。从已经关闭了的家庭空间到无限广阔的网络空间,都已经预先设置了界限来限制儿童的活动。这种界限由成人统治者所建立,通过纪律实施,并通过照顾、保护和隐私等意识形态获得了合法性。
所以,关于童年空间所需要探索的中心问题是控制。我们着眼于三个空间背景———学校、城市和家庭———这里要探索的是每个空间是如何通过纪律、学习、发展、成熟和技能的管理方式来控制和规范儿童的身体和心灵的。这些空间通常被教师、父母和同伴群体看作传统的、结构化的社会化场所,我们要对它们进行批判性分析,儿童可能会逐渐认识到他们所处的空间的性质与特定的控制模式的紧密关系。很明显,例如,学校、餐桌、操场、街道和儿童自己的卧室都具有共同的要素,但具有不同的性质。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场所随着时间发生变化:餐桌转化为绘画的地方,卧室成为惩罚的空间象征。但是,这种安置的转移主要是成人的特权,儿童感受最多的是不断的约束。因此,童年的空间和时间(见“童年的时间性”一章)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空间如何像时间一样塑造儿童经验,以及如何将童年自身的空间结构化,在结语中,我们将预先提到在后面的章节中对身体的讨论(“身体与童年”一章),我们会询问,是否童年的心灵空间现在也已经变得顺从(insubjection)了,因而使儿童的主体性也受到限制。
这种双重意图在普仁德加斯特(Prendergast)关于精神、身体和社会空间对童年的控制的分析中就已经能看出端倪。她在经验数据的基础上论证说,青少年女孩对于月经的意识和适应不仅是一个与她们经验有关的情景化问题———例如,在学校,月经的到来会成为一个让人尴尬蒙羞的事件,因为会涉及卫生保护,或是被获准不去游泳。更关键的是,这是一个形式上的因果关系(formalcausality)。学校这一空间实际上塑造了身体经验和有关性与性别的认同(见“身体与童年”一章)。所以,普仁德加德特(Prendergast,1995,第360页)的研究展示了一个学校、教育、社会和物质的空间如何塑造年轻女性在这一时期的自我意识和身体经验的具体的例子。学习发生在许多层面,特别是在无意识地学到正统的、看似自然的、内化了性别的层面,其核心就是那些被认为是恰当的女性特质的东西。同时,这个“天生的女性”身体的观念,和学校中致力于塑造它的过程,反映出一个西方社会中关于赋予成人女性现实价值的关键矛盾。
因此,在我们讨论与童年相关的问题时,社会空间从来都不仅是个中立的位置概念;前社会学讨论“儿童”时所说的来去自如的花园是不存在的,那只是成人的幻想而已。这种浪漫的华兹华斯式的对“一片已逝去的国度,一个我们过去的生活和过去的文化”(Pattison,1978,第58页)的想象,在新童年社会学研究方法中没有位置。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必须把童年解释为一种与现代的、复杂的全球劳动力分工相联系的社会空间,正如梅西(Massey,1984)所说,资本家生产的过程在空间体验中变得非常明显。将童年放置在这个背景中具有某种意图。结果是,儿童对这种意图的空间体验形成了未来的公民。正如厄里(Urry,1995,第13页)所建议的:
空间性……的涵义是多方面的,除了有区域的涵义外,还包括距离、运动、联系、特征、感知、象征和意义:用现实主义者的术语来说,空间对于社会实体(如阶级、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父权制)的因果力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显然,儿童这一现代西方社会(更不用说全球社会了)掌握权力最少的群体,潜在地受到这一现实实践的改变,但我们对他们的体验了解得还很少。因此,现在对童年空间进行思考(如童年社会地理学中已经开始出现的)正逢其时(Matthews,1992;Valentine,1996;forthcoming;Loweetal.,1993;Sibley ,1995)。史密斯(Smith)和卡茨(Katz)(1993,第67页)曾经论述道:
通过在社会和文化理论中再次重申空间的意义,一个完整的用于理解社会现实轮廓的空间语言浮出了水面。这种对空间和空间概念的兴趣的复苏具有广泛的基础,它部分地是对过去一个半世纪主导“西方”社会思想的广泛的历史相对论的一个回应。它是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批判地理学(criticalgeographic)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明确目标,是结构和后结构分析的中心组成部分,是信息理论的核心。最近,空间为许多女性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提供了非常有吸引力的概念,也为更广泛的文化讨论提供了语言(grammar)。
本章认为,童年的社会理论必须也要出现这种空间的语言和政治学。
学校化的儿童
当婴儿进入蹒跚学步的幼童时期,身体的改变带来了一种转变,一种新的独立活动的身体风格形成了(见“身体与童年”一章),这加大了他们接触电炉的可能性,或是再晚些时候,加大了他们接触网络色情或成人谈话和亲密行为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童年的社会空间也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童年的时间性”一章将要谈到,对于儿童个体而言,年龄的增长如何增加了他们进入社会空间的可能性,以及按照卡瓦力克(Kovarik,1994)的观点,我们因此能从空间和时间紧密交织的“舞台与剧本”的角度来将童年的经验的建构概念化。舞台和剧本———主要是家庭、学校和同伴群体———不仅带来与儿童环境相关的“在哪里”和“何时”的问题,也带来了“什么”和“如何”的问题。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学校的空间/时间的剧本作为我们的重点,考察它们是如何为儿童建构起童年的机构的。
在大多数西方社会中,儿童都有义务在学校中度过一定时间,学校为对数量众多的群体进行聚焦的精细化的管理和控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学校为儿童向成人身份转变提供了安排好的时间通道;同时,他们对儿童如何度过每一天也作出了限制(见“童年的时间性”一章)。在这种规划中,分析的单元并不是作为建筑或机构的学校,而是作为社会过程的“课程”,是它推动了作为正式组织的“学校”的产生,并为其赋予了意义。课程策略性地将空间、时间、地点、内容、联系、孤立、隔离、整合和等级结合起来,设计出儿童在学校内的总体经验。尽管对于课程的常识性看法会导致我们把它视为教育机构中的主要学习活动———但在这个意义上,课程和工厂的生产或办公室的工作不同,———仅仅以一个特定环境中的“人们做什么”来定义一项活动,就会忽略这种活动的目的。也会忽视这种活动被建构成被认可的形式的原则。
因此,我们认为,课程不仅仅是内容的描述。它们是认知发展和身体发展的空间理论,因此,它们包含了世界观(Young,1971),这种世界观从不是偶然的,当然也不是随意的。它们包含了挑选、选择、规则和规范,所有这些都与权力问题、个人身份问题、人类本性和潜力的哲学相关,所有这些都是特别针对儿童的。在这个意义上,课程是社会和政治的产物,它含有关于人们(主要是儿童)最好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假设。从历史上不同的观点来看,它们是累积性的、稳定的、促进性的和拒绝改变的。组成课程的知识是人类从世界上选择出来用以控制世界的实例;它的模式和风格的重复和复制,是通过将儿童的身体和意识建构为一种教育身份形式进而控制他人的实例。
因此,对于学校课程的分析使我们可以在童年的社会空间中开始对控制问题的研究。
任何课程的核心组织原则都是时间表,时间表本身是对经验政治的高度编码的空间化。例如,伯恩斯坦(Bernstein)关于教育知识的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章(1971)就将课程看作时间的正式分段(formalpunctuationoftime),具体化为“一堂课”、“一门课”或“一节课”。在这个意义上,各门课是活动的空间单位,它们通过时间分隔开来。伯恩斯坦告诉我们,每个独特的单元中所发生的就是课程内容,整个课程可以被定义为将单元和内容建立起正式关系的原则。这样就可以从内容角度,以及从它们的时间/空间分配角度来对单元进行分析。如果为每项内容增加必修或选修课程的特点变量,它们各自在儿童教育生涯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就会显现出来。
因此,一个儿童的教育状况———是“成功”还是“失败”———从某种程度而言是长时间通过课程进行时空控制的一个功能,按照福柯(Foucault,1977,第149—150页)的说法,它其实和时间关系不大:
时间表是一项古老的遗产其严格的模式无疑是由修道会提供的。
它很快就得到传播。它的三个主要方法———规定节奏、安排活动、调节重复周期———不久就出现在学校、工厂和医院中。新的纪律毫无困难地出现在这些旧形式中。学校和贫民院往往是附属于修道会的,因此沿用了修道会的生活和节奏。工业时期的严峻长期保持着一种宗教气氛。17世纪,大工场的规章规定了工作日的活动……但是,甚至到了19世纪,当工业需要吸收农业人口时,他们有时被组成“教区”,以使他们习惯于工厂的工作。“工厂———修道院”的构架被强加在工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