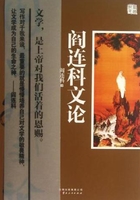下雨了。一直在听着窗外的雨声,期盼的雪久久未至,江南的冬天却似秋般的缠愁,静静地看着照片,回忆那年西行的点滴……
火车出了嘉峪关,却不知道自己高原反应竟那样强烈。躺在卧铺上,耳朵有阵阵刺痛迫入大脑,攒起的眉尖疲惫了旅途的行色。这一次西北之旅,加重了心中痴念的沉,车窗外戈壁的荒凉布满萧瑟的原野,纵是八月,边城的景色也无斑斓的多姿。
经过陕西的沿途,黄土高原上的沟壑是一片苍黄的色彩,低矮的山前有窑洞并列,一些景色被高像素相机摄入,和多年印象中记忆重叠,从而衍生了无限感叹。西部,除了荒凉,还有没有摆脱的贫困。
犹记那年暑假,你只身重返边陲,去继续深造未完的学业,似乎忘却当年离开时那片土地给你留下的苦涩。百川凝练,天山挂雪,埋藏一段纯纯的清恋把自己放逐在寂寂的草原。从塞北到江南,时间的距离里,虔诚的目光把天涯一次次丈量,鸿雁传书的青涩如何写得出青春的圆满?爱情,终被扼杀在频频遥望的天边。
远处,赤岩般的山峦扑入眼帘时,西游记里的火焰山已在眼前,过了哈密列车在这里转了个弯沿塔里木河继续南下。丘陵、戈壁构成了大西北无垠的空阔,曾经是亿万年前湛蓝的海洋什么时候变成了广袤的沙漠,而这一切一如你离开时的心境,少了生命中苍翠的葱郁。伫立的山形沉卧了梦的安静,而多年后给我今生意想不到的讯息,让这个季节有我万里奔波的重逢。
细心地捕捉着窗外掠过的景色,忽视了针刺般的头痛,低矮的红柳和芨芨草在车窗外飞速倒退,“井”字形的防沙坡有序地排列在铁路的两旁,偶尔隐现的塔里木河在蜿蜒的曲折中若隐若现。当一片干涸的胡杨出现在前方,心竟激动得加速了跳跃。胡杨林,你无数次和我说起的胡杨林,就是眼前这番枯苍么?
你说,无际的沙漠上只有胡杨才是这片土地的脊梁,“活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朽”,即使没有了生命依然傲立苍穹。当某日我驻足于胡杨林中才明白你曾经对我描绘的细碎。那造型古朴,写满沧桑的树干,纵然干裂枯萎,当一场雨润泽后的春天,树梢上有娇嫩的叶芽冒出。这样的不屈与顽强和你年轻的生命一样,任风沙肆虐,骤雪铺天,心中那团火焰总是蕴藏着春天的盼望。
飞舞的风沙中,古老的龟兹国伴着楼兰姑娘屹立了多少年?岁月的长河中,谁见证了你干涸的生命随塔里木河的流域在沙海上蜿蜒不屈?时间可以把胡杨变成了一个凝驻的标本,而你在离开江南那个小镇的时候,天风一样地席卷了你的苍绿。念你,是有惜无怜的灼痛,只是你依然把生活的信念挂于苍鹰的翅上,不倦地盘旋。
三月烟花堤岸柳都是记忆的旧景了,季节切换后的秋天远赴西域,我想象着你这些年来边城的岁月和容貌是不变的如初还是令人心痛的憔悴。十年弹指一挥间,所谓天涯真的就是一个无情的字眼儿。你像停留在塔里木河边的一只离群的孤雁,把忧郁的失落远遁在黄昏的落日里……
大漠孤烟,那条长河被时间断流,一条独木舟上的骨笛,吹不出阳关三叠。
年少的情怀总萌发天真的怀想,无力把你挽留在水乡泽国,只能用誓言把青春的理想装点,曾约定毕业后一同奔赴最向往的城市,天涯的寒会在未来的春天驱散。等你在山水蒙烟的静处,如麻的心思是日记里厚厚的落痕。
守着那份盟约,十年的眸光就这样守望着几千年来商贾不绝的丝绸路,守望着风卷流沙,孤烟万里的玉门关……
再回西域,放弃天空的飞越,只想有更多的时间把经年的点滴梳理,平息心中忐忑的躁动。当夜幕笼罩了车窗外的苍茫,黑暗中,我多年的遐想随旅途延伸。你的容颜是否蘸满了岁月的霜华,眉间收敛了张扬的稚嫩,再展于眼前的一定是娴雅从容的淡定。
思绪依然带我前行。走过库车,越过三千里的南疆,雄浑巍峨的托木尔峰出现在天际,你的远方我用跋涉逾越天涯的距离。雪峰辉映下的高山湖畔风吹草低见牛羊,我们的身影徜徉其间,而那些日子多了亲情却无形中拉开了距离。淡淡的笑声溢满旷野,却无法定格成想象的画面。古龟兹国的神秘,在长河落日的塔里木河畔,夕阳只把我们的身影拉长……
秋离,冬至,繁华落幕,记取少年心,空瘦有凭。我的国度不再有风沙的凌虐,春风温润了苍白的失望,唇间的一抹明艳,就是我今生倾醉的血酿。
离开你,离开你的城市,塞外的风撩乱发的柔顺,空旷的站台渐渐远成一个点。无法打开车窗,只能把脸挤在冰冷的玻璃窗上,初识在江南,校园的笑声不绝于耳,曾以为那一切是今生永远的停留,却不知道那年告别后定格成最后一笑。踏着西行的足音整肃青春的记忆,亲情蠢蠢欲动,写不尽的苍凉只有关山月照我天涯。披一身旧时明月照亮心中久久的昏暗,共有的记忆写成今生遥远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