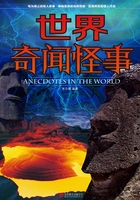一九一二年春天,曼殊住在上海了。此时我在上海七浦路租屋居住,曼殊和朱少屏都来同住过。我们白天同在太平洋报社办事,晚上还到七浦路睡觉。我们的同吃花酒,就在此时,大概每天都有饭局,不是吃花酒,便是吃西菜,吃中菜,西菜在岭南楼和粤华楼吃,中菜在杏花楼吃,发起人总是曼殊。有一天,有两个穿洋装的广东人,到太平洋报社来找曼殊,后来听曼殊讲,是他的异母弟兄。我现在想起来,—个一定是苏墨斋,还有一个,也许就是《答萧公书》中所谓穆弟吧。曼殊从杭州还到上海的日子,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但总在旧历二月廿日以前的,在这一天的《太平洋报》上,登有曼殊的《南洋话》。到二月廿三日,报上又登有曼殊住在编辑部的消息,可以证明。二月廿四日,他又到杭州,三月初二日才还上海。三月十四日,同孙伯纯等还去日本一次,四月十一日,仍到上海。还去的时候,我有一诗送他,他在日本时,有《与叶楚伧柳亚子朱少屏书》两通。曼殊重到上海后,即发表《潮音跋》及《断鸿零雁记》于《太平洋报》,刘三曾因血统问题,提起质问,曼殊含糊其词,这是我同陈佩忍两人亲耳听见的,佩忍还同我讲起油瓶的话。曼殊曾把一张日本女人的照相给我看,叫我往报上发表,问他是甚么人,他不肯讲,我替她题上了“东海女诗人”五个字,铸铜版登出,此照相铸版后被曼殊讨还,至今不知下落,也不知那“东海女诗人”究竟是谁。还有一张曼殊自己的西装照相,我也拿来铸版登报,题的是“东海诗人苏曼殊”八字,我对他讲,可以同“东海女诗人”凑成一对,他微笑而已。五月初五日,曼殊东渡日本,随后我也还到乡下去了。(曼殊起初的计划,似乎是四月廿三日星期六就要东渡的,后来偕马小进到华泾刘三家中去住了几天,所以直到五月初五日启程东渡,初六日过长崎,有明信片给刘三。)七月中曼殊寄我—信,拆开来一看,不是给我的,我就寄给胡寄尘,在《太平洋报》发表,这一信就是壬子七月《与某君书》,题目当然是我替他加上去的,所谓某君者,究竟不知是甚么人,后来也没有问明白。信中所讲的丹凤山、珠帘瀑、玉娘湖、沙陀江、樟溪、枫峡等地,我去问在日本住过近十年的老留学生,都说不知道,此信所讲的话,颇有小说风味,和《天涯红泪记》中的一部分相类似,我有些断不定他的是真是假了。九月中有三信给我,都不很长。他九月底到上海,住在英租界大马路一家客栈,名叫第一行台,我曾去看他。此时叶楚伧也正从北京还来,大家在上海欢聚,我的《海上杂事诗》中,有一首云:“东海骑鲸苏学士,朔方屠狗叶参军。归来心绪浑难说,付与西风怨夕曛。”讲的就是他俩了。曼殊说“难说”应改“无着”,但我没有依他。后来我匆匆还去,曼殊在上海住到旧历十一月,和郑桐荪、沈燕谋同赴安庆。在安庆时给我的信很多,我约他旧历年底到桐荪的家里来玩,他欣然允诺。到学校放了寒假以后,他果然和桐荪同到盛泽,还约了朱少屏偕来,我也先在盛泽等他,欢聚了几天,他就到上海过旧年去了。
一九一三年旧历正月,我到上海,曼殊还没有走。有一天晚上,曼殊在花雪南家请我吃花酒,少屏和楚伧都在,还有陈英士。这一夜就是宋钝初北上之夕,英士没有吃完,便匆匆先走,他说要到车站上去送别。谁知明天看报纸,钝初被刺,国民党右派想利用老袁来解决政治问题的策略,完全失败,中国的大局,从此又一变了。我先还乡下,曼殊二月中仍偕桐荪、燕谋赴安庆,三月又偕来上海,和燕谋同住第一行台,桐荪则往来上海盛泽间。此时似曼殊又到过盛泽一次,住有半个多月。四月中旬,曼殊再到安庆,但三十日又还上海,五月初二日同燕谋到盛泽,廿二日到苏州,住乌鹊桥滚绣坊七十二号,这便是桐荪老兄咏春的寓庐。曼殊在此与桐荪、燕谋同编《汉英辞典》,至六月底完成,又赴上海第一行台,一直住到旧历十二月,方还日本。曼殊在第一行台时,大吃花酒,直吃到裘敝金尽为止。十月中我曾到上海,去看过他一次,此时他忙于吃花酒,通信很少。到十二月还日本后,通信忽然加多,在一个月中间,有《与柳亚子书》七通,《与刘三书》六通,《与叶楚伧书》两通。
一九一四年旧历正月至二月,通信亦多,有《与柳亚子书》四通,《与刘三书》五通,此后通信就稀少了。从旧历三月到年底,曼殊没有和我通过信,刘三处也没有。但他有《与邵元冲书》四通,《与邓孟硕书》三通,时间是旧历七月到十一月。这一年曼殊大概常在日本。
一九一五年旧历三月,曼殊有《与郑桐荪柳亚子书》一通,《与柳亚子书》两通。四月有《与邵元冲书》四通,五月有《与柳亚子书》一通。以上各信,都是在日本发的。旧历五月以后,我们又得不到他的消息了。这一年大概他仍在日本。
一九一六年,曼殊到过青岛看居觉生,后来从青岛到上海,住在环龙路,曾看过桐荪一次,桐荪也去看过他一次,但我却没有和他见面。旧历十一月住西湖陶社,有《与刘半农书》三通。诸贞壮和林秋叶都到陶社去看过他,并有诗赠他。后来又还上海度岁,与仲甫夫人高君曼、刘三夫人陆灵素等往还,灵素曾弄八宝饭请他吃。这一年我没有接到他的通信。
一九一七年旧历正月,曼殊重到西湖,二月,从西湖还上海,住到闰二月,从上海赴日本。在上海时给我一信,到日本长崎时又有一信给我,信上写着:“留东约月余即西返,彼时亚子能来沪一握手否?”月余后他果然又来上海,我也到上海去看他。我在《燕子龛遗诗序》上讲:“最后仍晤君沪渎,时为英士归葬碧浪湖之前数日,握手道故,形容憔悴甚。”就是这个时候的状况,这一次是曼殊和我最后的相见了。别后他仍在上海,初住霞飞路宝康里,夏天住卢家湾程演生处,秋天住新民里蒋介石处。此时身体已极坏,到冬天便进海宁医院去了。这一年也许在医院中度岁,我处便杳无消息。
一九一八年旧历二月,曼殊卧病上海广慈医院,经济很窘,曾托楚伧问我借钱,我寄了三十块钱去,楚伧又延搁不即交曼殊。曼殊为此写信来问我,后来托人向楚伧处取到了,又写信告诉我,这两信就是曼殊和我最后的通信了。他叫我到上海去,我因事不能赴约。旧历三月廿二日(即阳历五月二日),曼殊殁于广慈医院,我闻耗以后,有七绝四首哭他。
我和曼殊生前的交谊,大概尽见于此文了。文中用旧历纪月,因为曼殊的书札,统用旧历,我现在根据着它来写此文,也不能不用旧历,虽然是和用公元来纪年很相矛盾的。
曼殊的杂碎
在黄嘉谟所编的《断鸿零雁剧本》内,有毛常的一篇序,他说曼殊“绘《石达开孤城洗马图》于《天讨》”,这一句话引起了我的记忆。原来,《天讨》是《民报》的临时增刊,一九○七年四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我处本藏有《民报》全份,可惜被人借去了,永不还我,并且连借去的人的姓名都忘记掉,所以无法追取,幸而还留得这一本硕果仅存的《天讨》。我见了毛氏序文以后,就找《天讨》来看,可是没有《石达开孤城洗马图》,而只有《太平天图翼王夜啸图》,翼王当然就是石达开。图中确有一城一马,并有章太炎题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太炎。”毛常所谓《孤城洗马图》,一定就指此图。大概他曾见过《天讨》此图,知为曼殊所作,而忘其名目,只记得是关于石达开的,并且有城有马,所以就杜撰出《孤城洗马图》的名目了。(此图的形式,和送赵伯先的一幅有些相像,不过送伯先的一幅是横的,而此图却是直的。)此图虽无曼殊署名,但笔意确像曼殊,一种萧疏中包含有雄劲的气象,别人是万万写不出的。并且一九○七年,曼殊也确在日本,此事可以无疑了。《天讨》上插画共五幅,除此幅外,尚有(一)《岳鄂王游池州翠微亭图》,(二)《徐中山王莫愁湖泛舟图》,(三)《陈元孝题奇石壁图》,(四)《猎狐图》,都有太炎的题字。其内容:(一)“‘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鄂王诗如此,古人善用兵者,亦多善歌咏,刘项魏武皆是,不独鄂王一人也。作饶歌以厉士卒,将待后贤,太炎。” (二) “徐中山功成以后,泛舟莫愁湖,盖有留侯辟谷,鄂公导气之意,太炎。”(三)“‘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崖云雨至今悲。一声杜宇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愧向苍苔读旧碑。’陈元孝舟泊崖山而作此诗,其云碑者,即张弘范灭宋纪功碑也,书之有感,太炎。”(四)“东方豸种,为貉为胡。射夫既同,载鬼一车。”这四幅和《夜啸图》笔意相同,一定也是曼殊的手笔。《陈元孝题奇石壁图》,在《燕子龛随笔》中也曾讲起过。
卢冀野君有信给无忌,内容如下:“兹又有一事奉告,亦关于曼殊者,即我乡伍仲文丈处,现存苏君当日所绘《女子发髻百图》,闻摹自东京博物馆,皆汉时装束,此殊足珍贵,大约留置京寓,兄就近打听可也。"提起此图,我也记得,是薄薄的一本。曼殊一九○九年上半年在东京时,曾和俞剑华同住,此图即当时由剑华寄我,嘱卖给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和商务不熟,转托朱少屏去问,但商务不要,于是此图就寄还剑华,以后也没有下落,我疑心它已不在世上了。隔了相近二十年,忽然发现了此图的消息,说是在伍仲文处,真真可算是一件奇迹。伍君南京人,我也认得,前年还在北京西安饭店见过,但后来踪迹久疏。直到最近期间,才从友人处探知他上海的住址,便同少屏去看他。谁知他说此图本在他的胞兄义伯处,不幸义伯去世,此图被友人取去,尚未访寻得下落。所以此事仍旧只好暂搁,我希望将来有把此图到手的日子。
一九一二年曼殊从南洋还到上海后,曾把几件东西送给我。这里面,有《潮音跋》四页,现在已成研究曼殊血统问题的唯一证物了。有《答庄湘博士书》,是曼殊亲笔手写的,白纸红格共八页,用血牙色丝线订成薄薄的一本,有雪鸿女士的八分书署签。这一本东西,在内容上果然非常重要,因为曼殊对于佛教的意见,差不多完全在此文披露;就是在曼殊的墨迹上讲起来,也非常的可以宝贵。有《去国行》和《哀希腊》的译稿,共四页,上面写着:“英吉利拜伦作,震旦曼殊译述,杨琛、黄鸾娘、苏金英、林璇女士校录。”字迹不甚整齐,但颇娟秀,一望而知为女孩子的手笔。杨、黄、苏、林四人,一定是曼殊在爪哇时所教的女学生了;(以上几件东西,都带在我手边。)有照片四张:一张是曼殊自己,和一个十几岁的青年,曼殊中坐,须髯颇长,青年旁立着;(此片亦在我手边,已翻印入集。萧纫秋处另有一片,青年的相貌极相像,惟曼殊戴黑眼镜,须髯更长。背面有曼殊的题识:“宣统二年春,同季弟南洋泗水埠造相一幅,时余为也班埠中华会馆英文教习也,苏元瑛记。”所谓季弟者,不知是他香山苏氏的义弟,还是学校内的学生,未敢断定。)两张都是女学生,每张两人,背后写着姓名,是她们送曼殊的,可惜此刻不在手边,不能将姓名抄录:一张是一个赤裸的小孩子,不过三四岁光景,大概是她们的小弟弟吧。还有,是金佛一尊,石砚一方,都很小,很精致,在乡间保存着。因为去年遭了兵匪之难,家中无人敢住,至今把门户封锁起来,我一时又不愿意还去。所以把金佛等拍照流传的事情,只好等待到本书的再版时期了。
曼殊当然不是傻子,但他的糊涂,有时候的确是可以的。一九一二年他和我同住在上海七浦路时,无忌已有六岁了,是和曼殊天天见面的,但曼殊总当他是一个女孩子,有时候还要把他的名字改做无垢。现在所有的证据,是几张风景画片,外面一个套子上写着“无垢女公子收入”七字;又,一张信笺上,写着:“绢花两朵,无忌女弟哂存,瑛。"可惜这两朵绢花不知还存在与否,大概已不容易寻找了。还有一本日文的《妇人画报》,上面也有题款,惜此时不在手边,不晓得他写的是“无忌女弟”,还是“无垢女公子”?一直到一九一七年的信上,曼殊才承认无忌是个男孩子,而写着“闻无忌公子竿头日进"了。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曼殊把无忌认做无垢时,我们的真真无垢(我的第二个女孩子)还没有出世,后来她出世时,我就把这个名字送给她,这也算是曼殊的一种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