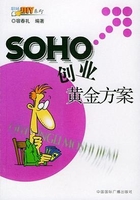没有想头了的林呈祥回到一方晴,在自己床上躺了一天一夜,饭都懒得起床吃。到了第二天夜里,才到别人灶房里摸了两个粑粑喂嘴巴,然后继续摊尸,继续心灰意懒。摊到又一个黑夜来临,他爬起来,拿来半边剪刀,插进隔门的门缝里,用力地拨那边的门闩。这间住房是土改时分给他这个雇工的,就在梅香房间的隔壁,原来他还心中暗喜,以后夜里会梅香就方便了,谁知梅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后来想念妈妈的覃琴就睡在了梅香的床上。现在,覃陈氏走了,覃琴也走了,覃家的人一个也没有了,一方晴算是彻底败落了。
门闩吱呀吱呀地被他拨开了,推开门,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他贪婪地深吸了一口气,慢慢地走了过去。房间一片晦暗,窗户上有淡白的月光。他摸索着在床沿上坐下来,拿过枕头,放在鼻子下嗅了嗅。他闻到了梅香醉人的体息。梅香走了多久了?三年,四年,还是五年?可他觉得昨晚她还在这枕头上睡过。他将整张脸都压在枕头里,想象着过去的欢愉……一个念头冒出来:也许,穿上梅香的衣服,就会感受到她的拥抱呢。他打开了衣柜,想挑一件梅香的棉衣,那样梅香的拥抱就会更柔软,更温暖。可是他没找到棉衣,连单衣都没找到,衣柜里除了一些零碎的布头和几件覃琴的婴儿衣服,什么也没有。谁拿走了梅香的衣物?莫非梅香回来过?他坐回床上,眼里不觉湿了,梅香肯定回来过,可是梅香,你为何不见我呢?你不晓得我想你么,我想跟你一起去啊。他倒在床上,将枕头紧紧搂在怀中,就像在遥远的深夜搂着梅香一样……
后来他被人摇晃了一下,整个黑夜都动荡不已,一个熟悉的声音低声叫唤,覃琴,覃琴,妈妈来了。朦胧之中,他看到了梅香模糊的面庞。他想他是在梦中,只有在梦中,他才有幸见到梅香。他慢慢坐起,委屈地说,梅香,你就只想到覃琴,没想到我吗,你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梅香摸了一把他的脸,噢,是你呵,我没想到是你。他叹道,唉,如今我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你了。梅香说,能在梦中见到也不错,至少还有梦中缘啊。他抓住梅香的一只手,她的手热乎乎软绵绵的,跟真的一样。梅香,你是不是怨我,搞得你有家难归啊?我心里好悔,我不该上台控诉你的。梅香摇头,怎能怪你呢,这都是命。他伤感地说,如今我真的是孤家寡人了,你走了,你娘也走了,覃琴也只认寄爹不认我这个亲爹了。梅香说,覃琴是自己的亲骨肉,你就不要怪她了,从来没有让她认过,你叫她面子上如何过得去呵,别人说她是私伢儿你心里好过么?他沉默了,即使是在梦中,梅香的话也是那样在情在理。梅香又说,你呀,一个大男人,不要光想着自己,只要覃琴好,叫谁爹都一样,幸亏玉成收留了她,我们感谢都来不及呢,就莫计较别的了。他点头,好,我听你的。
梅香说,你要真听我的,从此以后就不要游手好闲了,你要到农业社出工,要好好活着,不是为自己,是为覃琴,万一以后覃琴需要你做点什么呢?就是不需你做什么,你看着她长大,心里也舒服啊。他点头,梅香,你的话听着也舒服呢,你这么一说,我就有想头了,可是你呢?你在什么地方,过的什么日子?幽暗之中,梅香淡然一笑,我嘛,住在你想得到找不到的地方呢,我过得好,你不用挂牵。他抓住她的手捏了捏,很粗糙,从她的手看得出生活的艰苦,哪会过得好呢。他酸楚地道,梅香,只要我俩分开,到哪都过不好的,带我走吧,天天吃草喝水我都愿意。
梅香拍拍他的腮帮子,又说妄混话了,跟我一起你就变成鬼了呢,白天晚上都见不得人,以后还哪么见覃琴?当她有一天想见亲爹的时候,她到哪里去找你?他哑然,半天才说,那我们就这样分手了?梅香摸摸他的额头说,只要心里想着,就不是分手,再说,我们不是可以在梦中见么?他说,那你要时不时到梦中来见见我,别让我把心都想成了一坨铁!梅香点头,我答应你。他又说,你欠我的名份只怕是永远也得不到了,可我不想什么都没有,你要让我亲到你,摸到你。梅香不说话,俯下身来,抱住了他的颈子。他浑身一颤,随即搂住梅香的腰,眨眼之间,他与她溶化成了一个人。
第二天早晨起来,林呈祥看到了他的梦留下的痕迹。他细心地迭好被子,吃过早饭,便穿上草鞋扛上锄头,吹着口哨到农业社做工去了。
自从喝过覃玉成的喜酒之后,季为民就再也没有来过南门坊。当然,覃玉成有机会见到他,不过大多是在公共场合。莲城一有政治运动就开万人大会,一开万人大会季为民就会出现在主席台上。覃玉成没有再找过师兄,人家当副市长了,再找就有攀附之嫌了。
星期天下午,覃玉成夹着月琴去望江茶楼,半路上,见季为民从对面走来,右手夹支烟,左手插在裤口袋里,埋着头,心事重重的样子。覃玉成扬起手,想打个招呼,季为民正好一抬头看见了他。覃玉成恭敬地叫道:季副市长!但季副市长好像没有听见,一转身,拐进一条巷子去了。覃玉成扬起的手举在空中,半天才落下来。这不是他头一次在街上碰到季为民,季为民也不是头一次回避他了。他感到,季为民不光是摆官员派头,同时也在忌讳着什么。
进了茶楼,由于情绪不佳,覃玉成弹唱得有些马虎。茶客们都是老相识了,倒也不挑剔,照样给他鼓掌,毕竟,他们免费饱了耳福,表示谢意是应当的。唱了一气之后,他意外地发现季为民坐在一个角落里,戴了顶蓝帽子,还系着围巾,脸露出的部分很少,可能除了他,没人能认出这是一张副市长的脸。他没有跟他打招呼。他不想热脸挨冷脸。他不相信季为民还有这种平民的雅兴,他肯定不是为听他唱月琴而来。听说市政府有个小礼堂,每过几天就放一场内部电影,那电影不比唱月琴好听好看得多么?
天色渐晚,茶客们的脸暗下来。覃玉成收起月琴,要回家了。他边和老板打招呼边从季为民跟前走过,装出没看见的样子。他感觉季为民的目光粘在他的背上。他一出茶楼,季为民就跟上来了。覃玉成放慢了脚步,等季为民来到身后,回头道:“我以为你真的不理我了呢。”
季为民淡然一笑,不言不语。
覃玉成说:“梅香的事,我又没怪你,为何见我拐脑壳就走?”
“我没在意你怪呵,我拐脑壳了么?”季为民说,“梅香的事是处理得不太妥当,可她自己要负主要责任,要怪也怪不到我头上。”
“那是,谁让她跟政府作对呢?事情也过去这多年了,我早不想它了。”
“该想时还得想,马上要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了,所有出租房屋都将收归公有,南门坊也不能例外,你和小雅可要引梅香为诫,有个正确态度。”季为民的副市长派头不知不觉流露出来了。
“明白,该归公就归公吧,反正我们也没收过租金,给我们留下三间,能过日子就是了。”覃玉成问,“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事的?”
“是顺便和你说说,我是出来听听月琴散散心的。”季为民的眉心皱出一个浅显的川字。
“你也有烦心的事么?”覃玉成关切地问。
“你以为副市长就没烦心事了?比你更多呢。”季为民苦笑一下。
“那是,比百姓操的心多得多。”覃玉成信然,说,“看得出来,你一点也不快活。你把那些烦心事拿出来说说,也许就快活了。”
季为民四下看看,边走边说:“我的事说了你也不懂的。”
覃玉成说:“不见得吧,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布衣百姓,都食人间烟火,那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还不是一样的?”
“我为自己政治上不成熟,说话做事不老到而烦恼,你懂么?”
“嗯,那我是不懂。”覃玉成点点头,“不过,不管如何,以后只要有我帮得上忙的,你就来找我们吧。”
季为民摇头:“我的忙你永远也帮不上的。”
“话别说死了,人生难料的。”覃玉成说。
过去许多年之后,季为民会想起这句话,因为覃玉成后来果真帮了他的忙,帮了他一个生死悠关的大忙,不过此时他们都还对命运的捉弄茫然无知。
两人走到街口,覃玉成说如副市长不嫌弃,请他到南门坊共进晚餐。但是副市长显然没有心情,说家里人还等着的晚上还要开会云云。覃玉成只好握手作别。季为民扭头欲走,却又开口问:“听说,你收养了梅香的女儿?”
“你哪么晓得?”覃玉成再次感到意外。
季为民说,丁玉敏同志在市一中当校长,学校有个女生特别刻苦,成绩不是第二就是第一,那天她把那个学生带回家,被他看见,发现她长得特别像梅香,一问,原来她就是梅香女儿覃琴。覃琴是不是还没有上户口?听说大洑镇不给开证明?地主分子都要实行给出路的政策嘛,何况地主的子女呢。一个女孩子无依无靠,好容易有了个寄爹,应当给予方便嘛。这事我会过问一下,你们放心吧。
“那太好了,我们全家都谢谢你啊季市长!”覃玉成连忙拱着手说。
季为民挥了一下手,转身走了。覃玉成感激地目送着他,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才欣喜地回南门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