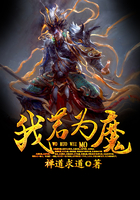1
夜很静。无边的黑暗涌来,严严实实压住她。
木子棉孤独地蜷缩在沙发上,一个人的离开会让整个世界突然间变得冷清,静若死水。犹如一场盛宴,因为某个关键人物的离去,气氛一下就没了。
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很灰暗,很茫然。自从那天在九音山葬完他后,木子棉就感觉自己把魂丢了,什么事也打不起精神,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窗帘全部拉上,一点阳光也不让进,灯也不开。她像个孤魂,囚禁在报社那幢旧楼里。心情潮湿,发着霉,思想更是灰暗一片。
乐小曼这个中间打过不少电话,以前遇上不顺心的事,木子棉会第一个找小曼倾诉,小曼也乐于听她倾诉,并且讲给她一大堆逃离痛苦解决麻烦的方法。乐小曼称这些为锦囊妙计,木子棉也觉得对待生活不如意,小曼办法就是比她多。比如发现凡君跟周培扬那些见不得光的秘密后,木子棉就感觉整个生活都掉进了黑洞,日子暗黑一片,冲突不出去。小曼劝她,你跟一死人较什么劲啊,她再本事大,能从你手里抢走那块宝?
“宝”说的是丈夫周培扬,乐小曼眼里,周培扬什么都好,能干、会挣钱、有气派,是这个社会的风云人物,给女人长足了精神。跟着这样的男人,哪能没有幸福感?换了她,美得要死了。所以小曼认为她是无理取闹,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
“想想看,凡君在前,你在后,人家对凡君有点情,很正常啊。他们三个大学时的故事,难道你没听过?三个都是情种,都对凡君想入非非过,这不怪他们,要怪就怪凡君太优秀,美人,还是冷的,还那么有才,男人不疯死才怪。但你拿这些折磨自己就不对了,要容许男人心里有想法,木木你错就错在想把男人的心控制住,男人心里想什么,咱最好不去管它,抓住钱袋子才是根本。”
乐小曼讲起来头头是道,一条接着一条。有些听了,木子棉觉得有理,比如不该跟一个死去的人争风吃醋,况且凡君还是他们大家的朋友,她自己都对凡君喜欢得不得了呢,周培扬想入非非一下,也不是多大的事。
“天没塌下来,就算塌下来,也由你家大老板撑着,干吗跟自己过不去?”小曼又说。
但有些,木子棉接受不了。比如乐小曼的身心分离论。说这年头儿,指望男人能忠心耿耿地爱你,外面不动一点心思不分一会儿神不失一回身,简直天方夜谭。这样的男人甭说没有,就算有,也是怪物,大奇葩,不值得稀饭。她故意学网络用语,将稀罕说成是“稀饭”。“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别再追逐什么爱情了,那种酸掉牙的东西中吃还是中喝,快扔给那些乳臭未干的青涩小丫头吧。我们是老娘级,要实实在在抓住一些东西。这叫什么来着,对,扔掉现象抓本质。”乐小曼非常得意,她能从一大堆陈腐滥调的词里找到最实用也最能排泄自己情绪的新用法。可是木子棉听了一点兴奋劲也没有。“什么是实实在在的?”她扭过头问。乐小曼认认真真看她一会儿,摸摸她的额头:“木木你没病吧,活这么大,你连啥是最实在的也没搞清?”木子棉嗯了一声。乐小曼很失望地摇摇头:“木木你完了,病得不轻,而且没法治。”木子棉刚要说没法治就不治,乐小曼突然指着她家偌大的房子说:“这,金碧辉煌的房子,花不完的票子,你家的豪车,舒舒服服不用坐班不用看别人脸色的日子,还有大老板太太的身份,哪样不实在?木木你怎么守着幸福叫穷呢,你是在气我是不是?”
乐小曼很认真,也很激动,说着说着,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嘴里喷出一个字:“换!”
“换什么?”木子棉把头歪过去。
“把我家那头猪换给你,把你家这花心萝卜让给我,我只享受一年,行不?”
木子棉以为她能说出什么新鲜话题来,没想又是一句陈词滥调。
“没劲。”
她回敬一句,就又沉浸到自己的心事里去了。
这一次,木子棉没跟乐小曼说。一来小曼刚从上海回来,正为女儿考音乐学院的事发飙呢,据说还跟她家那头猪狠狠干了一架,把汪世伦的脸都撕破了,是真撕破,汪大教授一周没敢去学校。二来,这次不比往常,往常都是她跟周培扬出问题,属于家庭纠纷,家庭纠纷当然可以拿来跟闺蜜讨论。可这次……
这次是啥呢,木子棉一时也说不清。
一件自己还没搞清的事,怎么拿来跟别人说,不能!
木子棉只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去想。她是想搞清楚跟杨默到底算怎么一回事,心灵出轨,还是?
快到中午的时候,手机叫响,木子棉以为还是乐小曼打来的,没接。她想杨默的时候,不想让乐小曼参与进来,这种心理很奇怪,但又舒服。木子棉还是第一次这么对小曼,自己也觉有点不够意思,但就是不想理她。可电话叫个不停,她烦了,走过去狠狠抓起,想掐断这烦人的叫声。电话居然是苏振亚打来的,木子棉呀了一声,接起。
苏振亚说:“还窝在家里吧?”
木子棉问:“您怎么知道?”
苏振亚说:“论坛那边找不到你,就想你一定又遇事了。”
木子棉哦了一声,没往下说。周培扬一直反对她参加的这个论坛,就是这位叫苏振亚的教授发起的。苏振亚是个学者,木子棉最早认识他,是因为一堆文章。当时她还在报社担任编辑部副主任,有天一位年轻编辑拿来一堆关于探究现代婚姻和现代人心理疾病的文章,要她看。只翻了几页,木子棉就被迷住了。文章观点新颖,剖析准确,尤其对现代人遭遇的婚姻危机、情感裂变,更是做了细致入微式的解剖,并尝试着用心理学的方法为婚姻中的男女号脉。木子棉花了两个晚上,算是把文章过了一遍。她被苏振亚质朴的文风、面对面交流式的语气感染,对苏振亚谈到的诸多案例更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文系毕业后来又对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学说着迷的木子棉如同枯燥航行中突然发现灯塔,兴奋死了。当天便打电话给苏振亚,非要跟他面谈,并诚恳拜他为师。苏振亚也是一位开朗的人,开朗且率真,讲话不瞒不藏,且往往能善良地击中要害。两人一见如故,很快便成了莫逆之交。不久之后,那些文章以专栏形式发表,反响极为强烈。木子棉办公桌上的电话被打爆,她这才知道,婚姻问题根本不是她原来想的那种个案,看似繁景一片的高歌中暗藏着那么多的不幸。除一般的家暴、外遇、第三者插足等等外,木子棉又听到许多新鲜事,比如性冷淡引发的不和,比如潜藏在极端自私后面的男性不安全感,还比如明明是炽热的爱表现出来却是冷冰冰的霸道。总之,那段日子木子棉听够了男人女人的倾诉,世界像是突然为她打开一扇窗,让她一下子看到了许多陌生而残酷的东西。当然,这些都是裹挟在婚姻外壳里的,个别外壳还光鲜透亮,耀人得很。
那个时候木子棉还没把这些跟自己的生活联想起来,那段日子她幸福着呢,老公下海创业,发誓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她很支持,是男人就该去闯,这是她的逻辑。若不然,周培扬也不敢草率从政府部门跳出来,吃什么螃蟹。自己在报社如鱼得水,上上下下恭称她才女,她自己也认为自己很不错。所以她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听去思考,这个世界上不幸的人原来那么多,这个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的隐秘,看似一桩桩鲜亮的婚姻里还藏着那么多难以启齿的痛。木子棉不安的,年轻优越的她忽然有了一份责任感,一份拯救他人的使命。
苏振亚笑她:“你是个理想主义者,而研究这些问题要有承认生活缺憾的勇气,你不具备。”
“我不具备吗?”她不相信地盯住自己已经拜过的老师。
“一个生活十分优越的人,是无法进入他人痛苦的。等你经历点波折再说吧。”
教授苏振亚当初本来是句玩笑话,谁知竟一语成谶。先是周培扬创业失败,从一条野心勃勃的大龙一下缩成一条虫。公司承接的第一项工程便出了事故,虽然没死人,但重伤五人。而甲方领导又是一名贪得无厌的人,不但贪,还色。为处理善后木子棉陪吃饭时竟然敢当着周培扬面将脏手伸到她胸脯前。要不是当时还有报社这块牌子罩着,怕是那时候她就会成殉葬品。事故最终算是处理了过去,周培扬却欠下一笔巨债,按当时的想法,这辈子都休想还清。这也成了她后来放弃热爱的编辑工作,接受广告部工作的一个原因,想为周培扬实实在在做点什么。谁知命运自此跟她作对,一连串的变故接踵而来,乱石一般砸向她,原本美满的日子横遭雷劈,一桩桩稀奇古怪的事令她应接不暇,喘口气的机会都没。
累啊。木子棉长长叹一口气,这些年,要说她真是不怎么容易。
先是周培扬跟母亲庄小蝶,她都说不出口。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撞眼里的那一幕,她怎么也抹不去。心情好时她能把一切想开,也能忘掉,能释怀,一旦心情变坏,那一幕便以刀刺剑穿的形式狠劲地咬她,让她瞬间觉得生活真他妈没意思,狗屁婚姻,狗屁爱情,全他妈的是骗人的。
再后来,周培扬是发了狠,二次创业成功了,大洋一天一个样,上天对他格外的恩赐,没几年,便从一个负债累累的失败者变身为光芒四射的企业家,商界明星、大腕,按时下的说法,是重量级人物。可木子棉却不慎坐了滑铁卢,广告部经理本来做得很稳,业绩也很突出,毕竟她的能耐在那放着,只要有平台,不可能发挥不好。按姚启明的说法,她是点石成金的人,女杰中的女杰。谁知那年报社突然曝出一起腐败窝案,分管广告的副总姚启明第一个被搅进去,跟着,一拨人受到调查,报社一时乱了套。木子棉也未能幸免,作为姚启明身边的红人,被有关部门怀疑实属正常。她在一个小宾馆住了两个月,当然是让有关部门“请”去的。那两个月,对她此生有摧毁性的作用。她尝到了从天上到地下的人生苦味。以前风光无限的报社广告部主任,报社上下宠着的角色,忽然间被打入冷宫,行动什么的全没了自由,还要天天面对一张张威严冷酷的脸,谈那些她根本不知情的问题。雪上加霜的是,也就在那个时候,她经手的一宗大额广告出了问题。一家叫作先锋的广告公司,以偷梁换柱的方式从她手里骗走五百万广告费。都怪她太轻易相信那个叫亚海的年轻人,之所以跟先锋广告公司谈代理权合作,木子棉就是看中了亚海的年轻还有魄力,以及二十多岁年轻人身上散发出的那股青春气息。她想帮他,太想帮。这是一种毫无来由的愿望,离奇得很。后来乐小曼得知内情后骂她:“什么是想帮她,你是发春,见不得年轻男人。”木子棉据理相争,说根本不是小曼说的那样,她是看好这个孩子,尤其他的奋斗精神。
“结果呢?”小曼恶作剧地问。
“结果被骗了,他拿着报社先期预付的五百万,跑了。”木子棉沮丧地道。
五百万预付是她自己做的主,跟被抓的姚启明没有关系,这事姚启明也不知情。报社广告部为谋求业务发展,承包了两条主街的灯箱广告,为了揽到更大的生意,要先将两条主街道的灯箱广告重新更换。本来这钱由先锋公司出,可亚海三番五次向她告艰难,说公司刚刚接手一笔大业务,投入太大,让报社先垫付一些,等客户的预付款到账,马上还回去。木子棉自作主张,从广告部小金库拿出五百万,垫付给先锋。谁知钱付出去三天后,叫亚海的消失了。
那笔钱是周培扬替她还的,如果不还,她有可能去坐牢。
这之后,周培扬对她的态度,就变了。按木子棉自己的话说,周培扬华丽转身,实现了从奴隶到将军的大翻转。
苏振亚打电话让木子棉过去,说有要事跟她商量。
木子棉不能不去。
这些年,苏振亚对她帮助很大,如果没有苏振亚,一次次的苦路,她是走不过来的。
他们这些人,按周培扬的说法,是疯子。一段时间乐小曼也这么说,包括对苏振亚,乐小曼意见大着呢。“你老跟他在一起什么意思啊,难道你恋老?”
木子棉知道自己不恋老,更没传说中的恋父情结,况且苏振亚也不会让她恋。但是生活永远不是一个人行走,每个人都需要别人引路。木子棉当天便坐了车,来到了这座叫银州的城市。
银州不大,所处的位置也很偏僻,跟铜水自然是没法比,可木子棉觉得亲切,一种归家的感觉涌来,木子棉突然想哭。
苏振亚没让她哭。
苏振亚也是刚刚得知杨默去世的消息,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木子棉。
“他的死让我们悲痛,不过木木。”老教授苏振亚顿了一下,在一条长石上磕了下烟锅。他抽大烟锅,多年的习惯。又装上烟末子,点燃,猛吸一口,然后爆发出一片剧烈的咳嗽。木子棉有点紧张,苏振亚的咳嗽很厉害,每次都有接不上气的错觉。她提醒过几次,让他少抽,或不抽。苏振亚听不进去,说人有些习惯能改,有些不能,改了,就不是你了。
“可这是坏习惯,不好。”
“习惯这东西,无所谓好无所谓不好,关键看适合你不,适合你的,就保留,不适合的,就把它剔除。”
苏振亚老是有他自己的理论,他在这个世界上应该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苏振亚终于咳完,自己给自己捶了捶背,说:“不过木木,你应该清楚,谁的生命都不可能永恒,人其实就是一道虹,有的人时间长一些,有的人时间短一些,但最终大家都得离开。”
“为什么先离开的是他?”
木子棉本来是不想谈杨默的,从九音山回去后,她就下决心要把这个男人忘掉。事实证明,她没忘掉,而且杨默一路跟着他,到了银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