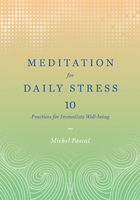作为一种进步,抒情诗的终止情节化和叙事化的滑行是重要的迹象。诚然,当何其芳否定那些轻飘飘的“云”而下定决心从此要叽叽喳喳地发议论,情愿要一座茅草的屋顶而不要那些云、以及月亮星星的时候,诗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的。但是,人们当时并不知道,云也好,月亮和星星也好,并不能完全从诗中赶走,它们同样地可以传达诗人内心的“沉甸甸”的情感。这个事实,已经由诗人的创作得到了证明。在当代诗歌的发展中,
公刘发表的《佧佤山组诗》,有一首《西盟的早晨》,其中就有给人以分量感的云的形象:
我推开窗子,
一朵云飞进来——
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
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没有琐碎的过程,没有多余的交待,这首诗的开头一节,就彻底地抛弃了那些流行病般的繁琐的叙述。这诗是表现守卫边疆的兵士的生活的,写的是兵士的站岗,但他完全不写过程,也没有情节,一开始,就是飞进窗子的一朵云。
这首诗在当时的出现引起震动。很清楚,它对那些太过具体的叙述的惯性是一种挑战。而且,它对于迷漫当时诗坛的满足于“务实”的气氛也是一种新的宣告。《西盟的早晨》写哨兵的夜间站哨而迎接了黎明,能够不去琐屑地交待细节,也不写他的夜间的所见所闻,而径直以一朵云来概括,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反抗流俗的举动。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吸引了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除了一些不愿随波逐流的诗人而外,有谁还注意到这平常的早晨飞过来的一朵云呢?但是,这实在是独特环境中的独特的云,它是南方群山中带着繁露和轻霜的潮湿的云,它不是轻飘飘的云,而是充满了水气而显得凝重的云。云朵飘起的深谷,充满了清晨的寒气,而太阳业已出来,透过那氤氲的水气,光线闪烁而富有变化,因而它有着“难以捉摸的光彩”。在这里,士兵的岗位的特殊性不言自明,士兵夜间的辛苦可想而知,略去对于实际情况的拘泥的描摹,而借助于一个独特的意象,象征性地总体地进行概括,这在当时,是颇有创造性的。整个西盟山上的特殊风光,他只用一朵飞进窗子的云,只用他的寒气未消而又通体披着梦幻的光,来为西盟的早晨造型。
当时的诗歌过于注重写实而忘了抒情,因为关注于客观的描摹而忽视主观的情感的抒发,一方面是由于诗人们对过去所积累的诗的艺术经验的简单的否定所致,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当时诗歌的幼稚和不成熟。当务实的气氛弥漫诗坛的时候,一些敏感的诗人已经看到了它的缺陷:它将阻碍诗歌的发展而立意悄悄地改革。李瑛是这些诗人中一直默默努力的一位诗人。而成绩显著成为异军突起的诗人,则是公刘。公刘解放前写过诗,如《我们是春天的据点》:“和风雨斗争的日子,树林是春天的据点,和黑暗斗争的日子,火把是光明的据点。”那时,他并没有具体地写事件的过程。但他也有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他也曾用诗“记录”过,如的《毛泽东的太阳照猛丁》,的《兵士啊,你们要小心!》。在那里,他的诗的照搬照记现实倾向恐怕比同时代的许多诗人都要“不厌其烦”。但是公刘只用了一两的时间便结束了这个幼稚的阶段。他已经领悟到诗不能是生活的实录,而是生活的综合,特别是诗人情绪的概括。与写《西盟的早晨》同时,他还有一首《山间小路》:“一条小路在山间蜿蜒,每天我沿着它爬上山巅;这座山是边防阵地的制高点,而我的刺刀则是真正的山尖。”公刘自己认为这最后一句诗是他在边疆生活的全过程凝成的,他《在学习写诗的道路上》说:“如果说,这座山的海拔高度应该加上战士的身躯和他的枪刺的长度乃是一个形象的结论。那么,在导向这个结论之前,就必须有大量的形象数据,进行反复的形象归纳;诗,来源于生活,我怎能不信服这一真理。”
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这是一致的,区别仅仅在于,公刘没有照搬生活的现象,他在掌握了众多的“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反复的“归纳”。在强调反映现实的时候,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实感”来排斥和反对诗人的想象(这种反对即劳辛说的“那理想就是他们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清醒的诗人没有照这种片面的理论去实践。仅仅满足于临摹现实的诗人,他可以绞尽脑汁去描写战士守卫的山有多么高,他决不会想到把战士的身高和枪刺的长度计算到他所看到的“制高点”上面去。在公刘这种超脱了写实的气氛中,战士和他的枪都融入了高山的形体之中,物和我化而为浑然统一的形象,而全然和那些只见物不见我的诗篇划分了两个时代:诗的幼稚时代和诗的走向成熟的时代。这些诗篇,也许还作了这样的宣告:那种诗人专门讲述别人的故事的局面已经变化,诗人的自我形象开始成为诗的真正的主人。,也是这位公刘写了《丝》,那是他在上海访问了一系列工厂之后为棉纺厂而写的一首诗。在这首诗中,我们没有看到一台机器,没有烟囱,也听不到马达的声音,更没有棉纺工人操作过程的描写,他没有去写织机的喧闹和纺锭的飞旋。他避开了容易就地写生的机器和车间。这一切都为他所轻视,他注意的不是过程和情节,而是棉纺厂所引发的关于中国的历史文明的联想:“应该写一千首诗,来赞美我们的丝。赞美自古而今采桑的女子,养蚕的女子和织纺的女子。像良心一样干净,像爱情一样缠绵,骑士因披肩而威风凛凛,舞姬因长袖而飘飘欲仙。母亲中国啊,当你披着丝的头巾,走在世界的大街上,吸引了多少行人!但我们的财富又岂仅在于丝?值得自尊的是天才的人民!”除了最后两句留下了时俗影响的痕迹外,其余的诗句:干净的良心,缠绵的爱情,骑士的披肩,舞姬的长袖,这一切,都是从具体的劳动妇女双手纺出的丝的形象引出的。最后,它化而为“披着丝的头巾”,“走在世界的大街上”的“母亲中国”。在风靡诗坛的写实空气中这种超凡脱俗的形象,确实带给人们以完全新奇之感。
标志着公刘艺术技巧的走向独立的,是他的《上海夜歌(一)》。这是一首写上海这座大城市的诗篇。在这样的大题目面前,那种跟着现实生活后面被动地“实录”
“实感”的“现实主义”,必定会陷于一筹莫展之中。掌握了现实生活提供的“数据”进行过反复归纳的诗人,如同当一下子抓住了升于深谷的一朵云那样,他一下子抓住了最富特点的上海关上的钟楼,而且站在高处把上海放在夜晚的环境中表现。夜晚当然是白日的结束,他不说白日结束了,而通过钟楼上面的时针和分针,说是巨剪般地“铰碎了白天”。他不再琐碎地描绘上海的夜景,而是只用短短的四行诗对上海作了总体的综合的概括:“夜幕从二十四层高楼上挂下来,如同一幅垂帘;上海立刻打开她的百宝箱,到处珠光闪闪。”不再是刻板的临摹,也不以状物写景的形似为目的,它追求的是表现出上海那种大气魄的雄浑的美。他追求一种立体感,而不是如同过去那样自始至终平面地铺展。在这里,公刘的贡献在于,他的确给当时过于写实的壁垒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这一点,被一些理论工作者注意到了,一篇文章指出:“中期公刘同志描写上海的那组诗歌,可以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就是由于吸取了现代派的某些手法来表现上海这个大工业城市的情调和节奏”
仅仅有这一点进展便给人以鼓舞。但以公刘为代表的一批青诗人的贡献却不仅仅这些,他们尽管未作宣布,却以自己的实践,对创作的实际局限作试探性的突破。例如,他们不再死守“基地”,不把自己捆缚在一个“据点”上,他们开始“流动”。“流动”给他们带来了更为开阔的视野,更为丰富的场景,更为活跃的情绪。例如公刘,要是他死守酉盟山,他的终点也就是《西盟的早晨》。他跨过了黄河,写《夜半车过黄河》,感到了我们民族“固执而暴躁的父亲”应该有慈祥而谦和的性格;他登上北京的景山,看到了“炊烟相招,鸽哨相邀,半城宫墙半城树”的京都壮丽气象;他到了上海,写出了一些表现工业的节奏和旋律的诗篇。打破了凝固状态的诗人的“流动”,能够为造就大诗人创造条件,而死守一点,只会因生活的枯竭而窒息灵感。
这一批诗人他们的确有自己的基点,例如公刘,他的基点是部队,是兵。但他们在打破固定基地的观点局限,兵是公刘画板上的“底色”,也可能是绿色,但绝不是单调的绿,而是富有层次的夏天的绿。他们吸收多样的营养,古诗的营养,外国现代诗的营养,民歌的营养(例如公刘、白桦、周良沛、高平、顾工,都是兵,但又都受到少数民族诗歌的滋养)。有层次感的绿,使他们的画面呈现出丰富,如同艾青写的:“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到处是绿的……到哪儿找这么多的绿:墨绿、浅绿、嫩绿、翠绿、淡绿、粉绿……绿得发黑,绿得出奇;所有的绿集中起来,挤在一起,重叠在一起,静静地交叉在一起。”这种并非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和立体的多层次的效果,来自多样的生活体验。有成就的诗人,绝不把自已局限在某一单一的题材上,他们写兵,写工业,写森林,写爱情,更写“我”。
注释:
李季:《我和三边、玉门》。《文艺报》(期)。
劳辛:《读诗随感》,《诗的理论和批评》,上海正冈出版社版。
摘自傅仇3月日给本书作者的信。
李季:《热爱生活,大胆创造》,《文艺的学习》(3期)。
同注。
刘登翰:《新诗的繁荣和危机》,《新诗的现状和展望》,广西人民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