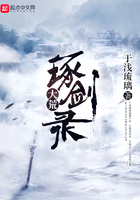“哎哟!哎哟!”黑汉子厉声号叫,“你跟爷动手!你知道爷是谁?爷道儿上混的,大名鼎鼎的乌老三,整个前门都是我的地盘儿!你还不放手!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社里弟兄聚上来,兴高采烈地就要帮手开打,米师傅急切地挤上来劝止:“天青!别惹事,快放开!你可改改你这脾气吧,让一步,服个软儿!”
天青吸口气,一推一带,将那乌老三掷向墙边的林郁苍,只听得一声尖叫,林郁苍抱着脑袋逃了开去。天青喝道:“今儿个就谢谢您赏光来听戏了,以后规矩着点儿,唱戏的也不是好欺负的!”
乌老三咬牙切齿地揉着膀子:“你够狠!趁爷不备,不算本事!敢不敢跟爷找个地方单挑一场?爷打断你的狗腿!你不是腿厉害吗,大武生吗,爷叫你一辈子唱不了戏!”
天青身子一挺,欲待开腔,米师傅死命将他拉回来:“天青!你还要命不要!”
乌老三更来劲儿了,扯着嗓子喊:“今天这事儿不算完!小家雀儿愣装个大尾巴鹰,我呸,什么玩意儿,没胆子单挑,就马上给爷磕三个响头求饶!”
林郁苍连忙凑上来:“给爷也磕三个!不然每天来砸你们场子!别寻思着什么弹压席能顶屁用,爷不怵那个!”
天青拉开米师傅的手,朗声道:
“我接你的招儿!来,就今儿个,你定地方!”
天色尚明,肉市街零星地挑起了灯,小贩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广盛楼一群半大小子拥出来,在这样乍暖还寒的天气里,个个光着头,只穿水衣彩裤,闹哄哄又叫又嚷。天青已经卸了妆,穿一身素灰夹袄,黑裤,白袜黑鞋,走出广盛楼院子,气定神闲地站在师兄弟中间,跟乌老三定地方。
乌老三定的地方是天安门前黑松林,离这儿不远,走两步就到,他气势汹汹地指着方向,冲天青喊:“有种的一个人过去!不许带人!不许带家伙!拳脚定胜负!”
妃红也出来了,头发披散着,身上戏服还未换。她伸手抓住天青:“你不要去!”
天青轻轻挣脱,笑道:“别担心,他不是我对手。”
“他们会使坏心眼子,伤了你!”
“我会留心。今天要是不结了这茬儿,以后总是麻烦。放心吧,有我在,不能让人欺负了咱们!”
眼看着天青被乌老三那帮人簇拥着往天安门去了,秦月明等小兄弟挤在玄青身边急叫:“师哥!咱们得一起去!”
玄青微眯着眼睛望住天青背影,凝神片刻,正色道:
“这么一大群人过去,岂不成了打群架,直接就叫巡警给抓了?咱们远远跟着,看看动静儿再说!”
天安门外黑松林,也不知哪年哪月长下的,古木参天,又深又密,平素无人行走。林中有块空地,平坦、宽敞、幽静,历来是个约架的好场子。天青一行人到了这儿,天也快黑了,小厮捡了松枝,燃成火把,簇拥在林郁苍身边,照着场子中间的乌老三和天青两个。
“打死这丫挺的,等会儿叫那帮戏子来给他收尸!”林郁苍跳着脚叫道。
乌老三两腿一蹲,向前猛蹿,真正是势若猛虎,两手直扑天青胸口。天青单手横扫,把他两手都扫在一边,一拳打在他腰侧。乌老三疼得一龇牙,也挥起拳来,劈面去打天青的脸,天青伸出左臂,硬接了他这一拳,猛抬右腿,膝盖撞向乌老三的肚子,直把乌老三的眼泪都撞出来了。
其实天青也没怎么打过架,但是常年练功,身上结实壮健,等闲拳脚伤不到他,而他自己的拳脚腰腿,饱经磨炼,十余年的毯子功,那举手投足的敏捷轻巧、速度劲力,都是随心所欲,油然而生,这一架打下来,出手快,落拳重,乌老三纵是皮粗肉厚,却也经受不住。只见乌老三哇哇大叫,越打越乱,急切间抱住了天青胳膊想把他扳倒,却不料天青下盘最为扎实,一扳两扳都扳不动。乌老三伸脚一踹,又踹了个空,趔趄着转了个身,被天青照着屁股踢倒。乌老三狼狈地爬了两步,挣扎着起来,又被天青拦腰一腿踢翻,脚踏在他肚子上。
“服不服?”天青脚踩着乌老三,眼睛却瞄着林郁苍那一班人。
林郁苍所倚仗的,就是乌老三,如今一见他被制服,满心霸道之气,顿时泄得无影无踪。他后退几步,冲天青满脸赔笑,连连哈腰拱手道:“英雄!好汉!您是我大爷!这孙子我不认识他,您随意处置,我就不妨碍您啦!”话音一落,朝后就蹿,一群人呼啸而去,竟将乌老三一个人丢在天青手里。
天青低头盯着这员手下败将,防着他趁己不备暴起伤人,谁知乌老三大声号叫起来:“都他妈的是什么玩意儿!爷不伺候啦!我服啦,服了你啦靳老板!妈的,我乌老三算是栽在你手里啦。”
天青一怔,道:“你还得向我师哥和米师傅赔礼!”
“赔!赔!咱江湖中人,说话算话!”
天青移开脚,乌老三翻身爬起,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居然真的乖乖拱手赔礼:“靳老板真是高人!文武双全,全都是真玩意儿!小弟冒犯,您大人大量!”
天青半信半疑地也拱拱手:“客气了。下手重了,也请多担待。”
“哎哟!哎哟!还真疼!愿赌服输,那也没辙。靳老板的功夫是打哪儿学的?”
“我没学过功夫,只会唱戏。”
“那就是天赋异秉了!小弟佩服得紧!你我一见如故,就此结拜兄弟如何?”
这一口煞有介事的江湖腔,倒惹得天青笑了:“这个不敢当。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吧,以后做个朋友。您常来听戏喝茶,就是给我们面子了。”
“那是准定!准定!靳老板的玩意儿,我服!我操他大爷的,我这是跟了什么人,一点儿江湖道义不讲!”……
玄青带着喜成社弟兄在松林外头等着,遥遥只见林子里隐约地一忽儿拳来脚往,一忽儿高声喝骂,一忽儿又没动静了。过了半天,只见那个胖子带一帮小厮狂奔而出,在他们面前蹿过,里头却没有乌老三,也不见天青的影子。秦月明连忙拉拉玄青:
“师哥,咱们过去吧?”
“再等一会儿!”玄青望着密林深处。
这一等可好,不一会儿,大伙儿目瞪口呆地看着乌老三和天青勾肩搭背地出来了。
“天青!”妃红急扑过去,上上下下打量着天青,闪亮的一双秋水眼里,满满的都是仰慕,“你怎样?没伤着?你……你真是个盖世的英雄!”
天青笑着摇摇头,还未答话,背后的乌老三已经扯开嗓子叫起来:“咳!咳!大伙儿都听着!以后我跟靳老板就是哥们儿了!”
喜成社弟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都愣愣地看着他。乌老三摸摸脸上划开的一道口子,龇龇金牙:
“靳老板身手厉害,信义过人!咱江湖中人,就服这个!以后靳老板的场子,就是我乌老三罩着了!谁敢跟靳老板过不去,就是跟我乌老三过不去!以后我就是他亲哥,他就是我亲弟!能做靳老板的哥,我倍儿有面子!他是石秀,我就是杨雄!他是武松,我就是武大……”
真是个浑人啊。喜成社弟兄忍俊不禁。天青无奈地转头,瞧着乌老三:
“兄弟,不带这么损自己的!”
依稀的胡琴调弦声,自未开戏的前台传来,丝丝缕缕,断断续续,仿佛一段未定的心事。
妃红坐在扮戏房镜子前,细细描画眉眼。她的容貌,本已十分秀美,化妆勒头之后,更是勾人魂魄。旦而不媚非良才,妃红最了不得的,就在这个“媚”字,她有着天生带来的一股子风流气韵,能用淡淡一瞥、轻轻一指、缓缓一个转身,演绎出千般娇美万种温柔,那个媚劲儿,是深入在她骨子里的。
当年刚开始学戏时候,第一次扮上,就教科班里老教师们都直了眼:“这孩子,将来了不得呀!”
科班老板娘,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太太,揣着毛皮筒子坐在旁边,喃喃说了几个字:
“冤孽,冤孽。”
小小的妃红,不知道这是不是好话,她只知道,自己在台上,有本事搅得台下翻江倒海,满园生春。十几岁在梆子班唱花旦时,多少人迷她迷得失心疯一样,叮叮当当的现大洋往台上扔。后来到京城来改唱皮黄,也仍是一枝独秀,到哪儿都是头牌。梨园行本是男旦的天下,坤旦根本不是同一个级数,但妃红凭着这一身本事,硬是在这男人堆儿里站稳了脚跟。
男人堆儿里争强,又有什么用呢?名旦筱妃红,年已足足二十岁,婚姻大事,仍是茫然无着。闯荡江湖也有十几年,台上台下,各式各样的男人,妃红的眼里,着实见得太多:戏班子里的爷们儿,功利心太重,为了台上一个位置,能想法子剥掉同仁一层皮;台下捧角的爷们儿,那都是取乐儿来的,她在戏台上卖命,他们在底下跷个腿儿喝茶,她在台上唱着,听着他们怪声怪气叫着,一双双眼睛,钩子似的,恨不得把她扒光……
时日久了,妃红早已拿男人只当手底下的玩意儿,恣意挑逗着、戏弄着,让他们为自己神魂颠倒,丑态百出,就是别想得到她的心。早已不指望能出现一个真正让自己倾心的男人,谁知道,还会遇上靳天青?刚搭喜成社时候,已经对他的出众仪表留了神,天长日久,渐渐发现,跟他的心地相比,那相貌上的英俊,简直都不值一提!他的好,不是演的,不是唱的,不是扮出来的,他那刚勇、良善、纯真、热诚,是真心真意、真刀真枪,一点儿不掺假的,比戏台上所有大英雄——武松、石秀、马超、赵云,都更让人钟情!
再好的人,不是自己的,也是枉然啊!
梳头桌的师傅,已经为她刮好了片子。一绺绺真人头发,用榆树皮汁液泡好,刮通,两个大绺、七个小弯,整整齐齐备在桌上。妃红轻轻拎起,对着镜子,贴上自己的脸。小弯贴额头,大绺贴鬓角,水润黑亮的一圈,勾出一个完美的脸型。旦角的化妆,是多么能骗人啊,就算头角峥嵘的大老爷们儿,在这样装扮下,都能拥有一张漂亮的小鸭蛋脸。可她筱妃红的鸭蛋脸,是天生的呢,她本人的美,丝毫不比台上的扮相逊色半分。
妃红看着镜中的自己,曼声吟了几句:
闲中习刺绣,寂寞困春愁。
心事难出口,见人面带羞。
她今天贴的是《拾玉镯》,闺中待嫁的孙玉姣。女人爱一个男人,是有多难?两情相悦,玉镯为媒,费了那么大周折,最后也只做了人家的妾。妃红想要的,也不过只是一个可靠的男人啊,爱惜她,保护她,能让她过上安稳的好日子,不用孤孤单单在这戏台上谋生活。她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靳天青的影子,那宽厚的肩背、雄健的臂膀,台上满坑满谷的碰头彩,台下解危济困、傲视群雄的气概……没错,妃红看准了,他就是那个最可依靠的男人!
梳头师傅为她戴上大簪、发垫,梳起大发,包好水纱,一个可以乱真的假发髻,活现面前。全套水钻头面,一一插戴:泡子、顶花、偏凤、串蝴蝶……这都是筱妃红购置的私房,最时新的水晶玻璃镶嵌,灯下闪烁着耀眼的亮光。戏台上的一切,都各有各规矩,像这头面,小家碧玉就只能用水钻,大家闺秀只能用点翠,苦守寒窑的王宝钏呢,只能用银钉。人生如果也有这样的规矩,倒也省心,可是,人生没这规矩啊,你这辈子,戴银钉还是戴点翠,要靠自己的修行得来。
环佩叮当的妃红,含着一丝浅笑,向上场门走去。戏要稳住了唱,她自己心里认定了的那出戏,才刚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