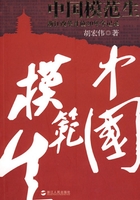“不知道,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这得看情况。说不定我压根儿不会再来了。”
“为什么?”
“这取决于许多原因,主要取决于我跟公爵的关系。”
“这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卡佳断然道,“我说伊万·彼得罗维奇,如果我来看您,怎么样?这样做好吗?”
“您自己认为呢?”
“我认为好。也不因为什么,就来看看您……”她笑了笑,又加了一句。“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除了尊敬您以外,还很喜欢您……可以向您学到很多东西。我喜欢您……我把这一切都告诉您,是不是不知羞耻呢?”
“有什么羞耻的?我觉得您很可亲,就像我的亲妹妹一样。”
“您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啊,当然,当然!”我答道。
“嗯,他们准会说,一个年轻姑娘这么做是不知羞耻,是不应该的。”她又向我指了指围坐在茶桌旁聊天的那帮人,说道。在这里,我要说,公爵仿佛故意让我俩在一起聊个够似的。
“我心里一清二楚,”她又补充道,“公爵想要我的钱。他们认为我完完全全是个孩子,甚至当着我的面也这么说。我倒不以为然。我已经不是孩子了。这些人也真怪:他们自己才像孩子呢;哼,也不知道他们成天价忙些什么?”
“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我忘了问您:阿廖沙经常去找他们的那两位,列文卡和鲍林卡,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他们是我的两房远亲。非常聪明,也非常正派,但是爱空谈……我了解他们……”
她说罢微微一笑。
“您打算以后捐赠给他们一百万,有这事吗?”
“嗯,瞧,就说这一百万吧,他们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让人烦死了。对一切有益的事我当然很高兴捐助,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对不对?但是什么时候捐献还不知道哩;可他们现在已经在那里分来分去,又是讨论,又是嚷嚷,又是争论:到底把这钱用到什么地方好,甚至为这事发生了争吵——这岂非咄咄怪事!也太性急了嘛。但是他们毕竟非常真诚,而且……很聪明。在学习。这总比有些人纸醉金迷,混日子强。对不?”
我跟她还谈了许多。她几乎把自己的一生经历都说给我听了,同时又非常用心地听我说话。她还总要求我多说点关于娜塔莎和阿廖沙的事,而且越多越好。当公爵过来找我,告诉我应该告辞了的时候,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了。我告了别。卡佳同我热烈地握了握手,别有深意地望了我一眼。伯爵夫人请我有空常来;我跟公爵一起走出了大门。
我忍不住要谈一个奇怪的也许与这事完全无关的看法。我跟卡佳谈了三个小时,我无形中得出一个奇怪的、但同时又很深刻的想法:她还完全是个孩子,对男女关系的种种奥秘还全然不知。这就使得她的某些言论,以及她在谈许多十分重要的问题时所使用的那种一般说很严肃的口吻,显得异常滑稽。
第十节
“我说,”公爵同我一起坐上马车时对我说道,“现在咱俩去吃点消夜怎么样?您意下如何?”
“真的,我不知道,公爵,”我犹疑不定地答道,“我从不吃消夜……”
“嗯,自然,咱俩一边吃消夜一边可以谈谈。”他加了一句,狡猾地定神注视着我,看着我的眼睛。
怎能不明白呢!“他想发表他的高见,”我想,“我真是求之不得。”我同意了。
“那就说定啦。到海洋大街的Б饭庄[29]。”
“上饭馆?”我有点惶惑地问道。
“是啊。那又怎么啦?我很少在家吃消夜。难道您就不肯让我请请您?”
“但是我已经跟您说过,我从来不吃消夜。”
“破回例也没关系嘛。再说,这是我邀请您的……”
他的意思是说替我付账;我相信,他加上这话是故意的。我答应陪他去饭馆,但是我决定自己付钱。我们到了。公爵要了个雅座,很内行地点了三两道菜,菜点得也很有味道。菜价很贵,他还要了一瓶高级的开胃酒,价钱也很贵。这一切都不是我付得起的。我看了看菜单,要了半只松鸡和一小杯拉斐特酒。公爵一听便大声抗议。
“您不愿意跟我一起吃消夜!这甚至很可笑。对不起,我的朋友[30],但是,要知道,这是……令人愤慨的洁身自好。简直是最渺小的自尊心在作怪。这里还几乎搀杂有等级偏见,我敢打赌,一定是这样。跟您老实说了吧,您这是看不起我。”
但是我固执己见。
“话又说回来,随您便,”他加了一句,“我不勉强您……请问,伊万·彼得罗维奇,我可以跟您友好地随便谈谈吗?”
“这是我求之不得的。”
“那就好,我看,这种洁身自好对您有害无益。你们这些人都有这毛病,因此也一样,都对自己有害。您是搞文学的,您应该知道上流社会,可是您却敬而远之。我现在说的不是松鸡,我说的是您完全谢绝同我们这个圈子的人有任何交往,这样做的害处就非常大了。此外,您还会失去很多东西——嗯,一句话,您会失去飞黄腾达的机会——此外,即使说这个吧,您描写的那些东西也应当亲自去体验一下嘛,在你们那些小说里既有伯爵,也有公爵,也有小花厅……话又说回来,我扯哪儿啦?你们现在写的净是贫穷,丢失的外套,钦差大臣,寻衅闹事的军官、官吏,过去的岁月以及分裂派教徒的生活[31],等等,我知道,都知道。”
“但是阁下此言差矣,公爵;我之所以不去您称之为‘那个上流人士的圈子’,那是因为,首先,那里很无聊,其次,那里无事可做!但是说到底,那里我毕竟还是常去的……”
“知道,一年去一趟P公爵家,我就是在那里遇到您的。而在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您就沉湎于您那民主主义的自尊自豪里,在你们那阁楼上为伊消得人憔悴,虽然你们那帮人并不个个都这样。也有那么一些人,偏好猎奇,连我都觉得恶心……”
“我求您了,公爵,换一个话题,别再提我们那些阁楼了,好不好。”
“啊呀,我的上帝,您居然见怪了。话又说回来,是您允许我跟您友好地说话的。但是,对不起,我还没做什么来配得上您对我的厚爱。这酒还行,您尝尝。”
他从他的酒瓶里给我倒了半杯。
“瞧,我亲爱的伊万·彼得罗维奇,我很清楚,硬跟人家交朋友是有失体面的。要知道,我们当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您想象的那样对您无礼而放肆,嗯。我也很清楚,您屈尊跟我坐在一起,并非出于您对我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我答应过跟您谈谈。不是吗?”
他笑了。
“因为您在照管某个小妞的利益,因此您想听听我说什么。是这样吗?”他带着刻薄的微笑加了一句。
“您没说错。”我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我发现他属于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只要看到有人哪怕只有一丁点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就会立刻让他感觉到这点。当时我就处在他的掌握之中,不听完他打算说的一切,我就走不了,他对此是一清二楚的。他说话的口吻突然变了,而且变得越来越狎昵和放肆,越来越充满嘲弄)。“您没说错,公爵;我正是为了这事才到这儿来的,否则,说实话,我才不会……这么晚坐这儿呢。”
我本来想说:否则我才不会留下来陪您呢,但是我没说,而是换了一种说法,倒不是因为怕,而是出于我那该死的弱点和讲究礼貌。怎么能当着人家的面出言不逊呢?尽管此人就配这样对待他。尽管我也很想说几句挖苦他的话!我觉得公爵从我的眼神中已经看出了这一点,他在我说这话的时候一直讥讽地看着我,仿佛在欣赏我的怯懦,又好像在用眼神故意挑逗我:“怎么,你不敢,你害怕了,可不是吗,小老弟!”想必是这样,因为我一说完他就哈哈大笑起来,并且用一种既宽容大度又不失亲切的神态拍了拍我的膝盖。
“你真逗,小老弟。”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这样的意思。“且慢!”我暗自寻思。
“我今天很开心!”他叫道,“而且,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的,是的,我的朋友,是的!我想说的正是这妞。心里有话,就应当彻彻底底地说出来,说出一个结果来,我希望这一次您能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到伯爵夫人家之前,我曾经跟您说到这笔钱的问题,说到那个傻瓜蛋父亲,一个六十岁的老小孩……哼!现在就不必提他啦。我也无非是随便说说而已!哈哈哈,要知道,您是搞文学的,应该明白我说这话的意思……”
我诧异地望着他。看来他还没醉。
“嗯,至于说到那妞,说真格的,我尊敬她,甚至喜欢她,真的;她有点小脾气,但是正如五十年前人们所说:‘没有不带刺的玫瑰’,又说,而且说得好:虽说刺扎人,但是正因为扎人才迷人,虽说我那阿列克谢是个大笨蛋,但是我已经多多少少原谅他了——这小子有眼力。简而言之,这种姑娘我喜欢,再说我(他意味深长抿紧嘴唇)甚至另有打算……好啦,这是后话……”
“公爵!我说公爵!”我叫道,“我不明白您怎么这样出尔反尔,但是……还是换换话题吧,求您了!”
“您又急了!嗯,好吧……换换话题,换换话题!不过我倒想问您个问题,我的好朋友:您很尊敬她吗?”
“自然。”我无礼而又不耐烦地答道。
“嗯,您也爱她?”他接着问道,令人厌恶地龇牙咧嘴,眯起了眼睛。
“您忘乎所以了!”我叫道。
“好了,不了,不了!请稍安毋躁嘛。我今天心情特别好。好久都没这样开心了。咱们要不要喝点香槟?您意下如何,我的诗人?”
“我不喝酒,不想喝!”
“快别这么说!您今天一定要陪我。我今天的情绪特好,因为我的脾气已经好到多愁善感的程度,因此我不能独自开心,幸福应该同享嘛。谁知道呢,咱俩喝来喝去,竟会喝成个莫逆之交也说不定,哈哈哈!不,我的年轻朋友,您还不知道我的为人!我相信,您一定会喜欢我的。我希望您今天能跟我同欢乐,共忧愁,同快乐,共落泪,虽然我希望我至少不会哭出来。怎么样,伊万·彼得罗维奇?您只要想想,如果您不照我的意思办,我的灵感就会不翼而飞,烟消云散,您就什么也听不到了;嗯,您之所以待在这里无非是想听到些什么。不对吗?”他又放肆地向我挤眉弄眼地补充道,“那,请您选择吧。”
这威胁决不能等闲视之。我同意了。“该不是他想把我灌醉吧?”我想。趁此机会,我想提一下关于公爵的一则传闻,而这传闻我早就听说了。据说他在社交界虽然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可是有时候却喜爱夜间纵酒作乐,直喝得烂醉如泥方才罢休,他喜欢偷偷摸摸地寻花问柳,丑恶而又神秘地淫乱无度……我听说过一些有关他的可怕传闻……据说,阿廖沙也知道父亲有时酗酒,可是却对大家讳莫如深,尤其不让娜塔莎知道。有一回,他对我说漏了嘴,但是又立刻把话岔开了,对我的追问避而不答。然而,这事,我并非从他那里听来的,老实说,我起先还不信。现在则静观下文。
堂倌送来了酒;公爵倒了两杯,一杯给自己,一杯给我。
“一个可爱的,非常可爱的小妞儿,虽然她骂了我!”他继续道,津津有味地呷着酒,“但是这些可亲可爱的小妞正是这时候才显得分外可亲可爱,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她没准还以为狠狠地奚落了我呢,记得那天晚上吗,把我奚落得汗颜无地!哈哈哈!她脸上的红晕多美呀!您玩女人是行家吗?您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脸陡地一红,会给本来苍白的脸蛋儿平添无限春色?啊呀,我的上帝!您大概又在生气啦?”
“是的,我很生气!”我叫道,已经按捺不住自己了,“我不愿意听到您现在谈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就是说,用这样的口吻谈她。我……我不许您放肆!”
“哎哟!嗯,好吧,依您,换个话题。我这人最好说话不过了。就谈谈您吧。我喜欢您,伊万·彼得罗维奇,您不知道我有多友好和多真挚地同情您啊……”
“公爵,好不好言归正传?”我打断他的话。
“您想说谈谈咱们的事。您一张嘴我就明白您想说什么,我的朋友[32],您大概没料到,当然,如果咱们现在来谈您,而您又不打断我的话的话,咱们就差不多言归正传了。因此,听我接着说下去:我想告诉您,我最最尊敬的伊万·彼得罗维奇,像您这样过日子,无疑会毁了您自己的。请允许我触及一下这个微妙的话题;我说这话是出于友谊。您穷,您向您的老板预支稿酬,拿来还债,用剩下的钱来苦度岁月,也仅够半年花销,还只能喝清茶一杯,您在您那阁楼上战战兢兢地等着,何时才能写完您那部小说,然后向您那位老板的杂志投稿;难道不是这样吗?”
“就算这样吧,但是这一切毕竟……”
“毕竟比偷盗,比奴颜婢膝,比收受贿赂,比玩弄阴谋诡计,等等,等等要光彩。我知道,我知道您想说什么;这一切早写在报刊和书本上了。”
“因此您也就不必谈我的事啦。公爵,难道还要我来教您怎么保持礼貌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