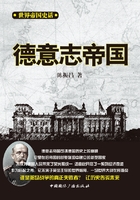他盯着她推过来的纸巾,一动不动。
他的脸色平常,她却知道他在挣扎,她微笑等他的答案。
良久、良久,他终于又推了回来:“陆小姐,我对找替身和取暖都没有任何兴趣。”
“哈哈哈哈哈哈哈——”
陆繁星捶着桌子狂笑了起来。“妙啊!”笑完还摇头晃脑地品了起来,“这句话太妙。‘什么童年?如果是你这种的话,确实没有’,哈哈哈,妙啊。帅哥,你这句话太酷了。以后别人问我说,你不懂廉耻吗?我就说,哪种廉耻?你这种的话,确实没有。哈哈哈哈——”
她笑了好一阵,才发现这个戴银框眼镜的男人从头到尾都不动声色地看着她,唇边带着他惯有的似笑非笑。
她吐了吐舌头:“不好意思,激动过头了。帅哥还有没有类似经典,再来几句听听?”
“你可以去看周星驰。”男人淡淡开口,建议道。
“星星哥啊?我有看的。我每次手上有筷子就会情不自禁——”陆繁星嘿嘿一笑,拿起筷子就敲起碗来,“小人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那唐伯虎,勾结官府目无天,抢我大屋占我田,我爷爷和他来翻脸,却被他一棍来打扁,我奶奶骂他欺善民,却被他捉进唐府,强奸了一百遍啊一百遍——老板!你这碗买得不好,高音不准,中音不甜,低音不沉,总之一句话,就是不够通透呀!”
光头老板这时候大概已经有冲动想进厨房拿菜刀了。NND,人家是开面店的,又不卖音响又不拍《无间道》,要那么通透做虾米?!
男人抱歉地对老板笑了笑。
男人……哈,她为什么要称呼他男人?
她见过他最落魄的时候,他见过她行乞的样子,他请她吃面,她的挑剔和佯狂足以吓走所有接近的人而他却依然坐在这,给别人的感觉他们仿佛是认识了一辈子的交情,可是偏偏彼此却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帅哥怎么称呼?”她咬着筷子,直起笑弯的腰板,又想起两次让他签名都没签,“还是帅哥你是做卧底的,三年又三年,到如今已经九年了,名字不可以随便说?”
男人笑着摇了摇头,拿筷子蘸了蘸汤汁,在红木桌上龙飞凤舞地写下隐隐约约的三字行书。
“雷——煦——明——”随着他的筷子,她一字一字地念,然后嫌弃地从鼻子里哼哼,“三个字啊,好难打招呼的,有没比较方便的叫法?比如小明、明明、阿明,明儿——”
“你可以叫我雷。”他放下筷子,拿手帕优雅地擦了擦手。
她表情有片刻停顿,尔后了然中掺杂促狭的笑意爬上了她的眼底,一点一点地漾到脸上,很狡猾、很狡猾笑,肩膀一耸一耸地笑:“她——我是说你那个女主角——是这样叫你的对不对?”
他看也不看她,似在对着面前的筷子筒出神,未置可否。
脸皮厚者如她,自然是不会被他冷然而疏远的态度唬住。这摆明就是默认呀。
“嘿嘿嘿嘿,”她笑眯了眼,似乎很好商量的样子,却在下一刻吐出拒绝,“我拒绝。”
他这才转过头,淡淡扫了她一眼。
她套近乎地靠近他:“如果我让你不戴框架眼镜你干不干?”
“给我个理由。”
“没有理由。”她无所谓地摆了摆手,坐了回去,“你不会干的,所以我也不会干的。”她不是他心里的那个人,他也不是她认识的那个人,再像都无法替代,他们也不愿意替代。
他懂了,点了点头:“随便。”
“当当当当,青春无敌美少女名字要闪亮登场啦。”她张罗起她的出场介绍了,从桌上拿了张黄色的纸巾,拿笔在上很有意境地勾勾画画了半天,才递了过去,“我比你厚道多了,我写的一定是又好看又清楚。”
陆繁星三个大字写在纸巾的正中,其下是一串号码,右下画了一个脸上有雀斑扎小辫子的Q版头像。她对绘画向来很有天分。
“这个是……”他点了点纸巾上的那串号码。
“我的手机。”报纸上说乞丐也有手机果然并非空穴来风,她想了想又补充了句,“不停机的时候打得通。”没钱的时候她也没办法保证手机畅通。
“我要你的手机没有用。”他隐隐有些不悦。
“打给我啊。”她很不要脸地邀约。
“陆小姐,我们的交情似乎还没有那么深。”他嗓音温醉如酒,吐出的话语依然儒雅斯文,字句却冰冷了起来。
“随便啦。你愿意把这个号码当情色电话打也没什么关系。”她笑嘻嘻,仿佛浑然不觉。
他微笑着,笑意却没到眼底,他将纸巾推了回来:“谢谢,不必了。”
真固执。陆繁星撇了撇嘴,看来只有用绝招了,语调一转,饱含深情:“雷,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你。”
他的表情出现瞬间空白,似乎被什么击中。
她笑了起来,知道自己赌对了,方才她的语气一定和他喜欢的那个女生有九成相似,才会让他出现这副被雷劈的表情。
他镜框后的桃花眼怔怔对着她,瞳孔里是一片茫然,许久才回过神来,忙移开了视线,掩饰地咳了几声:“你一点不像她。”
“像不像你自己明白就好。”她嬉笑着又将纸巾推了回来,料他拒绝不了似的,“可以听很多其他的话哦,我爱你啊我喜欢你啊我爱死你了啊之类的,你可以点哦,只有想不到,没有说不出口的。”诱惑他诱惑他拿糖果诱惑他,哈哈。
他盯着她推过来的纸巾,一动不动。
他的脸色平常,她却知道他在挣扎,她微笑等他的答案。
良久、良久,他终于又推了回来:“陆小姐,我对找替身和取暖都没有任何兴趣。”
她暖暖笑开:“那真是太好了,我也没有任何兴趣。”
场面僵了一会儿。
“你一定是个生意人。”陆繁星皱了皱鼻子,很是不满。真难伺候,她都花重本钱了,居然还不上钩。
雷煦明往后一靠,将身体的重量都交付给椅背,双手的手指在腿上自然交叉,并不给正面的答案:“怎么说?”
还需要怎么说吗?
“你身上的市侩气味飘过来了。”陆繁星拿手在鼻前扇了扇,觉得有什么臭不可闻。她语带鄙夷:“像你这样的人,一定是碰到什么好事都觉得有陷阱在里面,像你这样的人,一定是绝对不相信会有只利自己的事,所以一碰到什么别人毫无目的地付出就有即将上当的警觉。”
她一口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完全是已经替他定了罪了。
他不为所动,继续噙着淡淡微笑看她还准备说些什么。
“不过,嘿嘿,”方才还在横鼻子竖眼的,一个“不过”她马上又笑成了一朵花,讨好人的喇叭花,“我确实是有目的啦。”
他的眼中闪过“果然”二字,嘲讽地勾起嘴角。
“别误会,这个目的跟您老人家的感情和肉体都没有任何关系——”她想了想,又改口,“好吧,就算和肉体有一点点关系好了……”
“老板,结账。”他从口袋中摸出皮夹,抽出大票。
真不好玩,这样震撼的话语砸到他那,他一点反应都没有。陆繁星扁扁嘴:“我只是希望我偶尔提供情色服务的时候,你也能和我坦诚相见。”
“多坦诚?”他平稳地问,将找回的钱放回钱包里。
“很坦诚!”她玩兴大起,不过马上在他“老子耐心有限,最好给我说重点”的目光下老实开口,“不戴眼镜就好。你知道的,要碰上你正好被人揍很容易,可是揍得眼镜正好掉了,就太难了。”
她只是想偶尔能够见到那张记忆深处,许久未见,今后恐怕也见不到的容颜……
“成交。”她微一走神的同时,他已经抽走了她手指下压着的纸巾。
吼!这男人!
“你经常那么直接给女生难堪吗?”她蓦然想起方才他误会她对他精神或肉体有染指欲望时候的冷然疏远。并不是说他本身是让人无距离的,只是在那一突然间,他的距离感忽然就加强了。
他知道她问的是什么:“不让人有超出实际的期待是我做人的原则。走吧。”他起身,对老板微微颔首,和她一前一后走出了面馆。
“才怪,我看你是经验老到,先说清楚了,以后谁有什么或者让你占什么便宜都是人家活该。你们男人都这样。”
“男人是有这样的,但不是每一个都一样。”
“哈,”她笑了一声,表明不信,“男人才做不到灵肉合一呢,送上门的又说清楚的,谁会放过送上来的肉?”书上都是这样写的呀。
“食人族里都有吃素的,正常人类里更多,在别人眼里是肉也许他眼里是砒霜。”走到弄口,他停住脚步,一手插在裤袋中,一手拦车,并不看她,也不打算解释更多的样子,“我要去上班了。你怎么回去?”
“不要担心。”她笑嘻嘻,她张开手做了个飞的动作,“我会飞。”
“飞高些,这段路高架多,不要把高架撞坏了。”他随便附和了句,拉开TAXI的车门,坐了上去。
雷煦明坐在出租车上向后望。
不知怎的,总觉得陆繁星望着车子远去的单薄身影很低落的样子。他知道,她又在透过他在看那个人了。
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子,也曾经说过他不戴眼镜的样子很像一个人,一个她曾经喜欢过的人。
那天晚上,便是这同样的一句话,锁住了他离开的脚步。
不想这些了。
他搓了搓脸,觉得有些疲惫,想起自上次相亲后都没回过老家,于是回到自己店里和下面的人交代了声,便开车回去承欢父母膝下。
可惜承欢的时候,连打了好几个呵欠,两老看不下去了,让他回楼上年少时的房间好好休息。
他几乎一沾枕就睡了过去,直到敲门声将他从睡梦中拉了出来。
睁开眼,房间里的摆设有那么一秒让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昏暗的光线让他产生时间错落感,不知道自己究竟睡了多久,现在到底是早还是晚。
“来了。”他沉沉地应声,随手抓了件睡衣,边扣纽扣边打开了房门。
“你表姐和表姐夫来了,下去见见,顺便把晚饭吃了再睡。”丁蔼然抬起手理顺了他几缕翘起的头发。
“好的,妈,我换件衣服就下来。”雷煦明微笑着说。
“都是自己家的人,哪那么多规矩。”丁蔼然不以为然。
“很快的。”他将母亲反转身送至楼梯口,回房换了件衬衫才下去。
丁姗姗一见他下来就笑了:“姑姑,你那么客气做什么,小雷在睡就让他睡嘛,我和阿伟也只是办好事路过进来看看,一会儿就走的,小欣还在家让保姆带着呢。”
丁蔼然拍了拍她的手:“那么久没见了,虽说你们现在都搬到杭州了,可是总也难得过来几回。”
丁姗姗是丁蔼然娘家那边的亲戚,原本是在温州老家的,因为陆伟升职调到了省里,才一并跟了过来。
他坐到雷如东的旁边:“表姐近来气色越发好了。”说这话时,眼睛看了一旁的陆伟一眼,算是打过招呼。
陆伟是丁姗姗第二个丈夫,仪表堂堂,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只是四十来岁的模样。当初丁姗姗被第一任丈夫暴打时,便是在法院的陆伟帮她从家暴中解脱出来,也是这样产生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