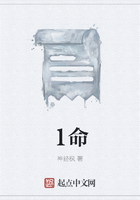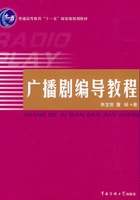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许多革命者为民族解放奋不顾身,无力照顾自己的儿女,还有许多革命先驱抛头颅洒热血牺牲在革命征途上,他们的儿女就成为了孤儿。
为了给世界革命者解除后顾之忧,1933年苏联政府在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小城建立了一所特殊学校,就是伊万渃沃国际儿童院。这座三层高的红色砖房曾收留过85个国家2000多名儿童。来自中国的117名红色后代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不平凡的童年。
这些红色后代大多数或跟随父母,或由组织派人护送,秘密走中东铁路出境,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2008年9月,笔者在北京寻访到了蔡妮的家。这是一处独门独户的四合院,院子里开满了绚丽的鲜花,83岁的蔡妮坐在藤椅上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蔡妮的家庭可谓非同寻常,堪称红色家族。她的奶奶葛键豪开一代先风,1919年底59岁的她携儿子蔡和森和女儿蔡畅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蔡妮的母亲向警予也随行其中。1920年,蔡和森与美貌的向警予在法国留学时结婚。蔡和森的母亲葛键豪对同在法国留学的李富春印象很好,认为李富春很有出息,她便支持女儿蔡畅与李富春处朋友。后来,蔡畅与李富春也在法国留学时结婚了。在葛键豪这位女中豪杰的引领和鼓励下,她的儿子蔡和森,儿媳向警予,还有女儿蔡畅,女婿李富春都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解放后,蔡畅成为新中国首任妇联主席,李富春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蔡妮的父母都是中共党史上彪炳史册的翘楚人物,她的母亲向警予是中共中央第一位女中央委员,是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她的父亲蔡和森是毛泽东的同学和挚友,是中共蝉联五届的政治局委员,是党的“五大”“六大”政治局常委。
谈及母亲,83岁的蔡妮对笔者说:“我小时候的印象,母亲向警予长得非常漂亮,工作太忙了,很少能见到她,我幼年时生活在奶奶的身边。记得有一次,妈妈赶到长沙奶奶家,对奶奶说,让我带女儿睡一宿吧。妈妈搂着我,用手轻轻地拍着我,在妈妈好听的儿歌中,我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听到了妈妈的呼吸,妈妈醒来后又将我抱在她的怀里亲吻了我的脸颊,然后又为我唱了两首悦耳动听的法国歌曲。我当时竟然有些羞涩,因为和妈妈在一起的机会太少了,对妈妈有些陌生。这次和妈妈在一起是我最难忘的甜蜜的记忆。”
“我妈妈在我3岁时,1925年去了苏联,是从上海坐船到大连,再坐火车到哈尔滨,走中东铁路从满洲里出境去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两年,1927年回国的。”
1928年,向警予不幸被捕,美丽而坚贞不屈的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委员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年仅33岁。
母亲壮烈牺牲时,蔡妮只有6岁。
父亲蔡和森对永失母爱的蔡妮,关爱有加,他经常挤出时间看望照顾蔡妮生活的老母亲和女儿。每次到长沙,他都会特意给女儿带上一些好吃的和女儿喜欢的洋娃娃。
蔡和森曾经4次远赴苏联,他的行走路线都是从南方来到哈尔滨,接着坐中东铁路的火车到满洲里再出境赴莫斯科。
1929年秋天,在长沙奶奶的家里,蔡妮看到大人们都开始忙碌起来,奶奶为她赶制了好几件衣服,姑姑蔡畅还亲手为她织了一件橙黄色毛衣,蔡妮很高兴自己拥有了这么多好看的衣服,更让她感到高兴的是,爸爸要和她一起走,带她出远门。
蔡妮好奇地问奶奶和姑姑,出远门到底要走多远呢?
奶奶葛键豪和姑姑蔡畅不能明确告诉蔡妮走多远,要到什么地方,因为此行是秘密的。她们只是叮嘱蔡妮一路上要听爸爸的话,同时难免对只有7岁的蔡妮恋恋不舍。尤其是年逾花甲含辛茹苦常年照顾蔡妮的奶奶,明白和疼爱的孙女在此一别,意味着什么,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她从头到脚细细地打量着朝夕相处的孙女,俯下身来轻轻地捧着蔡妮的笑脸看了又看,不知所以然的蔡妮有些纳闷地望着奶奶那充满慈爱和牵挂的眼睛,心想:这是为什么呀?
蔡妮对笔者说:“我在苏联学习和生活了24年,回国后,我第一个想看的人就是奶奶。姑姑蔡畅告诉我,奶奶没有等到孙女回来,已离开人世了。这时我明白了当年我和奶奶告别的时候,她为什么对我瞧个不停,看了又看啊。”
接着,蔡妮回忆了1929年的冬天,爸爸蔡和森提着一个小皮箱带着她一路北上的情景。蔡妮说:“我们从南方先是坐船,然后坐火车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还去照了相,父亲说要把我的照片寄回长沙,给奶奶和姑姑看。从哈尔滨又坐上火车走中东铁路到了一个寒冷的地方,那就是满洲里。满洲里风雪交加,冻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记得来了一个陌生的叔叔,就是交通员吧,带着我们在夜晚出境的,后来坐火车到了莫斯科。这一路的路程实在太漫长了,有半个多月吧,我都惊讶了,爸爸带我出远门,原来是去了另一个国家。”蔡和森此行去苏联,是党中央安排他到莫斯科治病,同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初到莫斯科,蔡和森被临时安置在联盟宾馆一个比较窄的房间,只是一张单人床,7岁的蔡妮和爸爸挤在一起睡,爸爸的呼吸和温度,让蔡妮禁不住想起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的那个夜晚。
蔡和森还带蔡妮到莫斯科公园游玩,爸爸牵着她的手,坐进了“过山车”的座椅里,并为她系好了安全带,笑着说:“女孩子也要学会勇敢和坚强。”蔡妮认真地点了点头说:“爸爸,你放心,我会做到的。”
清脆的铃声一响,“过山车”开始缓缓地启动,接着开始逐渐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高,到了最高处,几乎远离地面有5层楼的高度,悬在高空中稍停片刻,倏然间,猝不及防,猛地来了一个大翻转,坐在座椅的有人来了一个头朝下的大翻身,急速坠落,伴随着游人“啊,啊”的惊叫声,眨眼功夫,“过山车”已将人带入平地,然后又是急速上升,升高到空中。忽高忽低,忽快忽慢,周围的景致如万花筒般飞速变幻,这让蔡妮有些惊恐。
游戏结束后,下了“过山车”的蔡妮扑到爸爸的面前,她搂紧了爸爸有些瘦弱却高高的身体,内心逐渐平稳了下来。
爸爸牵着她的手问她:“怎么样,好玩吗?”蔡妮回答:“太好玩了,刚才是有些害怕,现在觉得还没玩够呢。”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人生不都是平坦的路,肯定会经历起起伏伏,曲折坎坷,人要学会勇敢和坚强。”蔡妮似乎明白了爸爸的叮嘱,她摇晃着爸爸的手说:“我记住了,不会忘记的。”
为了让女儿玩得高兴,在碧波荡漾的河水中,蔡和森带着蔡妮划船,坐在船上的蔡妮望着远处岸边那葱茏的绿树和蓝天飘浮的朵朵白云,想起了妈妈向警予曾经给自己唱过的法国歌曲,那歌声犹在耳畔,她还没有听过爸爸唱歌,于是,她就让爸爸给她唱首歌。
蔡和森一边划船,一边为女儿唱起了俄罗斯歌曲“喀秋莎”:“正当梨花开遍了原野,河上漂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村庄……”铿锵洪亮、雄浑悦耳的男中音,在悠悠流淌的水面上回荡。歌声伴着划桨声,在水面上荡起了层层的涟漪,蔡妮禁不住为父亲动人的歌声鼓掌喝彩。她觉得自己被浓浓的父爱环绕,心旷神怡,陶醉不已。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需要工作和治病的蔡和森将女儿送进了莫尼诺国际儿童院。
1930年深秋的一天,秋风萧瑟,落叶飘零。
蔡和森踩着满地枯黄的落叶,来到国际儿童院,向8岁的女儿蔡妮告别,并与儿童院主任打招呼,要将蔡妮长期留在儿童院,请他们照看。
蔡和森看到天真活泼的女儿对儿童院已不陌生,开始学着用俄语和小朋友交流,并已融入了集体生活,感到很欣慰。蔡妮笑着对爸爸说:“我记住了,生活要学会勇敢和坚强。”蔡和森听了女儿说的这句话,高兴地笑了。临别前,蔡和森留给女儿蔡妮一张照片作为纪念,那是他在疗养院修养时穿一身白色的西装照的。
蔡妮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一别,竟是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蔡和森回国后不久,1931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
蔡妮6岁时失去母亲,9岁时又失去父亲,从此她成了漂泊在异国他乡的孤儿。父亲牺牲后的她“长期无人认领,失去与亲人联系,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1933年,蔡妮在黑海古尔祖夫夏令营度假,恰好李立三也在。他一眼认出蔡妮是蔡和森、向警予的女儿,就把她抱在怀里,高兴地说道:“我是你父亲的战友,我认识你!”李立三把她父亲遇害的事告诉了她,并要她“长大后为父亲报仇”。蔡妮后来回忆说:“跟李立三的偶然相见,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李立三为我做了很多事,帮我跟国内亲人联系,我很感激他。后来是他送我进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在苏联莫斯科度过了24年的漫长岁月,蔡妮在莫斯科医学院毕业后于1953年回国,成为了一名新中国急需的优秀医务专家。
父亲蔡和森对女儿一再叮嘱的那句话,一直伴随着蔡妮的成长历程,在人生风雨的磨砺中,蔡妮渐渐地真正感悟到了父亲的叮嘱究竟意味着什么。
和蔡妮出国时的年龄一样,同样是7岁的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1928年5月下旬在母亲杨之华协助完成哈尔滨“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工作后,同母亲一道从哈尔滨坐中东铁路火车经满洲里出境远赴莫斯科。
党的“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留在了莫斯科,杨之华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培训班学习。由于父母的工作学习非常繁忙,瞿独伊被送进了由苏联红色救济会组建的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后来转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她在苏联学习和生活了近15年。
2009年10月,笔者在北京见到了瞿秋白的女儿,88岁的瞿独伊。经历了物换星移岁月沧桑,她依然珍藏着父亲瞿秋白当年寄给她的明信片。明信片正面是才华横溢擅长绘画的瞿秋白亲笔画的“勿忘我”的花束,一束“勿忘我”在几许绿叶的衬托下,开满了白色的花蕊,花很小,却很茂密,在空白处,依然有蹿出的花瓣在绽放,溢满了活力,透出了淡雅、别致、隽永、灵动的情趣。侧面是瞿秋白用中、俄文书写的文字:“送给独伊。爸、妈于1930年8月1日,克里米亚。”
随着岁月慢慢流转,明信片通体都有些泛黄。可是那束溢满了父亲深情厚爱的“勿忘我”,依然风情摇曳,栩栩如生。
当时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和杨立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定期地会去探望在国际儿童院生活的女儿。
在采访中,瞿独伊双手捧着异常珍贵的明信片,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她的讲述,让人看到了身为政治家、党的早期领袖瞿秋白作为父亲所表现的鲜为人知的极富温情的一面。
瞿独伊面带微笑地说:“我记得是在1929年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积雪,父亲把我放在雪橇里,他拖着雪橇跑,故意把雪橇拉得忽急忽慢,有时假装跑不动或摔一跤,用手蒙住脸装哭。这时我就喊妈妈:‘妈妈,我跌跤都不哭,爸爸跌一跤就哭,真娇气!’妈妈忍俊不禁地笑着说:‘孩子呀,爸爸是逗你玩呢。’于是大家拍手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回荡在天空中,似乎周围一切都在为我们幸福的一家而快乐。”
“父亲时常给我写信,而且每次都要在信上画一幅画,有山水画,有卡通画,还有漫画,画什么像什么,惟妙惟肖。有一次,他在明信片上画了一个大飞艇,还在旁边写道:‘你长大了,也要为中国建设这样的大飞艇。’父亲就是这样激励我要为将来建设祖国努力学好真本领。”
1930年秋天,因国内斗争的需要,瞿秋白和杨立华告别了已经9岁的瞿独伊,从苏联返回了中国。
此时的瞿独伊虽然远离了父母,可是她已经如鱼入湖般完全融入了国际儿童院的集体生活,不仅和中国而且和外国的小朋友都能和睦相处,成为亲密无间的小伙伴。
就在她快乐成长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将她充满玫瑰色的生活撞击得粉碎,让她少女的心灵猝然间颤抖不停。
在北京的家中,回忆到了最伤心的事,88岁的瞿独伊还是止不住伤感,她语调低沉地对笔者说:“我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经历的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是我永远失去了爱我的父亲。”
“那是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儿童院的一批孩子在乌克兰的一座城市参观,苏兆征的儿子苏和清在附近的橱窗阅报栏里好像发现了什么新闻,他匆匆过来告诉我,让我到阅报亭那边去看一看。我忙过去浏览俄文报纸,忽然从《共青团真理报》看到了父亲瞿秋白牺牲的消息,我惊呆了,感觉天旋地转,两条腿软绵绵地不停抖动,站都站不稳了。苏和清还有别的同学赶紧过来扶住了我,我止不住失声痛哭起来,那一年我才13岁。”
在茫茫人海中,这些烈士的子女,如一叶叶脆弱不堪的小舟,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人民却赋予了他们大海般的博爱和深情,让他们扬起了希望的风帆,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和雨露,得以健康地成长。
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就陆续建起了孤儿院、幼儿园,来收养革命者的后代,为革命者解决后顾之忧。
1933年建立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从建筑规模、环境、设备和教学规划及布局上,都堪称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