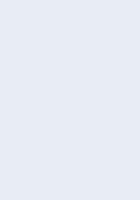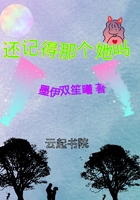假若脑海里有一块橡皮擦,我最想做的,是狠狠擦掉2009年至2010年这两年的记忆,一场关于易小天的记忆。
易小天,于我而言,是永远不能言说的伤,藏在我心底深处,不见天日。我不想轻易去撕开这块旧伤疤,不想去重温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但在这个故事里,我又必须说服自己去回忆、去记录有关于他的一切。因为只有这样,这个故事才可能讲述完整。
我该怎么去叙述你呢,易小天?原谅我,如今时过境迁,有很多关于你的点滴,我都不愿意去细细回味,我也没有太多的心情去缅怀你这个生命中的过客,我只愿意用极为平淡的笔触去还原这个故事的本真。
那么便从相逢的刹那开始写起罢。
2009年大年初六的晚上,我持着那张无座的票,挤在了那趟从N城开往北京西的特快列车里。
整个硬座车厢就像一个密封的沙丁鱼罐头,座位上、座位下、过道里挤满了前往北京的旅客。大大小小的行李堆在了过道上,行李的间隙塞满了人,有人蹲着,有人垫着报纸坐着,有人干脆躺着。我挤在一个靠近洗手间的位置,和别人几乎面贴面,呼吸着别人的呼吸,看着手机上爬得像蜗牛一样慢的时间,真有种无比煎熬的感觉。
我的旁边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长相猥琐,口气难闻,总是装作不经意地挨着我蹭。我往后缩一点,他前进一点,我越是忍耐,他越是肆无忌惮。我夹在人缝里,被挤得无处可逃。
正值烦不胜烦之时,我挨着的那排座位中,靠窗那个座位上的人站了起来,对我说:“哎,那个小姑娘,过来坐我这里吧!”
我连忙转过头,像遇到救星一般地看着他说:“谢谢。可是你……”
他笑着摇了摇头说:“没事,我坐得够久了,想站着活动下筋骨。”
就这样,我坐在了他原本坐着的座位上,并冲他感激地一笑。这个热心的男子就是易小天。我永远记得第一眼见他时的模样,身形瘦削,皮肤黝黑,其貌不扬。他的嘴唇很薄,鼻子很突出,有一双狭长的眼,眼里闪着精明的光。很久以后,我才从相书上知道,这样面相的男人,注定薄情寡义。但二十七岁的沈明欢,从不以貌取人。况且她彼时受恩于他,自然对他另眼相待。易小天站起来,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萍水相逢的沈明欢。他去了趟洗手间,又在过道上站了一会儿,不多时便钻到前方打牌的人堆里,和几个人玩起扑克来。我持着一张无座的票,忐忑不安地接受着这个陌生男人的恩惠。
有好几次,我站了起来,用眼神去寻找他,见他看了过来,便立马问:“你站着累不累,要坐会儿吗?”
易小天大方地摆了摆手说:“你坐着吧,别管我。”第二天中午,列车顺利到达北京西站,下车前我想对易小天再说一声谢谢,可一转眼,他却随着人群下了车,早已不见了踪影。我拖着行李箱走出西站,仰着头在路边等巴士。一辆灰头土脸的银灰色捷达停在了我的面前,易小天从车窗里伸出脑袋。“老乡,我找了你半天,原来你在这里,快上车!”
我摇了摇头。“不用了,谢谢你。我一会儿坐巴士回去。”易小天把车停住,下了车,径直走到我跟前,霸道地接过我的行李,说:“走吧,我送你,别磨蹭了。”然后迅速打开车的后备箱,将我的行李包扔了进去。
我默默地跟着他上了车,坐到了副驾驶位置上。易小天开着那辆银灰色的捷达车,在北京的公路上一往无前。他车技娴熟,将车子开得既快又稳,我甚至隐隐发觉他的身上透出一股狠劲。我还注意到他的烟瘾很大,在征得我的同意后,他一路上抽了好几根烟。
易小天开着车,没话找话。“N城人都跑广东发财去了,来北方的还是比较少的。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跑北京这么远?”
我笑着说:“来北京的N城女孩可不少,你看咱们坐的那趟火车不都是来北漂的N城人吗?”
易小天一咧嘴,笑着说:“你真会巧妙回避我的问题。”
我一扬眉。“哪有。”
易小天说:“你觉不觉得在北京生活久了,咱们就变成夹心人了?在这里生活得很边缘,回到N城又感觉融入不到过去的生活里。”
“真是这样。”我点了点头,表示深刻赞同。易小天说:“不过这样也很好,与其在N城过一潭死水的生活,不如在颠沛流离中享受生活的每一天。趁年轻,折腾下挺好。”我笑了笑,不置可否。每个人对生活都有自己的追求,有人喜欢平淡安逸,有人喜欢折腾刺激,我歪头看了一眼正开着车的易小天,他的眉眼间透露出几分轻狂,言行举止间藏着某种率性。在当时的沈明欢眼里,这是一个谜一样的男人。
到了劲松,易小天直接将我送到了楼底下。等我下车时,他叫住我说:“哎,老乡,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一字一顿地回答:“沈明欢。日月明,欢喜的欢。”易小天爽朗一笑,说:“沈明欢,有时间一块儿出来玩,我来找你。”又是这种不容拒绝的语气。后来我越发注意到,易小天待人接物直接而强势,不给人留有余地。我的固执与坚守,从来只适合应付优柔寡断的人,而在易小天面前,我变得软弱无力,总是进退两难。
我已独居太久,内心既空虚又孤寂,也许正适合人走进来。易小天适时地弥补了我的这份空虚,他像一个天外来客,开始频繁地降临在我的生活中。三月末的一天中午,在劲松附近的一家湘菜馆里,坐在我对面的易小天对我说:“沈明欢,我已经把你当成我的女朋友了。你呢?”
他的语气漫不经心,眼神却咄咄逼人,我不由得心里慌乱。
为了掩饰我的慌乱,我故作调侃:“易小天说什么呢你,别瞎开玩笑。”
易小天点燃了一根烟,吐出一口烟圈,轻描淡写地说:“谁跟你开玩笑,我是说真的。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我脸上一窘,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一板一眼地说:“到了我这个年纪,谈恋爱就是奔着结婚去的。易小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只是玩玩爱情游戏,请不要找我,我是个很认真的人。”
易小天哈哈大笑。“你还真有意思,你是想对我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就是耍流氓’对吧?放心,我不耍流氓,我也是认真的。”
见他言之凿凿,又十分坦然的样子,我反倒心虚起来,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易小天扬眉一笑,说:“你不说话就当你默许了啊。”“好吧,给你一个试用期。”我无奈地答应。“还有试用期的,多久?”他睁大眼睛瞅着我,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我笑着说:“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这时服务员开始上菜,易小天掐灭了手中的烟,夹了一筷子小炒肉送到我碗里,自己也尝了一口,撇着嘴说:“这小炒肉光见辣椒不见肉,还不如我自己做的好吃。”
我笑着说:“你嘴挺挑的,还不忘吹嘘自己的厨艺。”易小天说:“你不相信啊?这样吧,一会儿去我那里,晚上我做一顿正宗的湘菜给你尝尝。”我犹豫着没说话。
易小天催我表态。“别犹豫了,去吧。我想好好表现早点通过试用期,你也得给我机会啊,是不是?”
我点了点头。“好吧。”去了我才知道,易小天住在定福庄,就在先前我和姚小遥租的地下室相邻的那个小区。那个小区配套设施良好,里面有一个大的健身区,以前我和姚小遥经常在下班后去那里荡秋千。那时候我刚来北京,对这个城市还怀着许多美好的憧憬,我和姚小遥经常在这一带散步、聊天。现在故地重游,不禁思绪万千。
易小天见我熟悉路,便问:“你来过这里?”我笑着说:“何止来过,我先前就住旁边那个小区。”易小天一脸的恍然大悟。“我说怎么在火车上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眼熟,我肯定在这附近见过你。”我问:“你什么时候搬来这个小区的?”易小天说:“去年买的房子呀。”我撇了撇嘴,说:“撒谎不打草稿,还说见过我,我两年前就搬走了。”
易小天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又觍着脸笑着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哦,对,就是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不由得扑哧一笑。下午的时光转瞬即逝。陪易小天去小区附近的菜市场买了杭椒和五花肉,又买了一条大鲤鱼和一些蔬菜。我负责做红烧鱼,易小天负责做小炒肉外加一道清炒油麦菜,晚餐香喷喷地出炉。
吃饭时,我赞他做的小炒肉不错,他将我做的红烧大鲤鱼全部消灭干净,直接以行动表示认可。
吃完饭,收拾干净,两个人干巴巴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到了晚上十点,我催他开车送我回去,易小天斜倚在沙发上懒洋洋地说:“回去干吗,就住这儿呗。”
我转头看了看,他所住的房子只有一个卧室、一张床,便摇了摇头,说:“不行,你这里没法住。”
易小天笑着说:“怎么没法住了,你睡我的床,我睡客厅的沙发。”又不忘提醒我,“卧室门可以反锁的。”
“此地无银三百两。”我狠狠白了他一眼。易小天打了个哈欠,说:“说真的,我今天有些累,你又住劲松那么远,我不想开车送你回去了。明天一早,我送你去公司上班行吗?”我只好点头。第二天一早,手机的闹铃声响,我连忙翻身起床,穿整齐衣服。一拉开门,只见易小天蓬乱着头发,睡眼惺忪地站在门外,吓了我一跳。再仔细一看,他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一看就是晚上没睡好。“小样儿,你可睡得真香,晚上敲门也敲不开,给你发短信,周杰伦那首《菊花台》播了好几遍也吵不醒你。”易小天皱着眉头抱怨。我连忙抄起手机去看,果然有易小天凌晨三点发过来的短信:明欢开门,我忘了拿被子出来,这会儿躺沙发上快冻死了……“对不起,易小天,我确实没听见。”我抱歉地看着他。易小天耸耸肩。“算了不怪你,你快去洗漱,一会儿我开车送你去公司。”说着,他使劲打出个喷嚏,果然是冻感冒了。我内心十分愧疚,又对他充满同情,就在这一刹那,所有的心防都卸下。也是从这一天开始,易小天成了我名正言顺的男朋友。现在回头来看,易小天就像我在寂寞天地里随机寻找到的一个舞伴,音乐声响起,我闭上眼跟着他的脚步,旋转着、旋转着,最后晕眩在他的世界里。
四月末,可怜的更生感染了犬瘟,寄养在动物医院打了半个月点滴,病情一直反复,我只得把病入膏肓的小家伙接回了家。这时候的更生,持续便血数天,眼睛已经毫无生气,像一颗实心的桂圆核,不再黝黑透亮,完全丧失了神采。它奄奄一息地躺在阳台上,一动也不动,微弱地呼吸着。之前在网上查阅许多关于犬瘟的资料,知道更生这种症状,几乎是回天乏力了。
我实在很无助,打电话和易小天说更生的事,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易小天却不以为然。“你可真脆弱,一条小狗都让你哭成这样。”可更生对于我来讲,不止是一只小狗那么简单。两年来,它与我朝夕相伴,我是它的整个世界,而它是我精神上的寄托。夏虫不可以语冰,易小天淡然的语气中带有几分不屑,一不小心就刺痛了我的心。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控诉他。“易小天你可真是没有同情心,你以后会不会对我也这样薄情啊?”他连忙在电话里哄我。“你瞧你,快别哭了,你心情不好,我这就过去陪你。”
易小天来的时候,扛了一大袋狗粮。我给更生喂食,它只是轻微地嗅了几下,脑袋又耷拉下去。我勉强喂了几口,不一会儿,它又全部吐了出来。
我把它抱在怀里,坐在卧室里的凳子上,被不祥的预感袭击,一下子悲从中来。见它萎靡不振的样子,忽然觉得压抑、难过,甚至愤怒。虽然它不懂我的表达,但我还是冲着它一边哭一边骂:“你这只小坏蛋,你太坏了,你想气死我是不是?谁要你生病的?谁让你生病的?气死我了……”
更生抬头看着我,缩了缩鼻子,湿热的鼻息夹杂着涕液喷到我的脸上,它的眼神很无辜,有点不明所以的天真。仔细看,它右眼潮湿了一阵,但始终没有东西流出来。易小天在阳台上接完电话,进来见我正抱着更生哭,长长叹了口气。
那一刻我不觉得自己太癫狂。虽然一直知道,太多的情感,寄托在一只小动物身上,本来就有点牵强,更何况更生一直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又有何种义务来承载我汹涌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