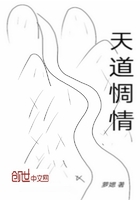我们进了大门。根据向导给我们的描述和从远处得到的印象,我想这一定是一座宫殿式的建筑物。可是大失所望!
它虽然高大,但是有一半已经坍塌。门窗残缺,室内空空,屋顶破损,墙砖裸露。墙顶上的瓦久经风雨,铺着一层厚厚的灰尘。
高大而宽阔的大门前,有一个男子在迎接我们,他拉长的、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使我们感到很不自在。
“这是胡穆姆,阿迦的侍从。”苏耶夫介绍说。
我们马上就遇到我们要提防的人了!他向我们深深鞠了一躬,指着两个站在我们后面的强壮的人说:
“长官,我的阿迦不幸地听到,你不能行走。因此,他命令我,派这两个人来抬你。他们力气很大,你完全可以放心。”
我下了马。两个被指定的人各伸出一只胳膊,互相交叉,用另外两只手抓住。我坐在他们的手上,靠着他们的胳膊,构成了一乘轿子。我被这乘轿子抬着,经过过道,穿过两间房,进入客厅。我的同伴们跟在后面。裁缝却不见了踪影。
这个客厅布置很简单。墙边放着一排长沙发。对着客厅正门的沙发高一些,宫殿主人坐在上面。他的旁边还有一张类似的高沙发,是为我准备的。他的座位前面有几个位子是给我的同伴们的。两个轿夫抬着我在门前停下脚步。阿迦鞠了一躬,没有站起来。他说:
“欢迎,长官!安拉恩赐你进入我家,并让你和我待几天。不好意思的是,我不能起身。脚痛风弄得我腿痛,使我不能动。只好派人抬你到我这儿来,坐在我的右边。你的同伴们可以在我前面歇息歇息。”
他们把我放到他身边,其他三人则坐在他对面。我说了几句表示感谢的客气话。他抱歉地打断我的话,说要表示感谢的不是我,而是他。轿夫们走了,侍从拿来了烟袋和咖啡。在东方,人们习惯于从烟袋质量来评价一个人的富裕程度。按这种标准衡量,穆拉德是个很富的人。他抽的和递给我的烟袋,都是用正宗花梨木做烟筒,上面缠着金线,饰以珍珠宝石,花边都是豪华的,琥珀是半透明的。在东方,这种琥珀比全透明的贵得多。小巧玲珑的无耳瓷杯放在金碟上面,金碟是透雕细工。说实话,我在这儿喝的咖啡比在开罗喝的品质还好,是按东方的方法加细盐泡制的。咖啡杯小的可爱,只有四个顶针那么大。
烟叶也是上好的。可惜烟袋头太小!抽上十多口,就得重新装烟叶。由他的贴身侍从胡穆姆装烟袋。
懂礼貌的人都知道,对客人不能一见面就问东问西,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聊聊。慢慢的,穆拉德的话题逐渐深入。他问:
“今天旅途愉快吗,长官?”
“还好。”我回答。
“阿夫里特,就是那位裁缝,告诉我,你是从什格曲来的?”
“我是昨天到那儿的。”
“在那之前?”
“在拉多维什和奥斯特罗姆察。”
“这么说来,你每天都在旅途中?”
“是这么回事,因为我是从埃迪尔内和伊斯坦布尔来的。”
“从伊斯坦布尔!安拉对你真好,让你出生在这个都城!”
“我不是那儿出生,而是从大马士革经过巴勒斯坦到那儿去的。”
“原来你是大马士革人?”
“也不是。我是法兰克人,即阿拉曼人,从我的祖国出发到撒哈拉大沙漠,再从那儿到埃及和阿拉伯。”
“安拉是伟大的!你的走路那么长的路?你的生意好吗?”
“我旅行不是为了做生意。我想了解各国的风土人情、文化风俗。我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离开家乡的。”
他看着我,表示不相信。
“为了这个目的?安拉!你看这么多山水、人、沙漠和森林,有什么用?你看别人的衣着,听别人的话语,得到的是什么?”
这都是些旧观念,是我常见的。这些人根本不理解,怎么会有人以拜访陌生的人民和国家为兴趣。他们只知道赚钱、朝觐,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喜欢地理?”我问他。
“很喜欢。我喜欢读这类书。”
“谁写的,阿迦?”
“到过那些国家的学者。”
“你懂得要感谢那些学者,是他们使你能与这些书交谈,得到知识。”
“当然!”
“那好,在我的故乡,也有人喜欢这类书籍。很多人阅读这类书籍。因此,需要一些人撰写。写书的人要到遥远的国度去,了解那些国家。我就属于这种人。”
“你是地理学家。不过,我还是要问你:你得到了什么?你离家外出,有福不想,到陌生的地方去受尽折磨,忍饥挨饿,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
“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同意他的说法。
“然后,你坐下来,眼睛红肿,我很好奇,你看到了什么。可是,你得到什么好处?”
“难道旅游不是一种享受?”
“不是享受,而是受折磨。”
“看来,你一定不会花费力气去爬高山,观日出?”
“不会,因为我的头脑是健全的。我为什么要离开舒舒服服抽烟和喝咖啡的沙发?为什么要去攀登,然后又跑下来?这一点用也没有。即使我不上山去坐,太阳照样升起和落山。安拉用智慧把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我的攀登不会对他的决定作出丝毫贡献。”
是的。这样的人,这样的观点!安拉,万能的安拉啊!这是他的格言,也是对他灵与肉的惰性的思考。
“也就是说,你不会仅仅为了解异国风情而去承受长途跋涉的折磨和风险的?”我问。
“是的。我不干这种事。”
“可是,我还是有利可图。我靠这个维持生活。”
“怎讲?你可以吃你看到的山,饮你看到的河?”
“不是。我如果写出这样的书,就会得到一笔钱。这笔钱就是我的收入。”
我终于说出来的,并不完全是疯话。
“啊,”主人说,“现在我明白了。你不是地理学家,而是作家。”
“我是作家,书商付钱给我,买我写的东西,把它印刷成书,再出卖给读者。我们两方面做的是一笔生意。”
穆拉德把手指放到鼻子上,想了一会儿,答道:
“现在我明白了,你就像那些从阿拉伯批发咖啡去别处卖的人?”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你把你看到的统统写进去?”
“不是全部,而是有阅读价值的部分。”
“例如,你认识的一个非常好的人。”
“是的,这种人要写进我的书。”
“或者一个相当坏的人?”
“我也写这种人,让读者了解他,厌恶他。”
他板着脸,把烟袋嘴放进头巾底下。他不喜欢这种事。这事看来让他不高兴。
“噢!”他小声说道,“就是说,好的和坏的,都通过你,在你的国家变得家喻户晓?”
“是这样。”
“你把他们的名字也写上?”
“当然,阿迦。”
“他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事?家住什么地方?”
“甚至更详细。”我强调指出。
“他们的所作所为,你和他们的谈话内容,你对他们的了解?”
“所有一切!”
“安拉,安拉!你是个大告密者!人们肯定会对你敬而远之!”
“好人用不着怕我,而且会名扬天下,因为这些书会翻译成其他文字。恶人则是罪有应得,如果他们变得臭名昭著,引起厌恶和蔑视的话。”
“你也写什格曲?”
“当然,我在那儿经历了很多。”
“或许还有基利塞利?”
“绝对的,因为基利塞利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不能忽略。”
“你都会写它的哪些方面?”
“现在还不知道,看看在这儿会有些什么所见所闻。无论如何,我会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你有豪华的烟袋和上等的咖啡。”
穆拉德沉默了一会儿。我一进门就发现他有些面熟。就好像在哪儿见过他?这位房主看起来绝对不像一个富人。他的头巾是旧的、肮脏的。长袍也一样。在他的腿上,只有患脚痛风的地方包得紧紧的。但两只脚都是赤脚,仅仅是插在一双又旧又小,磨损得很厉害的拖鞋里面。这个土耳其人又高又瘦,脸上过早地出现了皱纹。严厉的神色、凶狠的小眼、发达的下巴、宽阔的尖嘴,所有这些都使他让人看起来感觉特别的不舒服。甚至会联想到那些贪得无厌的人的模样。这种人所想到的只是捞取,不择手段的捞取。
“我希望,”这个土耳其人沉默了一会说道,“你在我这儿会满意的,只会写我的好处。”
“我对此深信不疑。你对我们这么客气,我只有感激你。”
“我本来是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迎接你的,照顾得要好得多。可是,我的内人到于斯屈布去了,我自己不能行动。脚痛风折磨我的脚。这病是在战争中染上的。”
“你当过兵?甚至当过军官?”
“那时,我比现在好,地位还高些。我是军需商!为苏丹的勇士们提供衣食。”
听了这话,我不由得想到了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的可怜士兵,想起了这些军需商们鼓鼓的钱包。
“你肯定是高官厚禄,深得君王的宠爱。”我答道。
“是的,的确如你说的那样,”阿迦自豪地说,“军需商打赢了这场战争。军需商将战争推向胜利。没有他,就没有士气,没有勇敢,只有饥饿、穷困和疾病。祖国对我非常感激。”
“要我在书中写上这些事?”
“好,写吧。请你写。可不可以对帝国和君臣们写许多正面事迹?”
“可以。”我简短地回答,因为我觉察到,他想转入正题,这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
“也有一些坏的?”
“也有,到处都有好人和坏人。”
“你在我们这儿遇到坏人了?”
“特别是在近期,而且是在这个地方。”
他摇摆着身体,一副很好奇的样子。
“本书的读者肯定会知道一切。我要是有一本这样的书就好!”
“你读不到,因为不是用你们的文字写的。”
“你现在至少要跟我说说它的内容。”
“也许过一会儿,我休息的时候。”
“我就派人指给你住的房间。不过,你至少先要讲一点。”
“我在实是太累。不过,我注意到我的好客的东道主实在太想知道那我就让我的同伴哈勒夫介绍一下我们最近所经历的大概情况。”
“他可以开始讲了,我听着。”
要哈勒夫讲一讲,他很喜欢。但是,这个阿迦用简短而又是命令的方式提醒,又使他感到不高兴。我知道,马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请允许我,”哈勒夫在开头时说,“自我介绍一下。他是怀着善意对你讲话的。我叫哈奇·哈勒夫·奥马尔·本·哈奇·阿布·阿巴斯·伊布·哈奇·达乌德·阿尔戈萨拉赫,撒马尔的主要部族哈德丁的战士。我曾祖父的祖先与先知共同作战。这位英雄的祖先与易卜拉欣,即伊斯玛仪的父亲一起品尝过西瓜。你的祖先的家谱也这么齐全吗?”
“我的祖先比这还早。”穆拉德有点狼狈地回答。
“这很好,因为评价一个人,不能根据烟袋和杯子,而是要根据已知的祖先数目。在极乐世界,有数千人在等待我。我是他们最宠爱的后代。我不认为每个人都欣赏我的讲话,可是我的朋友本尼西希望我讲一讲,所以,我要求你认真听。”
所有这一切都平心静气地讲出来,似乎当这位始祖与亚伯拉罕吃西瓜的时候,哈勒夫身临其境。他装作全神贯注地讲这番话,似乎要给东道主一份恩赐。
哈勒夫用最恰当的词语概括了最近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个法学家会比这个小个子哈勒夫讲得好。有关于可能使这位前军需商发现我们与他有关系的事情他只字未提。我暗暗为他高兴。他结束讲话时,用目光询问我,效果如何,我投去赞赏的目光。
穆拉德装作极为好奇。他把手中的烟袋扔掉,一个穆斯林这样做,是表示多种意义。然后,他紧抱双手叫喊:
“啊,安拉,安拉,把你复仇的使者派到凡间来,用烈火烧死这些罪恶滔天的坏人吧!我要相信我所听到的情况吗?我不能相信,不能,我不能相信!”
他沉默下来,拿出念珠,用干瘦的手指滚动珠子,好像是在祈祷。然后,他突然抬头,看着我并问:
“长官,你证明这个哈勒夫所讲的都是真的?”
“句句是真。”
“你在你的书中把这些都写出来?舒特,强盗,马纳赫,巴鲁德?”
“所有的。”
“这对他们是个可怕的惩罚。你认为,你还会与他们再相遇?”
“非常肯定,因为他们在追赶我。这儿,在你家里,我当然是安全的。我感谢你和那位好裁缝阿夫里特。但是明天,我们继续前进途中,坏人们还会袭击我。”
“你一定会成功的,长官,因为你只在我家住过一夜。”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的。此外,按你自己的看法,经书的开头就说得很清楚,我在你家将待多久,我们俩谁也无法改变。是的,即使安拉亲自来,也没法改变。”
“就这么办。不过我希望,我能长时间地看着你的目光在我这儿闪耀。我孤身一人在家,你使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使我脚痛得以减轻,如果你再待一会儿的话。”
“我也乐意再能享受一下你的陪伴,”我答道,“听说,你做过长时间旅行?”
“谁说的?”
“裁缝。”
我从他的脸上看出,苏耶夫说的是假话。而这个土耳其人却说:
“是的。那是在我的脚还没有毛病。我到过许多国家的城市和农村。”
“可你刚才说,你从不登山观日出!”
“我是说的现在,我的脚有毛病的时候。”他为自己辩护。
“你为什么把腿包扎起来,而让脚露在外面?”
我严厉地看着他。穆拉德显得很狼狈。难道他是故意装成有脚痛风?
“我的病在腿部,而不在脚上。”他解释说。
“这样做,你脚上的拇指不痛?”
“不痛,长官。”
“也不肿?”
“是健康的。”
“晚上发烧吗?”
“我从未发过烧。”
这个人暴露了,因为如果没有上述现象,也就不可能有脚痛风!他对脚痛风症状一无所知。现在我明白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了。此外,为了提一提所谓书房,我向他打听:
“你有许多书,它们会减轻你的痛苦和寂寞的。”
“书?”他吃惊地问。
“是的。你是一位博学者,拥有很多令人羡慕的文字资料。”
“谁说的?”
“也是裁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