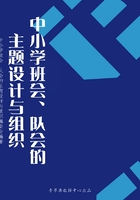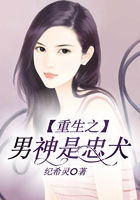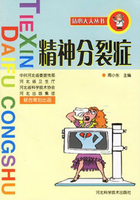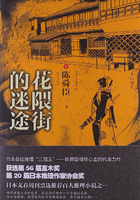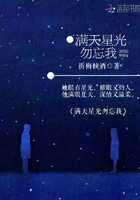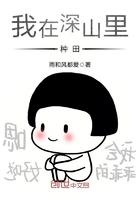“天人合一”强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把整体自然界看作一个统一的生命系统,主张尊重自然界一切生命的价值,爱护一切动物、植物和自然产物。[参照田广清著《和谐论——儒家文明与当代社会》,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6月版。]儒家把天、地、人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把天道与人道紧密地联系起来思考,体现了生态中心和整体论的宇宙哲学观。古代中国人对自然和生命的节律十分敏感并有各种禁令,主张凡事应当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亦记载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礼记》“月令”篇记载:“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履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孟夏之月:是月也,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而直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趋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到“季秋之月”,则“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内,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并且,“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总之,当春萌夏长之际,不仅特别不许破坏鸟兽之巢穴,不许杀取或伤害鸟卵,虫胎、雏鸟、幼兽、也一般地禁止人们各种有害于自然生长的行为。所禁的行为对象范围不仅包括动物、植物、也涉及到山川土石。而其中的“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则可视为基本的原则。这些禁令一方面为了人的利益,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另一方面也有让各种生命自然成活和生长、“无伤”、“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意义,即不仅人的生命、所有其他的生命也都有其价值和意义。
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周代,那时表达为“天、地、人”三才的思想。《周易·乾卦》中讲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相传为孔子所作的《周易大传》在阐发这一思想时认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立天之道,曰阴阳;立地之道,曰柔刚;立人之道,曰仁义。”这就是“天、地、人”三才之道。我国古代思想家在天地人的关系中强调必须按自然规律办事,顺应自然,谋求天地人的和谐,这就是“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周知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人要在遵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积极地顺应自然。
孟子以“诚”(意为“真实无妄”,属道德范畴)这一概念作为天人合一理论的指向,曰“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责上》)《中庸》把“诚”视为天的本性,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本:“诚有物之始也,不诚无物”要求以“诚”这一道德修养达到“天人合一”。汉代董仲舒认为“天地人”三者处于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作用,但却是“合而为一”。他说“事物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之神》)
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发展到宋代,更趋于成熟,宋儒在继承先前儒家思想的同时,吸收了墨家的“兼爱”,庄子“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以及惠施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天人合一学说,并由思想家张载首先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
程朱学派有关“天人合一”的哲学阐发为中国古代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生态伦理学价值,将“天理”作为最高哲学范畴,天理即生,“生”是宇宙的本体,在生生不息的天道之下,通过阴阳二气化生,产生天地万物,人是天地万物之一,即“人与天地一物也”,人明白这一道理才成为仁者。[葛荣晋《“天地万物一体”说与现代生态伦理学》,载《孔子研究》1995年第3期。]
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别于西方人主宰自然和统治自然和哲学思想,更符合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精神和原则。支持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故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先秦其他流派,尤其是道家的思想学说之中。《老子》第25章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试图说明天地人之间法则的相通,而这种法则并非以人为依归,而是以天地、自然为依归。《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则表明了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可以说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东方人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体现。[参照余谋昌《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99年3月版,第6-9页。]
2、“天道生生仁爱万物”[本段参照余谋昌《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99年3月版,第10-11页。]
“天道生生”是与“天人合一”并列的深湛的思想,“天道”指自然界的变化过程和规律。“生生”指产生、出生,一切事物生生不已,即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是具有一定规律的,生命的产生和生生不息,即是自然之“道”,又是“自然之德”。孔子在《周易大传》中注明:“生生谓之易”,意为世界万物生而又生,生生不息,这就是“易”。儒家哲学是把“道”和“德”联系起来的,而且认为“生”(包括人和其他生命)与“德”(专指人类行为)两者是统一的,万物生生不息是人类最崇高的德行,即“至德”或“大德”。
儒家生态思想将道德对象和道德共同体予以扩大,主张对生命和自然界给予道德关心,形成生态道德概念。儒学核心“仁学”是关于爱人的理论,但儒家学者在说“仁”时常把道德范畴从人的领域扩展到生命的自然界,这就是“仁民”而“爱物”。这两者相结合,便上升为道德要求,可用生态学术语解释为:人类行为既要有利于人类生存,又要有益于生态平衡,这才是有道德的。人源于天命之性,应对人及一切生物施以“悯恤之心”和顾惜之情,方为明德。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孟子理想的儒家生态社会——“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中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他说的三项有利于农业生产的举措:“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目的是为了“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由于孟子所生活的战国中期,“民不聊生”问题相当突出,孟子提出了这种最能体现“仁民而爱物”思想的生态伦理责任观。孟子这一理想社会不仅讲了人人衣食有着,讲文明礼貌,而且还强调了农业生态保护得好,能够可持续地发展(这里是儒家思想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平衡图景。所以这是名副其实的儒家生态社会,它充分贯穿了“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理念。
宋代以后的儒家学者,对“仁”的论述有重大发展,把“仁”直接解释为“生”,即一种生命精神的生长之道。朱熹说“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已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言,百行之本,莫不在是”。(《仁说》)。这就是说,天地之新要使万物生长化育,它赋予每一件事物以生的本质,从而生生不息。这个统一的生命就谓之为仁。仁即天地之心、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及至清代,思想家戴震进一步提出“生生之德”就是仁。仁不仅要人类遂其生,而是推之以天下万物,使天下万物共遂其生。[参焦国成《传统仁学的生态伦理意义》,载《森林与人类学》1995年第1期。]
3、行“和合、中庸之道”[参见余谋昌《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99年3月版,第20-22页。]
儒家虽然承认人与人、人与动物的差别,但也强调要“各正性命”,“各能自尽”,“无相夺伦”。在儒家那里,没有阶级斗争和种族战争的强烈观念,没有一心要征服、奴役他族、他国或实行阶级专政的执着心态。孔子主张中庸之道,讲求设身处地,将对象与自己置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共同和平地生存、交流与合作。这种和合、中庸的思想观念贯通于中国人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感等领域。
“和合”表示和谐,“和”指不同事物和因素的结合与调和,是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孔子把和的概念主要应用于“人际关系”这一社会生态环境,主张“为政应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直接强调“人和”的重要性;荀子把“和”与“神”联系起来,说“万物各得其和以声,各得其养以成,不见事而见其功,夫谓之神”,意为万物得着各自需要的和谐之气而生存,得各自需要的滋养而成长,虽然看不见它们如何工作,却看见了它们的成绩,这就是“神”,由此可见和的重要。
董仲舒则更进一步,把“和合”提到天地生成的本能,万物生成发展的机制,首次把“和”与“德”联系起来,又把“和”与“中”联系起来。他说“和者天地所生也”,因而“德莫大于和”;又说“天地之道,虽有不和者,为归之为和,而所为有功,虽有不中,必止于中,而所不为矣。”《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和”与“中”是有相互联系的客观规律,“中庸”范畴的生态伦理价值也是儒家所珍视的,它既是人类的德行,又是实践德行的方法。“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易·夫卦》)。中行无咎,中庸最早由孔子提出,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意为中庸是最高的德行,要求人的行为把握一定的度,即允执其中,以保持事物的平衡。
《中庸》系统阐述了中庸的思想概念:第一,中庸是天下万物的根本的性质,所谓“天地之道兼举”,“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庸,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点明世界本性是中庸,它是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第二,中庸是重要的方法,“中庸”为常道,“中和”可常行。第三,中庸是“至德”,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反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
正如儒家学者所总结“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且恕乎人,顺乎天,天人之道兼举,此谓执其中”,按世界万物的性质和规律,行“和合、中庸”之道即为适合人的社会生态行为。这里传达了一种限度和节欲的观念,将中和、宽容、不走极端、不为己甚作为对人和事物的正确态度。
4、“君子不器重义轻利”
儒家一直并非以经济的不断发展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不以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己任,而是更注重优美人格、崇高德性的培养,这种思想一方面体现在不断在道德上超越,力求造就高尚的君子、圣贤;另一方面也使社会风俗淳美,上下相安。儒家生态思想的价值取向客观形成了对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制约,因为主张“向内用力”而不是“向外用力”,所以有效地保护了生态环境。
儒家固然也主张富民养民,丰衣足食,但在这方面是有一个限度的,即在人们的生活资料满足到一定程度后必转向道德修身和教化,而不以不断鼓励民众攫取财富为能事。它促使社会上最优秀、最聪明的那一部分人的视线和精力朝向人文和道德修养,而不是朝向科技与经营,它抑制了最有可能带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商业活动,逐渐培养起一种以读书为荣、任官为贵的社会风尚,而不与读书和官职联系的财富则遭到怀疑和限制。孔子说:“君子不器”、“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说“仁义而己,何必曰利?”,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儒家思想家那里,一直有一种重义轻利的倾向,在他们影响的国家政策上则表现为重本抑末、重农轻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