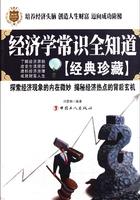密郡王府管家是这样向宁亲王爷禀报的,“回王爷,我们王爷与王妃娘娘前日参加谨郡王爷的婚礼,在回府的路上受了风寒,刚回到王府就病倒了,如今王爷和王妃病体难支,唯恐过了病气给旁人,所以不敢前来参加小公子的满月宴,还乞王爷和王妃娘娘见谅。”
密郡王府管家这番话刚一说完,便有人小声嘀咕起来,“这天儿又不冷,晚风不过只是微凉,怎么密郡王爷和王妃偏就受了风寒呢?”因为今日来的宾客人数仍然不少,所以没有人听出来这话是何人所说,不过这人倒是说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思。最近这六七日天气极好,风和日丽冷暖适宜的,有些身体好的人甚至还都穿着夏装,怎么密郡王夫妻双双受了风寒呢。
什么是不作不死,大抵说的就是密郡王夫妻了。密郡王妃回到王府之后,只是泡了个花瓣浴,手臂上便起了些针尖大小的红疹子,密郡王妃起初也没有在意,只是命丫鬟拿来红玉紫云膏薄薄抹了一层。红疹子很快就消失的差不多了。临睡之前,密郡王妃进了一盏宫燕羹,然后便上床睡觉了。不想到了后半夜她的手臂突然奇痒难忍,密郡王妃迷迷糊糊的抓了几下,可是越抓越痒,密郡王妃忙命丫鬟掌灯,她低头一看,只见手臂上便以极其可怕速度长出了一大片又红又硬如蛇皮一般的东西。密郡王妃只是看了一眼便被吓昏了过去。
丫鬟见王妃吓昏了,忙去找王爷。不想歇在柳侧妃房中的密郡王爷也出事了,王爷上身也长出与王妃手臂上一般无二的蛇皮状的硬皮。柳侧妃吓的花容惨淡,躲在离密郡王爷最远的角落里瑟瑟发抖,而王爷却连生气都顾不上,只疯了一般的拼命抓痒,不大一会儿就将自己抓的浑身是血,却还是解不了那种深入骨头的奇痒,密郡王爷实在熬不住,竟然一头撞到床架上,生生把自己撞的昏死过去。
密郡王府大乱,赶紧请太医,太医过府诊病,可是根本诊不出病因所在,只能开些疏风凉血解毒止痒的汤药膏药。因为药不对症,所以效果极其有限,密郡王夫妻已经痒了一天一夜,两人自然不能来宁亲王府吃源哥儿的满月酒,只能假称受了风寒命管家送上满月礼。
杜衡听说密郡王夫妻二人都称病不来,心中有些惊讶,她原本以来只有密郡王妃不能前来的,她对密郡王妃用的痒疹粉又不会传染扩散的,不可能传染给密郡王的。密郡王爷但凡还能在外面走动,就不会不来宁亲王府道贺的。
到了晚间送走客人之后,杜衡回到交泰园,她先去了药房,见药架上痒疹粉的黑瓷小瓶子还在,可是拿起来用手一掂,份量却轻了许多。杜衡莫约猜到了什么,便拿着小瓶子回了卧房。
“阿泽,你动我的药了?”杜衡将黑瓷小瓶放到萧泽面前的桌上,歪着头问道。
萧泽大大方方的点头应道:“嗯,我用了一些。前天晚上去了趟密郡王府。”
“你用了足足半瓶,不会全都用在密郡王身上了吧?”杜衡低呼问道。
萧泽理所当然的点头道:“对啊,密郡王太胖了,我怕用少了效果不够好。”
杜衡一拍额头急道:“你……你也真是的,就挑指甲盖这么一抿子,就够密郡王痒上十天半个月的了,你居然用了半瓶,若是不用解药,密郡王非得被活活痒死不行。对了,没沾到你身上吧?”
萧泽摇头笑道:“没呢,我戴了鲛丝手套,这痒疹粉厉害的紧,我怎么敢粘到手上。阿衡,你真聪明,一下子就想到是我干的。”
杜衡白了萧泽一眼,轻嗔道:“能想不到么,以后别不打招呼就乱用药粉,你又不知道用量。”
萧泽忙凑上前陪笑说道:“阿衡,那会儿你不是正睡觉么,你又不让我进房,我怎么和你打招呼啊。阿衡,你看我是不是……”
“不行,不与你说了,我累了……”杜衡先是斩钉截铁的叫了一句,然后又慌乱的不知道说些什么,接着就飞也似的逃进内室。这让萧泽的笑容僵在脸上,一时说不出心中是个什么滋味。
就在萧泽垂头丧气的走到床边坐下之时,内室之中突然传出一声细细的低语:“我……我还没准备好……你别逼我……”
萧泽腾的弹跳起来,冲到内室门前急急叫道:“阿衡,我不逼你,你慢慢准备,多长时间都行,我会一直等着……”
密郡王夫妻同时得了怪病,太医们束手无策,密郡王的母亲,宫中的陈妃实在熬不住了,便求到了当今的面前,求皇上派御医给密郡王夫妻诊治。当今派了御医到密郡王府,诊脉过后却也是束手无策。密郡王夫妻的脉相极为正常,并没有丝毫不妥之处,至于身上的如蛇皮般的结痂硬皮,其实只是皮肤过敏后过度抓挠导致的。
御医不查不出密郡王夫妻碰触了什么东西导致皮肤过敏,所以也没法子对症下药,只能让密郡王府的下人用苦参蛇床子半枝莲煎水让密郡王夫妻浸浴。原本这个方子清热止痒效果是再好不过的,就算不能立刻根治,也会大大减轻患处的奇痒之感。可是这个法子对密郡王夫妻却没有什么效果,这两人依旧痒的死去活来。
御医都没办法了,最后不得不将密郡王夫妻绑起来,不让他们抓痒,因为御医发觉若是不用力抓挠,患处的症状明显减轻不少。于是密郡王夫妻就开始了一段生不如死的煎熬日子。密郡王妃只是手臂奇痒,症状比她的丈夫轻的多,只受了十日煎熬,手臂上便不再有那奇痒之感,硬硬的厚皮也逐渐脱落,露出了皮肤的本来面目。
御医一看这法子倒是歪打正着挺管用的,便更加将密郡王爷严严实实的绑起来了,就连他想在什么东西上蹭一蹭都不能够。密郡王因为上身奇痒难耐,他又被绑的严实,便只剩下干嚎这一个发泄途径了,喊了不过半日,就将嗓子彻底喊倒了,嘶哑如粗砂磨擦之声一般,真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就连密郡王的亲娘陈妃都受不了那份魔音穿耳,只出宫看了儿子一回便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