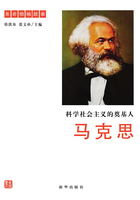如果说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的会晤,拉开了他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的序幕的话,那么,1945年8月~1946年8月,毛泽东为争取中国的国内和平,同美国等方面进行的交涉谈判,则是其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的尾声。在这一阶段,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逐步调整其外交政策,其中一项举措就是派极端反共的共和党人赫尔利,接替所谓“亲共”的史迪威为其驻华的全权代表,开始全面推行一条亲蒋反共的政策。毛泽东预见到抗战胜利后中国所面临的光明和黑暗这两个前途,他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正告美国政府,“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了揭露美蒋制造的假和谈阴谋,也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内战,并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毛泽东先后同美国政府的特使赫尔利、马歇尔等进行了认真的谈判,期间,他还亲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但是,蒋介石集团无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正告,无视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而是迷信自己的武力,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叫嚣在三到六个月内全部消灭共产党。和平的大门被关闭了,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的头上,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发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接着他开始踏上艰苦转战的征途。
(三)
1936年~1946年的外交活动,毛泽东尽管是初涉外交舞台,但仍显露出影响他整个外交生涯的一些特点。
第一、毛泽东是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双重身份登上世界外交舞台的,尽管各种问题错综复杂,但他不为具体的外交事务所陷,而总是能从宏观上和战略上考察问题,一开始就显露出非凡的战略眼光。如1936年7月15日他同第一位到苏区的外国人斯诺的第一次谈话中就指出:中国人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了中国的和平,而且威胁了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且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特别是美英法苏等与太平洋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敌人。”根据这样一个基本点,他鲜明地提出,除了日本和帮助日本的国家以外,所有的国家,包括苏联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乃至英美等在太平洋地区有重要利益的国家,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他没有计较这些国家历史上与中国的恩怨如何,也没有计较这些国家在现实中的矛盾和差别,而是从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这一个共同点上,提出建立世界联盟的战略思想,反映出毛泽东那战略家的深邃眼光。
第二、毛泽东把“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的思想,作为他外交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说,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虽然当时中国人民正在为从日本殖民地化的黑暗统治中摆脱出来而苦苦挣扎,但他却深信:“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
正因为树立了这样一种思想,所以他特别关心国际形势的变换,总是习惯于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他对国际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影响他对国内形势的判断;反过来,毛泽东对国内问题的综合归纳,也是他对国际问题作出判断的重要条件。虽然这一时期他对一些国际问题的分析和判断,并不都是十分准确,但已经在外交领域展示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家的高超智慧和博大胸怀。
第三、毛泽东是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援,把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才开始接触外交问题的。和1840年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包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相比,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以全中国的人民为后盾,以维护中华民族最大多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为目的,把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始终作为其外交活动的第一要义。虽然他十分注意策略,非常讲求团结多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但他和过去那些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以夷制夷”不同,他运用灵活机动的外交策略的先决条件,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他强调“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虽然他一再为争取欧美国家的同情和支持而努力,但他始终把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和觉悟视做夺取抗战胜利的最终力量。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地告诫全党“我们必须看到国际和平阵线各国有其各不相同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助我,政府则取某种程度的中立态度,其资产阶级则利用战争做生意,还在大量输送军火和军火原料给日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援华问题上已经具体的表现出来;然而国际形势目前还不容许它作超过现时程度的援助。因此,我们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十五个月经验证明: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他在向斯诺表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投资时,也曾郑重声明:我们欢迎用于建设目的的外债,但是,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由于坚持了以我为主的原则,这就和那种“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倒向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屈辱外交彻底划清了界限。
第四、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中还系统阐述了许多宝贵的思想,除了前面讲到的内容外,比较集中的是对外开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应该对世界有伟大的贡献,可现实的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他坚信: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世界文化水准,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对世界将有伟大的贡献。为了这个目的,他提出要全面地向外国学习和对外开放的思想。在政治上,他有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张;在军事上,他希望能得到外援,更新和补充武器装备,并同反法西斯国家合作对敌;在文化上,他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尤为难能的是,毛泽东当时就详细地构想了在经济上对外合作或对外开放的问题。这主要是:(一)开展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他说,中国人民一旦真正获得国家的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因为“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因此,他主张“对外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二)“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毛泽东深知,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个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三)战后中国最适宜与之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是美国。毛泽东虽然一直认定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中国最可靠的政治盟国,但在选择经济合作国家这个问题上,他却能不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是依据具体的国际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互补等因素,认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当年思想的开放程度。尽管由于受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国共之间阶级矛盾的制约,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和主张当时基本上未能实现。但在那样艰苦激烈的战争环境中,他还能想到这些问题,而且勾画得那么具体,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给我们后人许多的启示。
(四)
研究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活动,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毛泽东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有的论者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还谈不上什么独立的外交,他们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苏联外交政策的翻版。持这种观点的人,特别对毛泽东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为斯大林和苏联的辩护,微词颇多。对这些问题,似应该具体地分析。
苏联是从其本身的利益出发考虑中日战争问题的。一方面,随着欧洲的局势的日趋紧张,希特勒从其反共本性出发,同时也为了同英、法等国讨价还价,不时表现出或者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要发动对苏战争的姿态与行动;英国等西欧国家也希望能祸水东引,试图通过某些让步以换取德国向东发动对苏战争,防止其向西行动危害自身利益。而中日战争的发展对于苏联的国家安全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假如中国被征服,日本拥有中国的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这样,苏联就面临着东西线双向作战的威胁。所以,苏联希望借重中国以牵制日本。因此,援助中国对日抗战便成为苏联远东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另一方面,苏联虽然与中国共产党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但它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微弱力量对于抗击日本的强大侵略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它把牵制日本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这种认识和要求与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政策是一致的,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虽然在出发点上不同,但恰好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这是造成这个时期毛泽东与苏联在外交政策上,既有相同又有分歧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