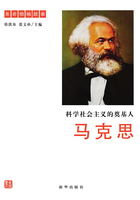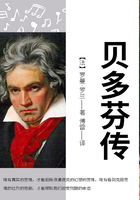自孔子始,中国社会的统治者,都抱着“作人之圣”、“作人之师”的心态,集权威、智慧、道德于一身。要求自己既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领导者,又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作为精通中国旧学的毛泽东显然受到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全国人民“导师”的角色。
这种传统的“导师”角色,不仅是出于统治者自身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民族的“精神粘合剂”。贝特兰·德朱维内尔在《论权力》一书中曾记述了这样一种观点: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单靠权力是不够的,必须有一种共同的感情,有一套得到普遍承认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即全社会需要的一种“精神粘合剂”,即一向被视为传统文化中心和标志的孔子首创的那套儒家伦理。它以仁礼互补的原则来处理人伦关系。其基本的内容即是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它要求以个人的道德实践作为出发点,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实用政治化了的这种道德学说成为中国宗法式的,小农经济社会的“精神粘合剂”。
当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明以坚船利炮的方式冲开中国的大门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被破坏了,传统的道德信仰和生活方式逐渐丧失了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在痛苦之中不得不脱离自己那套熟悉了的生活方式,进入一个东西冲突、新旧交融的时代的夹缝,新的东西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来,而旧的“精神粘合剂”又丧失了固有的作用。人们茫然回顾,无所适从。
这样的时代,呼唤着新社会的创造者的诞生,呼唤着一套新的指导人们行为准则的“精神粘合剂”的诞生。
辛亥革命没有做到这一点,孙中山毕生的努力也没有做到,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更是不可能。面对现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承担起重建民族精神、统一人们的信仰的重任。他们主张,必须把在红军中形成的同心同德之情灌输到全体人民心中,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必须确立一种新的伦理价值观。
那么,这种新的“精神粘合剂”是什么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灌输给人民。这种新伦理价值观可以在“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全面的认识,毛泽东以他的“老三篇”重新雕塑着中国人的心灵,建立一种全新的精神风貌。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中写道:它以“童子军直率老实的德行教训的音调”,“把这些教训灌输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里去”。
毛泽东一直在主动、自觉地承担着育人、改造中国人心灵的重任,尤其对于青年人。在毛泽东看来,老一辈革命家,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持有共同的信仰,他们已经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形成了新的理想、新的信仰,对他们,毛泽东是放心的,但对于青年一代呢?
尽管毛泽东说过,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但他对青年一代总不放心。这在他同斯诺的谈话中有明显的流露。斯诺认为,1937年听毛泽东讲演的青年,后来在实践中学会了革命,但是,今天的中国青年从来没有打过仗,并且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帝国主义者或者当权的资本主义。他们对社会没有直接的了解。父母讲给他们听,但是听讲历史和看书同生活于其中是两回事。因此,他问毛泽东:
“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是人类是按照自己的环境创造历史的。你已经根本地改变了中国的环境了。许多人还想知道,在比较舒适的条件下养育出来的青年一代将会怎样。你的看法怎么样?”
毛泽东回答道:
“我无法晓得。谁也不能肯定地晓得。”
在毛泽东看来,这~代青年人有两种可能性:可能革命朝着共产主义继续发展,另一种可能性是青年会取消革命,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使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回到大陆来,并站在仍然存在于国内的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自然,我并不希望反革命,但是将来的事情会由后代人解决,并且按照我们没法预见的条件去解决。从长远观点看,后代人应该比我们更加有知识,正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主义时代的更有知识一样。他们的见识会占优势,而不是我们的见识占优势。今天的青年和其后的青年,会按照他们自己的社会准则评价革命工作。
毛泽东越说,声音越低沉,后来便干脆伴着萦绕的烟雾沉思起来。
他在想什么?谁也无法肯定的揣摩。也许他在想必须把青年一代改造好,必须保证自己的教导对青年有持久的影响力,以保持江山万代红。也许他觉得他责任重大,应该承担起教导青年人的责任。他是一位导师,像古代的圣贤孔子一样。这种自觉的导师意识,使毛泽东为重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不仅教导着革命队伍里的人,还教导着中国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他作为一个精神的领导还改造着从旧社会过来的包括敌对阵营的所有的人们,教导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整套价值观、道德观,摒弃旧道德、旧观念,重新塑造着中国人的心灵。
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作人之师”的意识的驱使,他精心导演了一幕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悲剧,一场中华民族的“大劫难”。在一定程度上,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让青年一代置身于政治舞台,就像他那一代人在五十年前突然作为改造中国的新尝试者、推动者站到历史的前列一样。
一个从不满足于变化速度的进取者
毛泽东对动的环境有一种特殊的爱好,自青年时代以来,他一直认为“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喜欢动荡的世界,他不相信王侯将相有种的世袭统治的神话,在他很年少的时候,便在长沙的橘子洲头向苍茫大地宣告了欲主沉浮的宏大理想。在运动和斗争中不断前进几乎成了他身心的需要。要使他的人民处于不断“运转”过程中,以保持高昂的斗志和激情,同时在“运转”过程中不断地改造着人。对此,斯诺曾颇有涵义地写道:
“毛是一位进取者,是原动力,是创始者,最善于采取令人惊讶的局面、紧张局面和缓和局面交替出现的战略。他不相信漫长的稳定时期,而且从来不满足于变化的速度……”
确实,作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领导,他不欣赏,甚至讨厌中国传统心理中的中庸、和谐、不争、守旧、世故等心理境界,他力主在动中改造人,在动中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动方式灌输给别人。他的心中始终激荡着骚动不安的情绪,他竭力想打破现实的平衡,相信斗争哲学,相信一切的发展来自事物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相信理想的新秩序只有在动荡和不平衡中建立,在打破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二者之间他更喜欢、也更善于前者。他自己就是在非常的历史时期造就的,他喜欢在惊涛骇浪中搏击,在这种颇具浪漫色彩的自我肯定中能获得快意。“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句豪言壮语可以说是毛泽东性格的极端流露。的确,他需要强劲的对立面激发自己的斗志,在斗争中改天换地,大展宏图。斯诺是明了毛泽东这一性格的。
因此,他认为人的一生应该是斗争的一生,或者说造反。童年时代他造父亲的反,少年时代他造校规的反,青年时代他造省长的反,成年时代又造整个旧世界的反。
确实,正如斯诺意识到的,毛泽东这种从不满足变化速度的进取精神,造就了毛泽东与众不同的一代领袖形象。
一个深邃和果敢的人
人有复杂的内心世界,人不会将它全然表露于外。有些情绪,如痛苦、孤独、寂寞,会永远留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或无处流露,或不愿流露而永远留在自己的心中,构成外人难以窥视的内心世界。伟人也不例外。毛泽东作为一个圣贤,作为一个普通的、非神的人,他有他的“内心世界”,有同常人一样的情绪体验,史沫特莱曾这样说过:
“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有一扇门,一直没有向其他人打开。”
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他就感到毛是一个“复杂的人”,尽管在建国以后的一次会谈中,毛泽东曾告诉斯诺,“他不是一个复杂的人,真的很简单”,但种种迹象表明,斯诺没有改变他的“第一印象”。
毛泽东将知识分子的深邃和农民的机敏结合起来;将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起来。
斯诺写道,毛泽东“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的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但是,这种“必要时候”别人往往难以捉摸,唯有他自己内心清楚。也正是因为这种极强的自尊心,使他不愿多向别人袒露自己的心迹,禁锢了自己的心灵,严重影响了他的自我开放。
不仅斯诺有此感受,史沫特莱在初次见到毛泽东后,也有类似的感受。她认为毛泽东沉默寡言、态度冷淡,有点难以接近。她这样写道:
“我最初所强烈感到的他那种令人捉摸不透的气质原来是不喜欢与人交流思想。朱德受人爱戴,而毛泽东受人尊敬。最了解他的少数几个人热爱他,但是他性格内向,一般人敬而远之。”
在建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毛泽东不太熟悉、不太懂行的新课题摆在面前,随着自己年龄的不断增长,毛泽东的内心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了。
在1965年、1970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曾多次莫明其妙地对斯诺说他“快要去见上帝了”,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说,他的内心是怎样想的,人们不得而知,根据斯诺的判断,根据后来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这样说目的也许是“有意迷惑他的敌人——鼓励他们进一步暴露自己,而另一方面则准备着一种进攻战役。”诚然,这也是一种臆测而已。
在面临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面前,作为一直是一个思想家、军事家的毛泽东,他不太了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因此,在新的环境下他已有的权威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这种在党的历史上确立起来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某种因素冲击而动摇的时候,作为自尊心极强、一向是领导的毛泽东不可能没有一种失落感,加上他内向的性格,使毛泽东不能不为之困惑和焦虑。
毛泽东作为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伟人,他的确把毕生的精力付之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他一生的艰苦卓绝、内向的性格,增加了他内心的苦闷和孤独感。他的心态也是矛盾的,他既相信同他同甘共苦的革命战友、相信他自己深爱着的人民,但一旦有风吹草动,他又不放心了,包括曾同他一起战斗过肝胆相照的彭德怀、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疑他们会不会变修,变成党内走资派,他也怀疑他的人民会不会站在同他敌对的立场;他为人平易近人,努力将自己成为普通的中国人中的一员,他一方面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从少年到老年,他都在不断想象的世界中遨游着,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又不得不脚踏实地,在强制的、纯粹理性意识支配下生活,极强的民族责任感和领袖意识更强化了他的这一矛盾心态。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事业付出毕生精力的一生,也是在极端的矛盾心态下艰难地度过的孤独的一生,他虽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他拥有着脚下坚实的大地和广大民众,但他的心灵深处,作为一个人,始终是孤独的。
毛泽东未曾写过自传,至于何种缘故,后人也难以评说。他也很少向别人流露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连同他的夫人贺子珍,当毛泽东向斯诺叙述他的经历时,在旁的贺子珍听的出神而感动,因为她未曾听毛泽东这样讲过。然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斯诺的坦诚面前,毛泽东向斯诺流露了他的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斯诺是最了解毛泽东的人们中的一个。
斯诺的毕生专注于对这个震惊20世纪的世界的东方巨人的了解和研究,他在同毛泽东交往、相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以局外人的身份比较客观地用他的笔记录毛泽东这样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东方圣人。在斯诺的笔下,毛泽东是一个脚立大地的普通人,一个深爱着自己的人民的领袖,一个最了解自己国家的元首,一个中国人民公认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