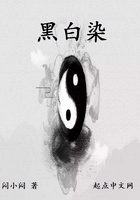出发那日清晨,我在向岛的旧书店里买了本啄木[1]的诗集《悲伤的玩具》,并在扉页题道:“远渡重洋,启程美国之清晨。购于墨田畔”。
在集训营,照例吃了有胜敌寓意的炸猪排饭,为征途撒上冷酒后,我们便身着华服,怀着灼烫的心情,踏上了旅程。
之后便是按照众所周知的路线赶上大洋丸。狂热的欢送中,连我这个无名小辈也被姑娘们索要签名,女学生送来巧克力和花束等。旗帜、人,还有体臭,与汗水杂糅着,忽然,我觉察出自己正拼命忍着疯狂想笑的冲动。
如此盛大的欢送真是让人感动不已。尤其是,京浜间多建有工厂,工厂的窗户、栅栏、甚至屋顶都挤满了挥着太阳旗的职工和女工,从车窗外看到他们个挤个挨在一起的纯真面容,让人禁不住想要落泪。
疯狂想笑的冲动在登上船被送行的众人挤得无法动弹时再次疯狂袭来,我钻进刚刚被告知的船舱笑了个够才再次来到甲板。
之前中学和现在大学的老师、朋友、后辈们都来了。随着一声锣响,借用母亲的表达,那就是,哥哥像哧溜溜的猴子分开人群登上船,将西服送到我手里。归国之后才知道故乡镰仓一起玩大的小伙伴们好像也来送行了。在码头混杂的人群中,看着被挤得东倒西歪还挥着手绢的老母亲的身影,我突然眼角一热。看到她周围跟着我家两位热心房客,我才放下心来,开始抛哥哥给我买的丝带,可是总也抛不到母亲那里。
丝带一会儿飞到了一群女学生那里,一会儿落到了学校朋友的手中,却总也到不了母亲那里。终于有一个到了母亲近旁,却被一位像是工薪族的人取走了,房客H先生跟那人说情,让他送给了母亲。母亲有些歇斯底里,她握着丝带抽抽搭搭地哭。看着她哭,不知为何,我反倒松了口气。环顾四周,我才发现,大多数选手身边都围着前来送行的年轻女孩,华丽非常。
我们KO队也不例外,甚至连魁梧的五号位松山,也正和熟识的黑猫咖啡馆的女招待交换丝带。帅气的六号位东海就更不用说了,他的丝带全被漂亮的女孩子握在手里。亲朋好友的关爱和祝福虽让我感到幸福。可我还是觉得丝带给了母亲着实可惜,要是有那么一两个女孩子夹杂其中,该多好啊。
寂寞的情绪一直持续到起航。当送行人群的影子和码头都逐渐模糊起来,港口和灯塔也渐行远去,欢送船也离开时,我一个人站在散落着花束和丝带的甲板上,盯着岛屿、海鸥、逶迤的波浪,心底涌出一股旅愁。
船上依然缭绕着出发时的华丽氛围,当然我们KO也不例外。无论是清晨的丹麦体操,还是绕B甲板的晨跑,又或是上下午的拉背以及引体向上,与隅田川相较,都格外地轻松起来,想必众人都怀着几分对大洋彼岸憧憬的心情吧。东海和候补有泽讲着和爱人的琐事,而森和松山则是黄色话题不断,甚是热闹。
集训以来,我便一直是一个人,混杂在众多队伍中,便愈觉寂寞。起航两三天来,除了训练时间,我只在甲板上散散步,在船舱里读读啄木,当客舱被同屋的松山和泽村占领时,便到吸烟室里给母亲写写信。
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在离开祖国的第三天,极度寂寞的我,在吸烟室的一隅,曾经一度打算写一封离谱的信。当然,信最终没有写成。那是前年夏天,在镰仓的海边,我认识了一位文化学院的女孩,我想给她写封情书。而回信多半在我到了那边就能收到了。可想着溜圆瞳孔的她或许已经有恋人了,我突然羞愧起来,便放弃了。
注释:
[1]啄木,即石川啄木1886年-1912年,歌人,诗人,原名石川一,著有歌集《一握砂》《悲伤的玩具》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