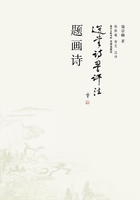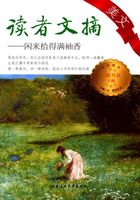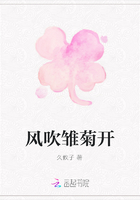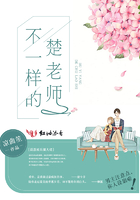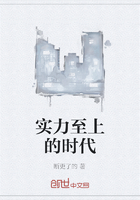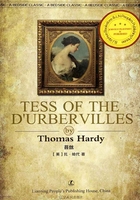也曾,深深地爱过,也曾立下誓言:此生,定要牵彼之手,从花前到月下。曾经,那么单纯地以为『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是一件并不太难的事。可是,终会明了,爱,从由不得我们左右,那些要走的路,那些爱过的人,都在命运的一个眨眼间,已经注定。
情到浓时起致辞
因为心中热烈的爱慕,
问伊是否愿作我底亲密的伴侣?
伊说:“若非死别,决不生离。”
——于道泉
情到浓时起致辞,
可能长作玉交枝。
除非死后当分散,
不遣生前有别离。
——曾缄
生离和死别,是世间最让人感慨的话题。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又有谁能笑着面对……深夜读仓央嘉措的诗,总有一句,催人泪落。
他的每一首诗都充满了那宿命的爱情,让人忍不住羡慕,但也忍不住伤心,不只是为他的爱情,更是为了芸芸众生中也曾有人有幸收获这最为真挚的感情。
宿命,让我们遇见爱情。
朝气蓬勃的花样年华,谁不曾有过最初的心动。而那个时候,我们也曾有过最美的誓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山无陵,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那些誓言,流淌了千年,流淌到了三百年前的西藏。
当爱情流经仓央嘉措,我们又一次见证了,爱的奇迹。
他那一声呐喊:“若非死别,决不生离。”如一记印章,在我们心里重重地印下“爱情”两个字。
好美。
开篇,我分别摘录了于道泉和曾缄的译本。因为他们译得各有各的妙处,无论是哪一首我都爱不释手。
在各种仓央嘉措的诗歌版本里,最触动人心的当属曾缄的译本。暂且不论他的译本究竟是由藏文直接译过来的,还是根据已有的翻译版本加以润色,最终形成七言绝句的,他译本中的诗的意境,以及他在古诗词上的造诣,包括他对人类情感的理解,都让人动容。
在这一首诗中,我最喜欢的是他的首句和尾句。
“情到浓时起致辞”,当一个人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会忧虑重重,患得患失。害怕自己对她不够好,害怕自己不够优秀,无法留住她的心,害怕有朝一日,她会不在自己的身边。
不自信也罢,庸人自扰也罢,只因爱太深,才会太在乎一个人的感觉,才会无法承受那种失去的痛楚,才会一遍遍不确定地问:你可否陪我到天荒地老,做我身边最最亲密的人。
一个被认为不应该拥有爱情的人,却恰恰拥有了一份最强烈的爱情。
这还不够,他还要和他的爱人一起看这世间浩大、人情冷暖。
爱在心头口难开,仓央嘉措巧妙地把这个答案交给了对方:“若非死别,决不生离!”
这一句,于道泉先生在力求原汁原味的原则上,翻译得明朗利落,让这一份爱的誓言变得无比有力,准确无误地击中了人的情感区,瞬间带给人爱的希望。
而这种干脆利落,也同样像极了仓央嘉措本人对于爱情、对于人生的态度。
誓言,本身就应该铿锵有力,带着那么一点惨烈的味道。
表面上,这似乎只代表了对方的感情。但若写诗者本人心中并没有浓厚的爱意,那么他必定不会忐忑不安地问那样一句话。爱情,总是相互的,若没有深厚的感情,怎能换来对方的一往情深、生死相随?
这一记侧面烘托的间接描写手法,一箭双雕,既写出了对方对自己的深情,又不动声色地完成了自己的“爱的宣言”。这生死相随的誓言,想必是两个人共同的心愿。
这一首,在仓央嘉措的众多诗歌里,不算是最著名或者最出众的,却是为数不多的提及了所爱的人对于爱情的坚守的诗作。
无奈此心狂未歇
今生,若你爱过一个人,你会知道,这爱情,太沉太重,是负荷不起的沉醉,让人不自觉有了逃跑的念头。而若是想爱不能爱,会把自己逼向崩溃的边缘,悬崖下面,等待着的是万丈深渊。
恍然发现,在爱情面前,真的需要坚定不移的信念。
我往有道的喇嘛面前,
求他指我一条明路。
只因不能回心转意,
又失足到爱人那里去了。
——于道泉
在午后温暖的阳光下,顺着玫瑰花茶弥漫出来的醉人的香甜气息,一个不经心,又惊见了那个玫瑰花一样的男子——仓央嘉措。
这个时候,他已经长大成人,玉树临风,相貌英俊。在爱情来临之前,他单纯地快乐着,世间五颜六色的绚烂,只迷乱了他的眼,从未乱过他的心。
直到有一天爱情来了,排山倒海一般。仓央嘉措的心被扰乱了,从此他的生活中不仅仅只有快乐,爱情来的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如影随形的“朋友”——忧伤。从此,他的生活再难回到过往的平静。世间五颜六色的绚烂,让他觉得自己的眼睛和心灵都要被灼伤了。
这一切令他的心里不再只有至高无上的佛法。爱情一点点地渗进他的生活,兴奋、欢乐,让他迷乱了性灵,忘记了所有的痛楚。
佛家的禁令和他特殊的身份,为这份感情罩上了一种偷尝禁果的刺激和神秘。那原本自由的性灵,借着爱情,肆意地张扬了一回。仓央嘉措被这巨大的爱情欢乐所包裹着,全然忘了在后面等待着自己的重重劫难。直到他的所作所为撼动了佛家至高无上的信念和权力,那最初的快乐终于成为了一个难以解开的茧。
他彷徨地站在山峰上,前是万丈深渊,后是悬崖陡壁。
他低下头,虔诚地跪在布达拉宫,虔诚地跪在莲花台上的佛祖面前,跪在得道高僧面前。
他忏悔对感情的放纵,以至欲出而不得,欲进而不能。他求高僧指引一条明路,使自己不再如此痛苦。高僧一定深明仓央嘉措的心思,也深谙他其实还未完全放下红尘俗事,但必须告诉他停止吧,放手吧。因为他的身份,因为他在世人面前已是看破人生的佛。
仓央嘉措还没能学会自如地拿起放下,还不能在爱情和佛法之间回转,他把那么多年给了佛法,如今,他想给她再多一点的时间。
终于,他还是回到了爱人的身边。
是沦陷吧?会万劫不复吧?那又怎样?
仓央嘉措不是不知道,通往佛法的道路,大道明明,在等待他的归来。
可是,他真的舍不得放手。他只能期待,此刻的山重水复,也许是下一刻的柳暗花明。
在这首诗中,于道泉、曾缄、刘希武三位先生各自采用了一种诗体。也难得,三位先生都没再往这首诗中加入过多自己的感情,三首诗在表意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但同样各有各的妙处。
至诚皈命喇嘛前,
大道明明为我宣。
无奈此心狂未歇,
归来仍到那人边。
——曾缄
我过高僧前,
求指光明路。
尘心不可转,
又往情人处。
——刘希武
于道泉的译本中“又失足到爱人那里去了”中的“失足”二字,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仓央嘉措本身的身份和爱情之间的矛盾,也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无奈。
曾缄的诗中,我极喜欢“无奈此心狂未歇”一句,单单一个“狂”字已经完美地表现了仓央嘉措对爱情的狂热和锲而不舍,表达了他对“自我选择”这条路的热烈追捧。而“未歇”又表达了他会一如既往地追寻自己所想要的东西,爱情也好,自由也罢。
但对于这首诗来讲,最让人赞赏的应该是刘希武的译本。因其既尊重原意,又简短富有哲理。
其中最为让人称道的就是后两句:“尘心不可转,又往情人处。”在于道泉和曾缄的译本中,虽然也提到了两心的对比,但都没能准确地为这个“心”定位。于道泉用“回心转意”一掠而过,曾缄直接用“此心”笼统表示,直到刘希武的译本,才出现了“尘心”这个词。“尘心”,尘世之心,世俗之心。仓央嘉措之所以成为西藏宗教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正是因为他对尘世自由、平凡人生的渴望。
这种心情,不恰恰就是“尘心”吗?而对于“情人”二字,则视乎你心中对仓央嘉措的定位,可以是真正意义上的情人,也可以指俗世中的万物。
生活和爱情都在自己的意念中,能左右自己的也只有那一颗心。
情缘虽尽莫咨嗟
花开的时节已过,
松石蜂儿并未伤心,
同爱人的因缘尽时,
我也不必伤心。
——于道泉
心中有根刺,扎在那儿,隐隐生疼,却不忍心拔去,仿若拔去了,那苦苦追寻的东西便丢失了。这感觉就像在深夜读仓央嘉措的诗,免不了悲伤,却停不下一读再读。
花开时,一片红色,铺满了你来时的路,你轻轻地牵起我的手,说要用尽此生温柔守候。微笑,绽放了整个脸庞,我为爱亭亭盛开,万千妖娆。
时光,转眼凋零了容颜,凋落了你对我的爱。你转身离去,寻找另一片花开,却忘了当初的誓言。你身后一地花瓣零落,满目嫣红如血。凋零残败亦如我的心。
而我,却没有勇气手刃那深入骨髓的背叛。
这首诗,让人陷入莫名的悲伤。
虽然常言总说,缘来缘去不由人半分,可是事实上缘分往往由人自行剪断。断了也罢,却偏偏把责任推给天意。
还是仓央嘉措说得好:“同爱的人姻缘尽时,我也不必伤心。”你看,那花已经纷纷落下,花开的时节已过,蜜蜂留在这里也是白白浪费力气。这就如同你我的缘分感情一样,既然你对我已无意,那我也无须枉自伤怀。自此好聚好散,各安其命。岁月静好,你我再无关联。
只是说来简单,做到却难。有多少人终其一生都活在有缘无分的阴影中,郁郁寡欢。
忘记,放下,才能收获心安,这是佛给我们的指引。
一开始仓央嘉措并不明白这个道理,直到等待了一季的花开花落,才慢慢地悟出其中的真意。
于是他写下这首诗,希望通过自己的感悟,教会人们学会淡忘。淡然处世,才能看惯清风明月。看得透得失,才能超然物外,收获意想不到的快乐与自由。忘得掉,忘不掉,只在一念之间。
又一次要牵扯到“情歌”和“圣歌”的话题。通过这首诗,我们更可以认定,很多时候,仓央嘉措的诗歌想要传达的东西不只是爱情,也是他对人生的“悟”。而这“悟”体现的全是佛教的核心思想——超越。超越一切,摆脱一切羁绊心灵的因素。在这首诗里,仓央嘉措想要传达的就是超越情感。
只是后来,几经辗转,仓央嘉措的很多诗歌都被传诵成了爱情诗。于是他的诗和他的人才会在流传中被冠以艳丽的色彩。
单单是在曾缄的译本里便能看出很大的不同来,这不在于诗体的形式,而在于内容的视角。
我与伊人本一家,
情缘虽尽莫咨嗟。
清明过了春归去,
几见狂蜂恋落花。
——曾缄
细细比较,于道泉的译本相对乐观豁达一些,如男子对自己的鼓励,而曾缄的译本相对比较忧伤悲观一些,似女子的叹气。
于道泉译本中的男子微笑着劝诫他人莫伤心,缘分得失之事,来去自有规律,不应看得太重。看那辛勤耕耘的蜜蜂,可曾因为花落了而自顾落泪,全然不顾之后的生活呢?于是听者,瞬间觉得豁然开朗。
在曾缄的译本中,少女漫步于落花时节的林荫小路,叹气声声,忍不住泪光闪烁,又看到落花凄美,狂蜂离去,更是感慨天下男子皆负心,同眼前这离了落花的蜜蜂一样,让听者更觉悲伤难抑!
同一首诗,站在两个角度来译,完全变成了两个故事。这故事中,一定也有你我的。
而造成同首诗风格如此迥异的原因,大致离不开两个因素:一是亲身经历,二是长期研习佛法所练就的豁达。作为西藏宗教的领袖,仓央嘉措所受到的佛法熏陶自然不同寻常之人,他在位期间,所经历的大是大非较之寻常人,也是更多一些。
这两个元素累积起来,使得他的诗或多或少地都会传达出“普度众生”的教化意义,给人以心灵慰藉。不管他的诗歌表面看来是不是爱情诗,但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这些诗或多或少地都起到了安抚众生的作用。
黄蜂散尽花飞尽
草头上严霜的任务,
是作寒风底使者。
把鲜花和蜂儿拆散的,
一定就是它啊。
——于道泉
这首诗和上一首相比,虽然同写的是蜜蜂与花的爱情,同样是离别的主题,但主旨却完全不同。
这世间有很多人,明明可以在一起,却执意要错过,错过了花开,又错过了花落。从没有人阻止他们的脚步,他们自己却离开了,或因爱得不深,或因不再爱了。
若说仓央嘉措的第一首蜜蜂和花的诗讲的是随缘,那么,这首诗中讲述的则是被阻挠的爱情。
有些人明明相爱,下定决心一生相守,却难以实现,连牵手都是奢侈。他们中间隔了千山,隔了万水。
世界上那么多美满幸福,却没有属于他们的花好月圆,离别都是难逃的劫。
爱,由不得自己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