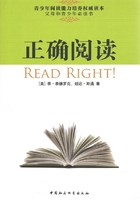/陈缺
山势陡峭,道上的泥土在雨后变得松软油亮,两旁茂盛的杂草覆盖了路面,翠绿铺了一地。康明抖了抖背篓内快要倾倒出来的草药,踢开了脚边的石子,一手拿着木棍撩开路上的草木,仔细查看,边走边呢喃:“还差一味药。”正午的阳光毒辣,仿佛将松针林都烤出了清香,康明像是走在羊毛毯上,脚步变得有些虚浮。眼前终于出现了几株淡红色的植物,康明呼出了一口浊气,屈下身子轻轻地刨出,拍了拍泥土,放入背篓中。从前传说这座山头里住着黑瞎子,很少有人敢独自上山。康明第一次入山时胆怯得发抖,胡乱地拽了几把草药,就飞也似的冲下山,那天晚上母亲的破锣嗓,伴着男人隐忍的咳嗽声响了一夜。如今已经到过这座山头无数次了,康明能顺溜地报出沿路的草木名称,五爪金龙、牛蒡子、鹅掌花和鬼灯笼。暖风熏得人昏昏欲睡,捋平躁动的心,让人的胸腔里响彻着与植物脉搏相同的频率。
各家的炊烟陆续从烟囱中爬升,承载着每家的喜或悲,直至消失在达不到的苍穹。康明放下背篓,朝屋里喊道:“妈,我回来了。”出来的却是听到声音的男人,他看见背篓里的草药,朝康明感激地笑了笑。男人咳了起来,脸又苍白了几分,眼睛里有了痛苦的神色。康明伸手轻缓地顺了顺男人的后背,等到咳嗽声低下来的时候才扶着男人进了屋。室内有些昏暗,弥漫着浓浓的中药味,甚至能听见这个房子内部发出的粗重的喘气声。他坐在那里,翻开书的另一页,康明摸了摸右手被划出的血口,终于感觉到了细微的刺痛。昏暗的灯光下,室内的物品棱角都很模糊,就如同在某一天,他来到康明家门口,一开始就是模糊的。
康明吃饭前在牌位前上了一炷香,看着照片里粗糙的脸,深深地记在心里。遗忘,是另一种背叛,而接受,或许也是困于自己设置的不忠的一种定义。康明的父亲五年前已经去世,男人也在这个家里待了五年。当初县领导即将升迁,康明父亲所在的矿井出了意外,一同下井的八个人都困在了井下。这样重大的事故本要紧急上报,申请救援,可是救援队伍到村里至少要两天,当时落后的救援器械要挖通地势复杂的矿井需要四天,如果中途出现意外,又要耗上一段时间。这样一来,井底下的人等到救援的时候,存活的概率也很小了。那个荒凉的山沟上,扑簌簌的风依旧刮着,似乎无论太阳在哪个方向,总有一群人踩踏在乱石上,原本的泼辣蛮横地消失在抿紧的唇角,她们有着相同的表情,眼睛投向同样的方向。等风终于落了,山沟里的黑影也落了。事情的发展似乎是理所当然却不忘将最后一根稻草扔在那些怀着卑微希望的人身上。听取了别人意见的县长为了不丢掉乌纱帽,给了康明家一份协议,七份协议之中的一份,第八份随着那个坠下山崖的女人,被山谷里的风吹到很远的地方。那一年,康明家的存折上多了一笔钱,那可能是贫穷的山里人一辈子都挣不来的财富,恰逢那一年粮食遭了大水,村子里面充斥着的都是腐烂的味道,那是康明长大以来接受过最多的目光,带刺的羡慕,就像勾进肉里面的铁红色钢钉,拔不去的煎熬。那份协议是康明的母亲签的,放罢笔的那一刻,康明望向矿山那边狭窄的天空,或许,会有一场大雨。那晚,母亲的屋里传来呜咽的声音。康明知道,这个不眠之夜,有那么一群人同样无可奈何却又痛得撕心裂肺,但明天太阳照旧升起的时候,活着的人要在脸上抹上厚重的泥巴,掩去所谓日子落幕的痕迹。
吃饭的时候,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话,男人在一旁安静地倾听,仿佛所有的话都被他记在了心上。康明正出神,母亲突然道:“阿明,听说你们学校来了个新老师。”
因为教育改制,村里的中学合并到了镇上的一中。由村里到一中的距离约莫有3里地,平时都要徒步行走,家庭富裕些的,便骑着辆老旧的自行车,“哐当哐当”声响了一路,将人拖入一个久远的记忆中。当时迁校的通知传下来的时候,康明房间的灯亮了一夜,第二天康明和少数学生留在了这几间破旧的泥瓦屋中。面对男人焦急的询问,康明只淡淡地丢下一句:“我走了,谁去采草药……”康明记得男人当时愧疚和自责的眼神,而康明却在懒洋洋的午风中,闻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味道。
男人当初来到村里时也曾在这所中学里当老师,领着不多不少的工资也算补贴家用,当时矿难补偿的钱因为偿还旧债已所剩不多。瘦弱的男人担起了这个家,闲暇时跟着村里强壮的男人一起下田干活儿,因为手脚慢,一干便是一天。康明记得母亲当时看见男人佝偻着背挥舞锄头时抹泪的情景,那一刻惧怕“寡妇门前是非多”的母亲才真正地接受了男人。再到后来,男人的身体渐渐不行了,到学校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现在的学校里只剩下年老的李老师任教,有时需要连续上一天的课。而新来的老师是李老师一个月前收留的外地女人,听说了李老师的苦处,主动要帮忙。
铃声响了,教室里仍然乱哄哄的。一个女人走进了课室,她蓄着齐肩的黑发,皮肤是异于乡村妇女的白皙,眼睛不大,却是上挑的丹凤眼。教室里的男生都安静了下来,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的老师,而有些女生则意味不明地撇了撇嘴。女人扫视了整个教室,窗外的鸟不合时宜地鸣叫了一声,伴着她清亮的声音冲撞着康明的耳膜。康明觉得鼻子有些痒,甜腻的花香久久地在嗅觉范围内停驻,讲台上的老师嘴巴不断地张开闭合,每一下的频率牵动着她太阳穴上跳动的脉搏。今天教室里的窗户显得过分狭小,连景色都拥挤在了一起,康明将视线从窗外转了回来,朝讲台多瞥了两眼,尔后刻意地收回目光,又变回了那个寡言内敛的男孩。
康明盯着课本上木棉花的插图,想起了校门口的那棵木棉树。有几朵木棉花小心翼翼地展开花蕊,面朝阳光,然后再在某个时间沉重地坠落,作最后一次告别。叶要落,何况是这沉重的花,开得再好,有时也是树所不能承受的。每年五月,康明都会在木棉树下用簸箕收集起那些硕大的花,然后将它们轻轻地切开,蕊瓣分离,放在阳光下曝晒。晒成花干后,就成了康明家必备的木棉凉茶。男人最爱喝这种茶,每次拿起那个豁口的碗,他的眼睛都会眯成一条线,一副满足恬淡的样子。今天吃早饭的时候,康明往男人的碗里倒上了热腾腾的凉茶,蒸腾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视线,康明喝下第一口有些发涩的凉茶时,听见母亲叹了一句:“这花都落了,我也成黄脸婆了。”屋子里面只能听见康明大口喝茶的吞咽声,男人皱起了眉头,想张开口安慰,却最终只憋出一个“不”字。康明的喉咙有些滚烫,眼前的男人却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似乎找到了某个解决方法,笑了。
正出神,林老师走到了他的跟前,仍是笑眯眯的模样:“康明,你放学的时候留下来。”在周围的一片哄笑声中,康明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
夕阳在发挥它最后的热度,康明忐忑不安地跟在林老师的身后,不敢发一语。看着眼前的女人不熟练地干着家务,烧水做饭,忙乱得一塌糊涂。康明最后不忍那将要被打碎的第三只碗,立刻上前接手烂摊子,开始自己熟稔的活计。正忙着,康明分明听见林老师在身后一声如释重负的呼气声,他难得地笑了:“老师,您留我下来该不会是为了帮你烧水做饭的吧?”林老师慌乱地摆摆手,被柴火熏得发红的脸有些紧张:“当然不是,是你上课不专心才留你的。”这句话让康明陷入了沉默,像是想起了什么,再开口就乱了。康明快速地完成了手边的活儿,在林老师小心翼翼地注视下,终于端出了热腾腾的饭菜。来不及回应林老师的挽留,康明简单地道了别就匆匆地赶回家,今天还没有帮男人熬中药,他怕是又咳得厉害了。
回到家,果不其然听到了男人那令人揪心的咳嗽声,屋内却还有另外一个人。
“季林,你这又是何苦呢?”
“别……别再劝我了……快走吧……不要……要……再来了。”男人断断续续的声音响起,一声叹息若有若无地回荡在屋子里。
随着陈旧的木门被打开的声音响起,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康明和中年男人都有些发愣。最后,在康明抱有敌意的目光下,中年男人尴尬地离开了。他是那个本应被罢免现在却反而升了两级的县长,那次矿难事故的主要负责人。
康明走进屋子里,男人在抚摸着一本黑皮笔记本,抬头见是康明,张了张口状似要解释,最后叹了口气作罢。那本封面简洁的笔记本上贴着男人的名字“季林”,他总是保持着这样一个习惯,用一张写有名字的白胶布贴在他所熟悉的物件上,这些康明和母亲不可理解的行为成为了男人的一种执着,正如他那本黑色的笔记本,似乎藏着别人读不懂的故事和沉甸甸的情感。突然,康明的手触碰到一个硬质的冰凉物体,瞄了一眼,脑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手就把它快速地揣到了兜里。等到康明感觉到口袋里沉甸甸的坠感的时候,他想起了早晨教室里的花香,钻进了自己的鼻腔,然后轻轻地挠了自己的胸口,几乎不可察觉。
香炉里的香仍在燃烧着,由淡黄转白灰,慢慢地落了,连那些滚烫也变得冰凉。
滑腻的淤泥没上了膝盖,康明慢慢地往前迈步,手上不忘往水里扑腾着,看准时机快速地向水里劈去,一连串动作流畅自然,将一条鱼摸起扔向小土坳上的筐内。
“哎,这些泥巴都要糊到我的衣服上了。”站在坳上的妮子抱怨道。
康明没有理会,继续认真地在水中寻找猎物。倒是一旁的张扬调笑道:“泥巴啊,泥巴,你为什么要黏着妮子不放啊。”接着状似认真倾听的模样,然后阴阳怪气地朝妮子说:“那是泥巴想要知道,爱干净的妮子为什么要跟着来鱼塘啊。”正累得满头大汗的李辉朝张扬眨了眨眼:“人家那是跟着夫婿过来的。”说罢,瞥向了康明的方向。
妮子羞红了脸,大声嚷嚷道:“李辉,你这黑鬼,再胡说我就撕烂你的嘴。”
李辉也不甘示弱,露出与皮肤颜色不符的大白牙继续调笑道:“嘿,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跟来鱼塘却不下水啊?”
“那是……那是因为我怕水……”妮子嗫嚅道。
显然没有人相信她的这番说辞,大家笑作一团。妮子看向康明,这个瘦弱的男孩却仍旧在继续他的动作,丝毫不关心周围的一切。从前这个让她着迷的认真的模样,现今却残忍得像腊月的冷风,嗖嗖地直刮心底。
康明数了数筐内的鱼,本要提起筐的手顿了顿,似乎想到了什么,又低头继续捞了两尾。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康明顶着一脸泥来到了泥瓦房前,屋子内不时传出几声低呼声。康明歪了歪头,抿嘴笑了。提着两尾鱼来到厨房,跟预想中一样,女人正在忙活着做饭。康明自然地接过了她手中的活儿,看到一旁女人呆愣的模样,康明又笑了:“我今天去了鱼塘,顺便给你带了两尾。你去洗洗吧,等会儿下锅。”语气熟稔自然得不像对一个长辈的对话,林老师终于从惊讶中醒觉,提着两尾鱼又开始忙了起来。
饭做好后,第一口热气还没完全飘散在空气中,康明就赶忙洗了洗手,准备回家。林老师此时也满头大汗,第三滴汗划过她的眼角的时候,衬得她的眼睛更黑更亮了:“你又要赶回家了吗?听别人说,你父亲身体不是很好,你是要赶回去照顾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