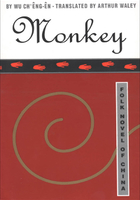“您又不是没有这样做过。”裴简轻笑了一声,“从小到大,儿子不知死过几回。只可惜每回都让您失望,没死透了又活回来。不过您放心,儿子在京中几年,从没跟人说过半点您的不是。就算受了伤,也都是自己咬牙忍着,没哭没闹地给您丢人。至于姑祖母那边是怎么知道的,儿子委实不知,不如您自去问问她老人家!”
裴和面色阴晴不定。
裴简扫了乌尔玛一眼,目中的寒光让她不自觉地微颤了颤:“其实有一次就差点如父亲愿了,儿子本来已经一脚踏入了黄泉,结果被人不小心又给拽了回来,啧啧,父亲您这样看着我做什么?难不成这事您会不知道?”
“也是,您多少年了连正眼都不愿意看儿子一眼,又怎么会知道这种小事。”裴简并没在意院子里有乌尔玛的存在,仿佛她就是棵木桩,是缕空气。他慢条斯理地解了外衫,将襟口扒开,露出胸口自锁骨到左肋的三条狰狞疤痕。当年紫红色的巨大伤痕现在颜色已经变淡了不少,但依旧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像三条千足蜈蚣趴在裴简白皙的胸膛上,狰狞可怖。
裴和也被吓得后退了两步。
裴简又慢慢将衣襟合起来,把外衫穿好。
“那年太皇太后宣召儿子入京,一路上下毒的,扮做土匪截道的,还有流民冲击的不知多少次。只有这次最危险,儿子九死一生,损失了好些忠心的下属,这才留了半条命艰难进了城门。太皇太后见儿子受了这么重的伤,心疼的很,还给了我不少赏赐。只是这伤疤是去不掉了,得跟着我一辈子。”裴简系好了腰带,对着裴和施了一礼,“父亲若没什么事,儿子还要去荣王府一趟,告辞。”
裴和直到裴简的身影完全消失,也没能说出一个字来。
他转过身,看着乌尔玛,唇上血色尽失。
“乌尔玛,这是怎么回事?”
乌尔玛一脸的震惊:“侯爷,您为什么这样问我?世子受伤的事,您前些年就知道的,他曾经写信回来过,京城也有人来问过啊!”
是啊,是有信来,是有京城宫里来的人质问过。
他当时是什么反应?
以为裴简娇气,又像以前一样,动不动就说有人要害他,借此挑拨他与乌尔玛的关系。
觉得宫里来的人骄横霸道,仗着自己是京城来的,或是得了荣王的授意,故意做出高高在上的样子给他添堵,让他难堪。
他写了回信,把裴简骂了一通,又将宫中的人不客气地赶出了滇南。
他当时想着就算裴简受了伤,也不过是擦破点油皮,受了点惊吓,男子汉大丈夫,总是这样大惊小怪,跟个小娘儿一样,弱不经风的能有什么出息?
今天才知道,裴简的伤有多重。
那三条狰狞的伤疤就像活了过来,浮在他的眼前不住的扭动,嘲笑他的无能,往死里恶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