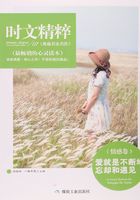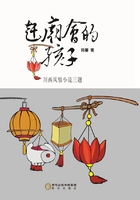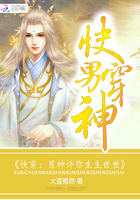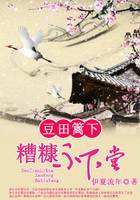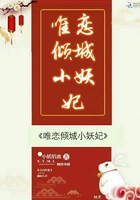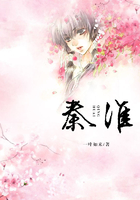四位学贯东西的大名人,恰如其分地选择了四座大城市,分别登台讲演,构成了1922年中国思想文化界一道绚烂的风景。各人论题不一,表面上毫无关系;可在某些关节点(比如白话诗的评价)上互相指涉,值得仔细玩味。在具体讨论各自讲演内容前,有必要先欣赏讲演者的风采。
在没有录音录像设备的1920年代,所谓“讲演者的风采”,只能靠时人的文字来呈现。这里需要史料的钩沉与考辨,更需要想象力的发挥;只有读者的共同参与,我们才能大致复原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场景。
不妨倒过来,从以“讲演”为“文章”的周作人说起。单是讲演前的认真准备,以及讲稿之可以直接发表,而且还是可圈可点的“美文”,很容易判断周氏讲演的风格。上述应邀为清华文学社讲演《日本的小诗》事,在梁实秋的回忆文章里,有精彩的描述。梁氏的记忆力真好(不像是有日记做依据,因所记日期,常有一两年的误差),这两篇文章发表在周作人日记公开刊行前,提及那天进入八道湾周寓时鲁迅正和写新诗的何植三谈话,得到周作人日记的证实。梁不愧是散文大家,关于周作人讲演时状态的描述,实在有趣得很: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他仆仆风尘的到了清华园。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岂明先生便是一个实例。我后来看到他的讲稿发表,才明白他讲的原是松尾芭蕉等等的俳句。梁实秋:《忆岂明先生》,《梁实秋怀人丛录》200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这也未免太夸张了,连主持人都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一般听众岂非更是蒙在鼓里。《忆岂明先生》中这段渲染过度的描写,在《忆周作人先生》那里变得节制多了:“由于周先生语声过低,乡音太重,听众不易了解,讲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讲稿,随即发表。”梁实秋:《忆周作人先生》,《梁实秋怀人丛录》272页。在电视直播成为时尚的今日,像周作人这样念讲稿,效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可在渴求新知的青年学生眼中,有真才实学的启明先生,“依然受人敬仰”。
同样是梁实秋,其描述梁启超的讲演,完全变了一副笔墨。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梁实秋回忆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的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310—312页。在另一则短文里,梁实秋将同在台下听讲的梁思成也拉扯上,场面更为生动: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的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听梁任公讲演》,《大成》130期,1984年9月。这两段文字实在太精彩,以至你不忍心质疑其真实性。梁启超讲演时很认真,也很投入,效果也不错,这点毫无异议。我感到疑惑的是,如何看待任公先生浓重的乡音,是否像梁实秋所说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311页。
在夏晓虹所编《追忆梁启超》里,除了梁实秋这则名文,还有梁容若的《梁任公先生印象记》和杨鸿烈的《回忆梁启超先生》同样涉及任公先生的讲演。前者文章写得不错,作者很会捕捉细节,渲染气氛,只是其笔下的梁启超,讲演的效果实在不理想:我最初听到他的讲演,是北京高师国文学会邀请,讲题是“清初五大师”,时间在民国十二年。他那时是五十一岁,蓝袍青褂,身材魁伟,有些秃顶,却是红光满面,眼睛奕奕有神。讲起来有许多手势表情,笑得很爽朗。他引书成段背诵,背不下去的时候,就以手敲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下去。敲几次想不起来,就问当时陪听的教授钱玄同、单不庵、杨树达等。熟于学术史的单不庵先生,常常能随时提醒他。他懒于写板书,他的广东官话对于我们很生疏,所讲的问题,事前又没有预备知识(这时我对于黄黎洲、王船山、顾亭林、李二曲、朱舜水等的书和传记全没有读过),所以两小时讲演的内容,听懂的实际不到六成。当晚在日记里写“见面不如闻名,听讲不如读书”,因而联想任公先生南北奔驰,到处登坛讲学,究竟是否收到比著书更大的效果,怕要大成问题。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记》,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339—340页。照梁容若的解释,当年北京城里大学文科教授浙江籍的最多,学生于是练就听浙江方言的本事;至于广东籍的,只有梁启超和黄晦闻(节)。后者讲六朝诗,印有详细讲义,所以不感困难;困难的是听激情洋溢的任公先生讲演,很少人能完整记下来。
梁实秋、梁容若都只是偶尔听讲,其褒贬未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更值得重视的,是梁启超晚年入室弟子杨鸿烈的回忆。先是私淑弟子,后又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追随梁师读书,毕业后又因梁的推荐任教南开大学,课余还常到梁宅请益、借书,杨君应该说是难得的见证人。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中,杨君是这样谈论梁启超的讲演的:长期以来,梁氏虽为众所公认的一代作家,但在说话的时候,虽非蹇缓口吃,却很缺乏流利明白的口才,他在讲演的时候有时只闻“啊啊”的声音,即表示其词不达意。……后来,因梁氏常与外省人周旋接触,新会乡音便逐渐改变,所以他某次提及在河南开封时,应冯玉祥督办的邀请,向西北军的官兵讲话的一段故事,说当时,因自己一时情感兴奋,竟滔滔不绝,使冯玉祥首先放声大哭,全军亦泣云。但这只是他一生所仅有罕见的场面。事实上,全国大多数听众都以不能完全明了他的西南官话为憾。尤其在华北方面,如一生最崇敬他的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史学教授王桐龄氏,凡有梁氏的讲演,几乎风雨无阻,每次必到,但总是乘兴而往,怏怏而归。问其所以,总是自认对于讲词的某段某节,竟完全听不明白,其他人士,十有五六,亦均抱同感。杨鸿烈:《回忆梁启超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287页。中间省略部分,是引录王照关于戊戌变法时梁启超不会讲官话,口音差池,导致与光绪君臣间相对,无法表情达意的故事。此类故事不止一见,其真实性有待验证。至于任公先生的浓厚乡音,妨碍其讲演水平的发挥,我想是确定无疑的。看看当年东南大学的学生,是如何描述梁启超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情景:他并不是一位具有讲话天才的人。他教书和讲演都有充分情感,可是都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甚至急时还有口吃现象。他的广东官话也要听过一两星期才能习惯。可是课后私谒则清谈娓娓,引人入胜,于为学作文都有指示。罗时实:《由南高到东大》,《传记文学》1卷4期,1962年9月。如此说来,所谓梁启超的广东官话比标准国语更有力,也更有味道,大概只能理解为“不平常”、“有个性”。
虽说因夫人指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的自述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52页。,必须稍打折扣;梁启超带新会口音的官话,应该还是比章太炎的浙江话好懂。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和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民报社听讲》,都提及太炎先生东京讲学如何“新谊创见,层出不穷”,而且“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参见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261、264页。。但请注意,第一,这是小班,师生坐而论道,比较容易沟通;第二,谈的是非常专业的《说文》等,知识背景很清楚;第三,听众多为浙江人,没有语言障碍。到了1930年代的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可就不一样了,汤炳正称:“我们听讲的学生,每听完一次讲,就三五成群,互对笔记,习以为常。因先生浙语方音极浓,我开始听讲,很感吃力,后来才习惯。”汤炳正:《忆太炎先生》,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457页。
一心求学者,可以通过三五成群互对笔记来解决疑难问题;至于一般听众,面对如此艰深的讲演——从国学到方言,实在没有把握。1936年上海发行的小品文杂志《宇宙风》上,有一则乃蒙所撰文章,嘲讽章太炎的讲学,语调相当刻毒:他坐在藤椅上,一面吸烟,一面低声的演讲。低声没问题,因为听众很少;只是满口土话,我们一点都懂不来。好在他讲完一段,那胡子大汉,便在黑板上将大意写出,我们才知道今天所讲的,不是国学的,而是革命的。……在演讲的姿态中,章先生是个悲剧的人物。他不知道自己的土话,人家不能了解,而好以眼光,追寻听讲人的颜色。乃蒙:《章太炎的讲学》,《宇宙风》22期,1936年8月。不知道是作者年少气盛,还是小品笔调使然,此文对于太炎先生的讲学,只有嘲讽,而无丝毫“同情之了解”。
在一般人眼中,新旧截然对立,讲国学毫无疑问是落伍的表现。但学界不至于如此近视,1932年春天太炎先生的北游,还是受到北平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周作人追忆太炎先生在北大研究所讲《论语》时的情景,不无诙谐与幽默:当日讲演系太炎所著《广论语骈枝》,就中择要讲述,因学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语,所以特由钱玄同为翻译,国语重译,也是颇有意思的事。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52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当年的学生中,能听懂且感兴趣于这种专业讲演的,大概不是很多。校方于是又安排了一场普及性质的公开讲演,地点是在北大三院的风雨操场。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还有站在窗外的。据张中行事后追忆: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张中行:《负暄琐话》6页。就像周作人说的,“国语重译”,确实是“颇有意思的事”。可对于渴望传播或接纳新的学识与思想的当事人来说,这事情一点也不好玩。想想章太炎那热切地追寻听讲人的目光,或者因听不懂浙江方言而万分苦恼的听众,你能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回到1922年上海举行的有关国学的系列讲演,以太炎先生名气之大,“观众”肯定不少;以太炎先生方音之重,“听众”估计不会很多。读《申报》的报道,听众从三四百迅速上升到近千,而后又回落为七八十,自在意料之中。曹聚仁说得更具体,这十回的系列讲演,逢星期六下午举行,第一回听众千人,第二回不到一百,最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结束的那次好些,有七八十人。除了世人对于国学并无太大兴趣,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缺乏基本了解,更重要的是,“因章师的余杭话,实在不容易懂”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5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二年,太炎先生应邀到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讲“治史学的方法”,满口余杭土调,急得学生们吵吵嚷嚷,要求在座的史学家柳诒徵帮助翻译,于是:“柳先生翻译时,好象西人讲学,中国人翻译一样,但他声如洪钟,有条不紊,娓娓动听。”邵镜人:《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传记文学》1卷3期,1962年8月。
有趣的是,乃蒙在嘲笑章太炎不合时宜的讲学时,拿胡适作为比照:“我更而想到人间的晚年,隔离时代的悲哀!胡适之演讲‘儒与孔子’,听众有一二千;而一代大师的章先生,只能于不相干的十数人面前,销磨生命的余剩。”乃蒙:《章太炎的讲学》,《宇宙风》22期,1936年8月。而梁容若在回忆梁启超与胡适共同主持戴东原二百年生日纪念会时,也是明显地偏袒胡适:任公两小时的讲演印象模糊,倒是“胡适之的十分钟演说,留下了清楚的回忆”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记》,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340页。。同样不露痕迹地褒贬一番章太炎的讲学,张中行转过身来,表扬起胡适的口才与幽默感:三十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张中行:《负暄琐话》34页。可以与此相印证的,是此前十年胡适到北京女高师兼课时的情景。苏雪林在《胡适之先生给我两项最深的印象》中,用烘云托月的笔法,描述胡适讲演的风采:我们国文系的教室本与我们的图书馆毗连,中间有可以自由开阖的扇槅门隔开为两下。每逢胡先生来上课,不但本班同学从不缺席,别班学生师长也都来听。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图书室槅门打开使两室合并为一。甚至两间大教室都容纳不下,走廊里也挤满了人,黑压压地都是人头,大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倾听这位大师的讲解。这个印象留在我脑子里,永远不能漶灭。苏雪林:《胡适之先生给我两项最深的印象》,见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348—34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与张、苏二君不无夸张的描述有别,徐也是在北大二院听胡适讲哲学,感觉却不太好。“听讲的人不但挤满了课堂,而窗外也站满了人”,这种景象,引诱胡适进一步发挥其“很活泼的口才”,以满足不同层次听众的需求。如此一来,对于热心求学者,未免有所怠慢。像徐就抱怨“这像是公开演讲,内容很通俗”参见徐《念人忆事》,见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430页。,不像是哲学系的功课,因此而放弃选修。
北大的课不好讲,尤其是大课,能讲到“使发困的人不想睡”,这可不简单。胡适对讲演兴致很高,对于所谓的“讲演术”——比如如何掌握语气的缓急,声音的高下,以及调子的抑扬顿挫等,很是下了一番工夫据梁实秋称,胡适1960年在西雅图会议上用英文作演讲,“事后有一位美国学者称道这篇演讲具有‘邱吉尔作风’”(参见《梁实秋怀人丛录》197页)。如此比附的是非,非我所能评判。还是中文容易体会,台北的胡适纪念馆里保存若干胡适晚年讲话的录音。因系广播稿,从属政治宣传,内容不见精彩,但胡适念起来抑扬顿挫,颇能显示其讲演学方面的训练。。可也正因为较多考虑如何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胡适的讲演,必然趋于平易畅达,而缺少幽深与奇崛。而这,与其著述风格颇有关联——章太炎的特立独行,梁启超的酣畅淋漓,周作人的雍容和缓,又何尝不是“文章”一如“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