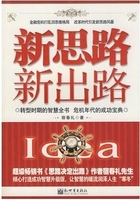对于象征派、现代派诗,单就接受者来讲,心理原型的调整和改变,固然不是容易的事,它更多与先天条件有关。但是,读者多向性与流动性的思维的养成,并不是完全由先天所决定,而更多还是在于后天的训练。接受者与创造者对于这种“野性的思维”,经过艰苦的努力,是可能获得的。
这种多向性与流动性的思维,具体地说,就是接受者努力以创造性的思维,进入象征派、现代派诗的意象复杂的内涵,进入意象与意象之间“距离的组织”,进入作品中诗人独特的思维运行的轨道。总之,要培养和训练一种“破译”象征派、现代派诗的意象与语言及传达组织的“密码”的能力。
与这种努力相反,也必然会产生在象征派、现代派诗的理解与欣赏中的误读。这种现象往往产生在以“造形”类的心理和单向性的思维面对复杂文本的时候。接受者自身的局限筑成了进入现代派诗歌世界的障碍。对于局部运用象征手法的诗《米色的鹿》的分歧与误读,即源于此;对于许多更为繁复的象征派、现代派诗的分歧与误读,也多源于此。
这里是废名的《十二月十九夜》:“深夜一枝灯,/若高山流水,/有身外之海。/星之空是鸟林,/是花,是鱼,/是天上的梦,/海是夜的镜子。/思想是一个美人,/是家,/是日,/是月,/是灯,/是炉火,/炉火是墙上的树影,/是冬夜的声音。”首先从题目来看,这是一首“无题”诗,同时又暗示是一个冬天的夜晚,我们也可以叫做《冬夜有感》。是泛写,并无那一天发生的事件或故事。对于诗题的理解,就不能过于实了,而要有一点“流动”感。就诗的内容,有的理解就很值得商榷了。
如有的鉴赏者认为,诗里写的是:“冬天的深夜,诗人默坐在书房中,他面对室中的一盏灯,眼前仿佛出现了耸立的高山、潺潺的流水,而寂静的黑夜又宛如大海一样包围着他。他想象夜空闪烁的颗颗明星,仿佛是座座鸟林,又仿佛是温馨的花,是游弋的鱼。变幻不定的星空给他幻梦般的感觉,仿佛蓝天的梦魇。而满天的星斗,倒映在海上,海仿佛是夜的镜子。诗人浮想联翩,又从夜景回到自身,觉得自己美好的思想仿佛是一个美人,是家,是日,是月,是灯,是炉火。跃动的炉火在墙上留下影子,仿佛树影一般。在诗人的感觉中,这活动的树一般的影子,仿佛是冬夜的声音。这就是这首诗在读者面前呈现的一连串的意象和诗句抒写的对冬夜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是“诗人冲破冬夜的寂寞的主观愿望”。
最富于传统内蕴的意象,和跳跃性极大的意象组合,由于受一种非现代性的思维的限制,被引进了一种非常死板的理解。一些重要的意象,失去了诗人创造中本来的意义。
诗人的心情是寂寞的,又是洒脱的。那盏深夜独对的孤灯,在这里不仅是客观的对应物,也是诗人“知己”的象征。“若高山流水,有身外之海”,就不是什么“眼前仿佛出现”的“耸立的高山”和“潺潺的流水”,而是诗人独特的思维创造出来的富于暗示性的、别具内涵的意象。前一句讲诗人与灯的关系。这里化用了一个人们熟悉的美丽的古代典故:钟子期听俞伯牙奏琴,觉得声若“高山流水”,由此钟子期被引为知音。后一句中的海,也就不是自然的海,而是诗人独对孤灯,似乎找到了“知己”,进入了对于生活和自己生命思考的“人生之海”。独对孤灯是寂寞的,但是找到了“知音”,于是便可以得到一种脱离世俗的快乐,进入超于现实的想象世界之中。“身外之海”,既是寂寞的包围的象征,又是想象的自由广阔天地的象征。它可以容含无边美丽的一切,于是才有“星之空是鸟林”,不仅灿灿发光,而且有动听的声音。下边,均是形容“身外之海”的。那里有美好的一切,是花,是鱼,是月,是日,那是很美、很自由、很高洁、很纯净的世界,但又都是无法捕捉的遥远的存在。“海是夜的镜子”,与前边的“海”相呼应,显然不是一个孤寂的象征。夜在海里鉴照自己的美丽。海因“星之空”而显得丰富幽深。“我”在思考中可以彻悟人生的一切,因而思考着是美丽的。戴望舒在一首诗中说“我思想,故我是蝴蝶……”,就是这个意思。诗人告诉我们,美好的想象代替不了无声的现实。多少美好的遐想,仍然逃脱不了现实的制约。人生的寂寞感与孤独感,是与生俱来的。独对孤灯,又回到孤灯,最后面对的仍然是身边的炉火与“墙上的树影”。或者,另外一层意思是说,一个人一旦彻悟人生之后,就会获得更大的自由。后边的在灯前的感受,已经不是开始时独对孤灯的心境了。诗人感到,连身边的炉火也是那么美丽而有诗意,炉火的身姿乃如映在“墙上的树影”,它发出的是噼噼啪啪的“冬夜的声音”。
鉴赏者在解释中的误读在于,他离开了诗人带有很大隐藏性的独特的思维,以及由此凝成的具有特定意蕴的意象,没有把握诗人化用的典故,以致弄错了“灯”、“高山流水”、“身外之海”这些意象的真正含义,因此,他也就没有办法弄清楚诗中出现的一连串其他自然意象的更深层的内涵。
在阅读与接受中,误读者的思维与作者的思维之间的差异,是习惯性的传统思维与现代性的创造思维之间的差异。象征派、现代派诗人的思维,往往与潜意识的作用或者对隐曲的追求有关。思维巨大的跳跃性,心理活动的非连贯性,造成诗的意象和句子的间隔与空白。意象的模糊与多义性,乃是象征派、现代派诗重要的基础。何其芳所说的“追踪”作者的“想象”,实际上,就是追踪作者的思维运动过程。我们要追踪作者的思维运动过程,就必须把握住象征派、现代派诗人的隐性思维同他们创造的意象的独特内涵之间的联系。象征派、现代派诗中的意象有两类,一种是经过改造的传统的意象,一种是自创的意象。我们一般人接受习惯性思维的训练较多,比较容易接近和了解一般的传统的意象,对于诗人赋予新的内蕴的传统性意象,已经觉得陌生,如前面提到的“高山流水”;更不容易接近和解读的是诗人自创性的意象。这是因为,传统的意象,是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它们离人们的想象比较近,很容易唤起接受者固有的记忆,想象与想象之间的“桥”,呈现的是最近的距离。相反,现代派诗人们精心改造过并给予全新内涵的传统性意象,和他们最具个性特征的自创性的意象,往往都表现出思维的极大超常性。这种思维创造所凝成的意象和诗句,因此也就有了别人所难以接近或进入的特征。倘不能进入他们的思维轨道,不按照他们的“诗的思维术”,经过一番苦苦思索,也就不能“破译”那些用普通的或扭曲的语言、日常的或神秘的物象所构成的诗的独特“编码”。
不具备这种思维特征,又没有经过反复的思索,贸然进入象征派、现代派的作品,由此而产生的误读现象,有时往往会弄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杰出的女诗人郑敏的一首杰出的诗,就遭遇过这样的不幸。这是她的《心象组诗》中的一首,题目是《渴望:一只雄狮》。全诗是:
在我的身体里有一张张得大大的嘴
它像一只在吼叫的雄狮
它冲到大江的桥头
看着桥下的湍流
那静静滑过桥洞的轮船
它听见时代在吼叫
好像森林里象在吼叫
它回头看着我
又走回我身体的笼子里
那狮子的金毛像日光
那象的吼声像鼓鸣
开花样的活力回到我的体内
狮子带我去桥头
那里,我去赴一个约会
诗人于40年代开始富于现代意识的创作,成为著名的“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之一。1949年以后,这个流派的诗受到不公正的评骘。诗人郑敏的创作才华与激情,也被迫处于压抑的沉默之中。进入“新时期”之后,她的创作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被压抑已久的创作冲动,一旦获得自由,便与奔腾不息的生活湍流契合,进入昂扬的创造高潮。体内的“雄狮”,是被压抑的生命或创作激情与冲动的象征。“桥头”下的湍流和其他景象,是自然,是时代生活及其呼唤的暗示。重新“回到”体内的“开花样的活力”,象征了新的生命活力和创作激情。“那里,我去赴一个约会”,讲的是内心被压抑的生命感、自由感、创作的激情同自然,同生活的契合,带给自己个性和创作生命以新的天地。按照象征派、现代派诗人的思维特点和他们的意象系统和构成方式,进行思考,不难正确地进入这首诗的艺术世界。
但是,有的鉴赏者,完全违背这一类诗作的思维运动和意象构成的复杂性、隐曲性的特点,而是以习惯的思维来进行理解和鉴赏,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解释的“误区”。在一本《中外爱情诗鉴赏辞典》里,就把这首诗收入爱情诗之中,而且竟出现这样的“鉴赏”和理解:“‘渴望’是指爱的渴望,渴望异性之爱的情欲。诗人说它像一只雄狮,一只困在笼中的雄狮;它的冲动勃发,正如雄狮临江——在澎湃急流的感发下,亟欲奔腾、振鬣长啸。但狮子‘又走回我身体的笼子里’,情欲被压制住了。”鉴赏者进一步发挥说:“‘笼子’是人的理性、观念。几千年来,封建主义压制人性,视情欲为污秽不洁之物,更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戒条。‘我’体内的雄狮正是被这些陈腐观念束缚、囚禁着。然而,毕竟是20世纪80年代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也响起了不可遏止的人的解放的鼓鸣。雄狮在咆哮,时代在吼叫,内外呼应,‘我’终于冲破牢笼,满足‘雄狮’的要求:‘去赴一个约会’”。后面还有一些更为可笑的发挥性的理解,恕不引用了。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解释与鉴赏,不是在刻意展示别人的错误,以显出自己的高明。我是想从这一不算少数的现象中探讨一下,“误读”是由哪里开始产生的?说得简单一点,还是没有遵循现代诗人的“诗的思维术”的轨道,而以一般人习惯性的思维进行思考的结果。据我的推测,这首诗的鉴赏者“误读”的起点,在于没有理解诗人“那里,我去赴一个约会”这句话的特殊含义。由字典意义上的“约会”二字,自然地想到“爱情”,有了“爱情”诗的印象,以后就又由“雄狮”想到性的“渴望”。顺流而下,按着习惯思维滑动,结果是南辕北辙。其实,在象征派、现代派诗人的思维进程中,不遵守常规性的语义和语法逻辑,进行拆毁或“错位”的运用,这是常有的现象。他们偏偏绕开一般人的思维轨道,给日常见到的意象、日常应用的词语,以一种新的象征的含义。被压抑的生命力和创作激情与大自然、与奔腾不息的生活的“契合”,诗人用“约会”来传达或暗示,就造成了按常规思维来想象的人理解的屏障。这一点朦胧,这一点“错位”,是诗人的权利。从“错位”造成的朦胧进入诗人的正确含义,是接受者的义务和快乐。鉴赏者把赴“约会”理解错了,下面一连串的分析与鉴赏,也就随之而错了。偏离现代派诗人的思维,不能进行接受者与创造者之间思维的“接轨”,对于现代诗的阅读和鉴赏,会产生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结果。
30年代中期,现代派诗人金克木就指出,用理解散文的思维无法理解现代诗。他说:“几乎所有情绪微妙思想深刻的诗都不可懂,因为既然不用散文的铺排说明而用艺术的诗的表现,就根本拒绝了散文的教师式的讲解。”这里的“艺术的诗的表现”,不妨理解为现代诗人的诗的思维;而“散文的教师式的讲解”,就是违背了这种“诗的思维术”的习惯思维的理解。进入思维的独特性才能进入象征派、现代派诗的解读和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