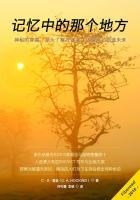上午,医科大学组织低年级学生参观了城外的艾滋病医院,晚上两人约会时,伊尹还沉津在强烈的情绪波动中。这些病人太可怜了!一个40岁的男子,已是晚期病人,身上到处是溃烂的肉瘤,惨不忍睹。他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是一遍一遍地念叨着:他不幸生在艾滋病肆虐的时代,所以一向洁身自好,从来没有婚外性关系,没有输过血,没有使用过不洁针头。唯一可能传染上艾滋病的经历,是一次去理发店修面时,被剃刀划了一道浅浅的血痕。另一个病人是个5岁的女孩,经母婴垂直感染途径得病,母亲已经死了。她正在非常投入地和布娃娃玩,轻声轻语地安慰布娃娃:好好吃药,让我给你打针,医生伯伯说,你不会死的……
科学家太无能了!伊尹愤愤地说。研究了40年,还是没找到真正有效的艾滋病疫苗。现在,最好的治疗也只能延缓病人的死亡!在伊尹的激情倾诉中,宇文平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那年他23岁,正在读硕士,专攻基因治疗技术。他的络腮胡子已经十分旺盛,那天刚刮过,腮帮周围泛着青光。这时他突然截断伊尹的话头:
愣了一会儿,伊尹才理会到他的话意:虽然早已听惯男友的,伊尹还是十分气愤。她高声嚷道:
宇文平讥讽地说,伊尹哑口无言,停了一会儿,她不服气地说:宇文平笑而不答,伊尹胜利地喊:
宇文平平静地说:
伊尹也在认真思考宇文平的话,她担心地说:
他突然卡住了,就像是机器人突然断电,两眼呆愣愣地望着远处,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他以这个雕塑般的姿势僵立了10分钟,20分钟。伊尹对他的这种已经见惯不惊,知道他又迸发了某种灵感,便耐心地等下去。但今天他的时间未免太长了,半个小时后,他的眼珠还死死地固定在原处,甚至连眼皮都没有眨动。伊尹有些担心,忍不住轻轻摸摸他的脸颊。这一摸才解除了魔法,宇文平忽然把伊尹抱起来,在宿舍里转着圈狂喊着:
他抱着比自己高的伊尹,就像蚂蚁举着一个大豆荚,不过举得毫不费力。伊尹喜洋洋地捶着他的背:
伊尹问我,我尴尬地摇摇头。
她指指我们下面的巨大容器。我追不上她的思路,困难地揣摸着:
我听懂了。虽然我是半个科盲,但这回我完全听懂了。我感觉到一道强光突然射进我的心灵,心中如海涛般轰响。我感到晕眩,感到颤栗,我敬畏地看着下面那个巨大的未来世界,想象着数万亿个在这里(替我们)同病毒搏斗、变异、生生死死,最后锻冶出宝剑——天哪,这太神妙了!
伊尹接着说:
伊尹把宇文平推到自己屋里,关上房门,把拖鞋放到面前,以命令的口吻说:
宇文平满目血丝,络腮胡子至少两个月没刮了,衣服也发出汗酸味。他很不情愿,不过无法抵抗伊尹的柔情。伊尹把他按到桌边,端出早已备好的饭菜。她着急地嚷,宇文平无奈地收回思绪,狼吞虎咽地吃着饭,心不在焉地夸了伊尹的手艺。饭毕,伊尹又端来一杯热腾腾的绿茶。等伊尹在厨房忙完,宇文平难为情地说:
伊尹真急眼了:她耐心地开导着,宇文平很感激女友的真情,尽管不乐意,但再也不提离去的话了。伊尹逼他洗澡,刮胡子,裹上一件雪白的睡衣,拾掇得像个擦洗一新的小瓷人。整个晚上,他陪着伊尹漫天漫地地闲聊。不过他的话头会突然中断,他的眼光越过怀中的女友看着远处,然后在伊尹的连声斥责下,他才收回心思。
晚上10点,宇文平探询地看看女友:我可以走了吗?伊尹站起来,不声不响在拉上窗帘,散开头发,一件件脱去衣服,换上浴衣。
宇文平困难地说:
伊尹生气地抢白他:
宇文平叹口气,脱下睡衣,拉着女友躺到床上,变回到那个激情如火的XYY型男人。那晚他们度过缱绻的一夜。云雨过后,身心俱泰,伊尹把小个子的爱人搂在臂弯里说:
宇文平闭着眼,抚摸着她的后背,漫应道:好的好的,结婚,结婚——忽然他的抚摸停止了。他睁大眼睛,猛然坐起来,瞪着窗外的星空。伊尹伤心地发现,这个男人的灵魂又出窍了。她当然很扫兴,但她知道男友的脾性,在这种灵感迸发的时刻,切莫去打搅他。十几秒后,宇文平几乎是沉痛地喊道:
他跳下床,赤身裸体地冲出屋门。在伊尹的连声呼唤中,他才折回来,匆匆穿上衣服。
他总算还记得与情人吻别,然后匆匆带上门走了。那晚伊尹没再合眼,她赤着身子站在窗前,久久地沉思着,猜想着男友从她这儿得到了什么灵感。她凭直觉预感到了男友的成功,但也看到了婚姻之途上的不祥之兆。直到天光放亮后,她才沉重地叹息一声,回到床上。
我急急地追问着。说来也怪,在这儿,伊尹和我都跳出了世俗感情的圈子。伊尹坦率地讲述了她和宇文平的关系,我也没有因此而激起什么感情上的涟漪。现在,宇文平的成败成了我们之间最强的引力场。
伊尹平静地说:她耐心地解释道,我忍不住打断她,我笑着说,我皱着眉头思索着,总觉得这里有什么细节不对劲。噢,对了,性别!我问伊尹,伊尹专注地看看我:
她的夸奖使我颇为得意,我藏起自矜之色,追问道:
我随着她的叙述爬山越岭,最后痛痛快快地吁了一口气:我不解地追问,我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
伊尹轻轻叹息着:
我嚷道,伊尹沉默了很久,决然说:
我恐怕自己听错了:
伊尹没有多加解释,简单地说:
我随着伊尹走出大厅,向旁边一幢浅黄色的建筑走去。进去后,所有遇上的人都尊敬地同伊尹打招呼。我们又遇见了那位最先见到的中年人,他姓金,是宇文平的高级助手。他和伊尹低声交谈着:然后他们都退回房内,走廊里只剩下我们两人。
我们走近一座大厅——我的心猛然缩紧了。没错,的确是囚禁。大厅的所有门窗都安上坚固的铁门,并且全部焊死,没留一个出口!无疑,这是最残酷的永久囚禁。在一个鸟语花香的研究所里突然见到这样的监牢,使人觉得格外阴森恐怖。这儿唯一与监狱不同的是没有守卫,一辆满装饭菜的小车悄无声息地开到牢墙边,一个小门自动打开,小车开进去后,小门又自动关闭。
然后是模糊的咆哮声和碗盏摔在地上的声音。
想到最著名的科学英雄竟然被囚禁在这里,我觉得浑身发冷。我想这里一定有最可怕的阴谋,最黑暗的内幕,连伊尹……我不愿怀疑她,但从她在这儿的地位看,我已经不敢保证她的清白。伊尹看看我,没有多作解释,掏出手机打开。当手机屏幕变亮时,一个贴在墙上的超薄型屏幕也显出图像。
没错,是他,当然是他。一个身高不超过1.5米的小个子,满脸是茂密的大胡子。他正在歇斯底里地蹦跳着,咆哮着,把碗盏、运食物小车、乃至旁边的椅子都一个个拎起来朝地上摔。不过显然这些东西都是特制的,一个个在地上弹跳着,没有被摔碎。屋里有一个方头方脑的小机器人,就像球场上的捡球员,不错眼珠地盯着主人,看到东西滚远了,马上把它捡回来。
伊尹肯定是见怪不惊了,她轻轻叹息一声,对着手机柔声说:
屏幕上,宇文平猛然回头,我看见一张狂怒的面孔,一双怒火熊熊的眼睛。随之屏幕被关闭,给外边留下一个难堪的冷场。不过,仅仅一分钟后,大屏幕再次亮了。我甚至惊诧得揉了揉眼睛——那个盛怒的、失态的宇文平已经消失,现在屏幕上是一张完全平静的面孔,嘴角挂着揶揄和浅嘲。他和伊尹就这么对视一会儿,随即转向我,用闪电似的目光把我全身刮一遍,我似乎能听到目光所及之处哧哧拉拉的电火花声。在他的威严中,我像是被定身法定住了,连话都说不出来。
所幸,我大概通过了他的审查,他以命令的口吻说:
否则怎么办,他没有说,只是咬牙切齿地做了个怪相。我这才想起自己来这儿的目的,忙嗫嚅着凑过去,想开始我的说客工作。但宇文平已不再正眼看我,对伊尹命令道:
屏幕暗了,把这个才华横溢的、带点歇斯底里的科学家撇到牢墙之后。我从他目光的魔力中醒过来,转向伊尹,怒声问:
伊尹收回了恍惚迷离的目光:她叹息道,我们坐在大楼旁的石凳上,初春的天气颇有凉意,背阴处还留着几片残雪,几株迎春花已绽开黄色的花朵。伊尹裹紧大衣,说,那是两年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