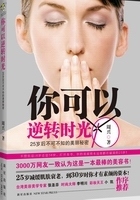病好之后,由于罗师长的升迁,黑寡妇失去了保护人,形势大变,急转直下。根本没人提起什么给他记特等功的事儿,这倒不打紧,戚勇想立功并不困难;更重的打击,是野战医院的政治协理员板着面孔通知他:“不要再回司令部去啦,你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了医院,出院以后,就到后勤去报到吧。”
“什么?这是为什么?”黑寡妇嚷起来。
“你自己还不明白吗?我看过你的组织介绍信,正在留党察看嘛!难道还不服从组织分配?继续犯错误?”
“明白啦!”黑寡妇是个痛快人,“卸磨杀驴,不新鲜。”
“我劝你少讲怪话!不要跟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老老实实地到后勤去工作。”
“谢谢!看起来你也是个好人。不过,为什么去后勤呢?我请求下连当兵。”
“因为野战医院就归后勤管。不要回战斗部队啦,这样也许对你有好处。”
“那,至少我也要回一趟司令部。我是侦察科长呀,总应该交待一下工作,取一下我自己的背包吧!”
协理员一笑:“背包已经送来了。你们师也离开了肃川野战机场……戚勇同志,你是聪明人——人家不欢迎你回去,何苦再去惹麻烦呢?”
黑寡妇点点头,不再言语。来到后勤部报到的时候,组织科的小干事当面拆开介绍信,指着这样一行字:“屡犯严重错误。战士待遇。”问他:“你岁数大啦,去担架连还是炊事班呢?唔,你会点儿什么技术吗?”
“会!我不但会开汽车,还会修汽车。”
“那好,汽车团正缺人哩,你赶快去吧。”
很快,黑寡妇便驾驶着苏制“嘎斯—51”型军用卡车往返于安东市与“三八线”之间。主要是送弹药、粮食、被服上火线;拉伤病员回祖国。有时候也空车回国去拉一些香烟、肥皂、烧酒、火柴、药品、记者、演员和祖国人民捐献的慰问袋来前线。
问题就出在放空车回国这个“机会”上。
在我家吃罢了晚饭,小白师傅和我的妻子女儿都坐到电视机前去看那牵肠挂肚的连续剧了,这边卧室里才清静下来,给我们两位老战友提供了一个随便谈心的场合。
黑寡妇确实喝多了,头重脚轻,歪倒在我的席梦思软床上。酒后吐真言,虽不连贯,舌头根儿也有点儿发硬,我还是听懂个大概。
“汽车团成份复杂。没办法,你也知道,抗美援朝主要靠汽车运输,所以国内就网罗了一批国民党时期的司机,特许他们参军,到朝鲜来开车……汽车有的是,斯大林把他二次世界大战用剩下的军车,大大方方卖给了咱们。是卖!不是支援咱中朝人民跟鬼子打仗。售价还真贵哩!他们多余的飞机大炮坦克车,全都高价卖给咱们,大大方方,后来逼着咱中国人拿猪肉鸡蛋对虾去还账,不是气得毛泽东都宣布不吃猪肉了么!这都是历史。咱老战友关着门说说,没关系。唉,从前我也说过,就被人家扣了个‘反苏’的大帽子,哈,那也是历史。中国人吃了老大哥的亏,还不准中国人说话,你要说,他就批斗你!他是谁?也是中国人嘛!为了给斯大林护短,中国人就死整中国人。我骂他是洋奴,他批我是右派。”
“老兄,跑题儿啦!还是说说汽车团吧。”
“对,那些国民党的司机呀,跟我差不多,我也在国民党的青年军干过几年嘛,我了解他们,吃喝嫖赌全来,好人不多……很难说我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倒不如说我这个人也很坏!”
究竟是怎么回子事哩?原来,当年朝鲜战场的运输任务实在繁忙,买几万辆苏式汽车并不难,配备这么多司机可就难了,所以出现了“歇人不歇马”、车多人少的局面。而那制空权也还处在互相争夺的状态。重点目标,比如野战机场、铁路大桥、坦克群和喀秋莎火箭炮集结地等等,敌机一来,我军的“银燕”必然奋起拦截,几乎天天都发生好几场空战;而一般地区的制空权,则仍然掌握在美国飞贼手中,他们重点爆炸的目标,就是交通运输线。究竟炸毁了我们多少汽车?我不知道。但是,朝鲜战争四年当中我军一共击落击伤敌机一万一千多架,这个数字倒是公布过的。
在北朝鲜开汽车也是非常危险的。白天要跟敌机兜圈了,捉迷藏;夜晚开车也得黑着灯。如果汽车中弹起火,司机能跳车就好样儿的,空手回来报告一声就行了,不会受指责,更无须追究毁车“事故”的原因。
为了减少伤亡,通常都是一人一车,不派助手或押车的。这就给那些“吃喝嫖赌”惯了的旧司机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确实干了不少坏事儿,”黑寡妇并不隐晦,更不害羞:“让我说句公道话吧,我们也确实玩命开车呀!支撑着一场反侵略战争。”小周,不,老周同志,你是作家了,你说说看,有没有这种逻辑:“坏人干好事儿?”
“有。”我笑着说,“不妨修正一下:坏人既干坏事儿,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干好事儿。”
“呸!太罗嗦。你们耍笔杆儿的就喜欢拐弯抹角儿,云山雾罩。依我看,倒是坏人创造历史,你敢同意吗?”
“不敢苟同。最好咱们取消‘好人’‘坏人’这个简单化的词儿……或者,把你所说的‘坏人’理解为打破常规的人;把你说的‘好人’理解为按照传统办事的人;那么,我就同意,是敢于打破常规的人创造历史!”
“哈哈,小鬼你越说越罗嗦啦!先听听我这个坏人都干了些什么坏事儿吧。”
他在放空车回国的途中,看着沿路有许多六轮和十轮朝天的破汽车,苏制美制的都有,扔在马路沟里,实在心疼!黑寡妇灵机一动,便停下车来拆卸轮胎。每次都拉一车轮胎回国。他坏就坏在不去交公,而是卖给了安东市内的私营汽车修配厂,大把大把的票子入了腰包。半年之后,他用这笔钱在鸭绿江边买下了一所日式小洋楼的两间房,以及成套家具。做什么用场?黑寡妇金屋藏姣了。
这位姣娘,便是米脂县的美人儿小胡。北朝鲜就那么大,黑寡妇又开着小嘎斯车到处跑,情人见面的机会终于来临。
“小胡,跟我走吧!”
在一次送文工队去野战医院慰问演出的途中,黑寡妇特意叫舞蹈演员小胡同志坐到驾驶棚里,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抚摸着她圆滚滚的大腿,动情的说着。
“那,我表哥非气死不可。”
“别忘了,你还有位表嫂呐!”
小美人儿最听不下这句话。差点儿没被这句话噎死!在黑寡妇的挑逗、怂恿之下,她终于走火入魔,“人约黄昏后”,坐着小嘎斯车开小差,住进了鸭绿江边的日式小洋楼。
从此,黑寡妇更积极了,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抢任务回一趟安东,沿途不但拆轮胎,就连破汽车上的发动机他也拆下来卖钱。1952年嘛,私营工商业尚未进行什么改造,做这种买卖方便得很。转眼之间,米脂县小美人儿的脖子、耳朵、手指、手腕儿全都戴上了黄灿灿的金器。
然而戚勇命运多蹇。就在这一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部队里只开展“三反”,比地方上少那“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两样儿;即使这样,黑寡妇还是和那些旧司机为伍,关进了候补“老虎”的防空洞里。
心里惦记着小胡,决心保卫小胡和她肚里的小小胡,黑寡妇这次作检讨极不痛快。“大不得了是一枪两眼儿吧!”他决心顽抗到底。任凭你挤牙膏、洗热水澡、政策攻心、车轮战术,他心中只有一句话: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边,白政委丢了表妹,断定是黑寡妇拐跑了,可又不好声张。此时趁着运动之机,通过组织“公报私仇”,要求“严办”戚勇的材料不断飞到汽车团——那些“挑土匪”、“砍匪头”、“吊女匪”等等鲜血淋漓的罪行全都写成了书面文字——即使你黑寡妇不交待新罪行,翻翻老账也够你受的!
无巧不成书。战争又一次帮了他的忙。就在黑寡妇接近呜呼哀哉的关键时刻,上级一道作战命令就把“三反”运动给停了。无论白政委的步兵师还是后勤部的汽车团,统统星夜上火线。黑寡妇和若干已经定性的“大老虎”再也不能使用了,只好派人押上汽车,连同他们的定案材料一同送回国去处理。
车过清川江大桥,黑寡妇无限感慨。再从肃川野战机场附近穿行,心中更加不是滋味儿。押送回国,交给一个什么军法处,面对着血淋淋的罪行材料,谁还承认我那些赫赫战功哩?想着想着,轰隆一声,天昏地暗,眼冒金星,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再醒来时,只看见一串串小火球——高射机枪的红色曳光弹划破夜空,好看极了!又躺了个把钟头,摸摸自己不缺胳膊不缺腿,鼻子耳朵鸡巴卵子样样齐全,这才试着爬起来,借着敌机投掷的照明弹——犹如悬在半空中的一串“孔明灯”,看清了押运自己的那辆囚车底盘朝天,一定是被敌机的火箭炮击中,油箱起火,把车厢板和六只轮胎都烧光了嘛。他趔趔趄趄,挣扎着跑过去,神经质地翻看囚车残骸,发现了几具黑炭般的尸体,根本无从分辨是司机、押送员、还是“大老虎”?他记不得车上一共有多少人,更数不清此处有几具尸体。也许有几只活着的“老虎”和自己一样,被甩出车厢之后就跑掉了。总之日他娘,飞机打汽车算个毬!家常便饭。
黑寡妇看着黑乎乎的囚车残骸,毫无凭吊之意,更无怀古之情。忽然心头一热,妙哇!“大老虎”都能烧成黑糊炭,我那档案袋连同罪行材料岂不早就化成纸灰、烟消云散了么!哈哈,果然是战争可以勾销一切。乃至焚尸扬灰。只剩下一片大地真干净!
他踉踉跄跄地走了。从此不见任何熟人,包括鸭绿江边小洋楼里那位米脂县的小美人儿。你放开嗓门儿哭吧!天天咒我吧,生了儿子不认我这个爹也行。反正我不该来见你——害你!
岁月飘忽,转眼三十多年过去。黑寡妇本性不改,所以当过“右派”,下过煤窑,淘过大粪,当过盲流,蹲过监狱,卖过冰棍儿,娶过老婆。老婆跑啦,“四人帮”也倒啦。
“我仍然相信乱世出英雄!”
喝了两杯酽茶,起到了醒酒汤的作用,黑寡妇从席梦思软床上坐直了腰,侃侃而谈。
“现在可不是乱世。是太平盛世!”我反驳道。
“没错儿!”黑寡妇不想抬杠,“从政治上说,还有国防力量,国际环境,都是太平盛世。政通人和。可是经济上就有点乱,我是说有空子可钻,只要敢干,坏人也能发大财。”
“你又说坏人!”
“没错儿,你问问去,那些倒爷有几个是没前科的?我们跑单帮,长途贩运,走私偷税,敢冒风险,为什么?为什么正经的工人、农民、干部、军人,还有你这路号的正派文化人就不敢?道理很简单: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本来就是不三不四的家伙嘛,百无禁忌。”
我也不愿意抬杠,“有一定道理。”
“从前好象有谁说过:每逢大变革的初期,总有一批勇敢分子打头阵,而这些勇敢的人,又往往带有破坏性。是有这个说法儿吧?小周,明告诉你,我黑寡妇就是这种勇敢分子。几十年的体会:勇敢就是护身符!”
我大感兴趣,“说说,愿闻其详!”
“什么详不详的!上个月我就当了一次被告,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小老太太硬是讹了我五万块钱。原因很简单,我的家电服务公司完完全全是私营企业,可是申请营业执照的时候为了保险,就找街道居委会当了个挂靠单位。后来他们见我赚了钱,就得了红眼病,告我不给他们分红……唉,我就忍痛让他咬了一口。”
“为什么让他?”
“因为我不是书呆子,让他咬一口,五万;如果不让,纠缠下去,工商财税部门认真一查,连白政委的老本儿也得没收充公!”
“白政委的老本儿?对啦,你和他,是怎么又搞到一起的呢?”我乘机追问一句。
“唉!”黑寡妇叹口气,“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还不是因为小胡——如今的白太太嘛。我老啦,总记着她可能给我生了个孩子。要是个儿子有多好!所以我就到处打听。后来有老战友透了口风,才知道小胡当年还是投入了她表哥的怀抱,52年就生了个胖小子——我肯定是我的!大家都在北京,我当天就找到白家去了。”
这是1984年的事情。当倒爷的戚勇来到了白家,并没把白政委气死,也没把白太太吓着,而是战友重逢,皆大欢喜。喜从何来?互相需要。白政委已离休多年,由于在“文革”中挨过残酷斗争,却斗懂了个什么人道主义,所以态度超然,超脱到了飘飘欲仙的境界,只关心气功,再也不计较与自己同属白毛老头老太的黑寡妇和白太太之间的什么旧情复发了。可喜的是大少爷已赴美国留学,学成之后干脆入了美国籍,娶了美国的洋媳妇,乐不思蜀,更不存在什么当面认亲爹之类的尴尬事啦。至于白太太,手中捏着几万元积蓄,正想找个可靠之人拿去做买卖,玉皇老儿就派来了黑寡妇这位倒爷兼老情人儿,绝对大胆的人精,又绝对可靠,那就让他拿去扩大再生产,鸡生蛋,蛋生鸡的倒腾一番吧。第三方是黑寡妇了,他实在是抗美战争中的英雄豪杰,如今儿子反倒成了美国鬼子,数典忘祖,夫复何言!罢罢罢,老首长和老情人既然信得过我,把一辈子的积蓄托付给我,当我的后台,我也就能利用他们的老关系,参加这可爱的关系网,摇身一变而变成官倒爷,又何乐而不为哩!
他的家电服务公司很快就发啦,三年过后,由一位数的万元户变成了三位数的万元户,我怎能不令街道居委会的小老太太患红眼病哩。特别是今年开始清查官倒爷了,所以让她咬一口,赶紧跟居委会“脱钩”,才是上策。
“黑寡妇!”我不客气地叫他的外号了:“这脱钩政策,难道指的是居委会吗?”
“书呆子!”他更不客气:“脱离了居委会,我就是个纯粹的私营企业了。哈,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脱钩呢?统计员做报表的时候,也可以把我列入脱钩企业的什么数字里去嘛。”
“可能,你跟白政委的关系网并没脱钩呀!”
黑寡妇笑了一下,那眼神有点儿狡黠。
是啊,这是一张无形的网,看不见,摸不着,你奈他何?一方面,白政委只打太极拳、打牌、打鱼,打台球,天天练气功,意守丹田,超然尘世,飘飘欲仙;一方面,“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处处袍泽,余威犹在,只消白太太出面就能办事。难道你还教他夫妻脱钩么?
“我只跟夫人挂钩。连她的老头子都不吃醋了,别人还怀疑我们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吗?”说罢,黑寡妇哈哈大笑起来。
隔壁屋里的电视连续剧暂告一段落,留下了个什么悬念便戛然打住,吊起胃口,请君再看下集。妻子和女儿忙着重新沏茶,白政委的小少爷却打个哈欠要走了。
“周小姐,你真是个懂行的主儿!”白少爷对我女儿说,“如果愿意,欢迎你到我们服务公司来当公共关系部的主任。”说着一笑,大大方方地把那70元工钱退还给她。
“就你们俩出来修冰箱,怎么还有个什么公共关系部呢?”
女儿提出了我也想问的问题。白少爷说出了黑寡妇不愿说的秘密。
“韬晦!戚叔叔和我上门修理冰箱电器,全是表面文章,做样子给人家看的。敝公司的实际业务是买卖家用电器,所以很需要你这样可靠的雇员——咱们算得上世交啦!干不干?月薪一千,半年分红。”
“干!”
女儿毫不犹豫,从她那硕士研究生的小嘴里迸出这么一个字儿来,就象黑七当年在湘西七里洞口下令儿说那个“挑”字一样干脆和可怕。
“不行!”我大吼一声,恨不能抽她两耳光。
女儿满不在乎,“怕什么?家家卖私酒,不犯是好手!”
黑寡妇笑了起来,“好样儿的!没想到周家的小姐到具有我黑寡妇的性格。来吧,我保证你这公关小姐的收入比作家高十倍。”
“周叔叔,你别怕,”白少爷竟然开导起我来了,“我爸爸活得跟神仙一样舒心。我妈妈也天天去跳舞——老年迪斯科舞蹈队,还上过电视哩。你就甭管我们小字辈儿的事儿了。人各有志,我们愿意跟戚叔叔学徒——勇敢就是护身符——玩的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
临走的时候,黑寡妇交待一句:“作家,可别把这些秘密写到小说里去,免得别人看了生气。”
他穿好汗渍累累的工装服,拎起油渍麻花的帆布工具袋,领着徒弟,像两位正派工人那样蹒跚着走了。只从背影儿望去,谁又能断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哩?
我将摆出一切革命的道理来,说服女儿不当公关小姐,远离那张发霉发臭的关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