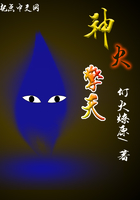胡适与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出场有点像凤姐在《红楼梦》中的出场,一样的先声夺人,当然也一样的光彩照人。
一九一九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年代,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渐入高潮。如同男女做爱,经过诱惑、接吻、抚摸、动情以后,热血沸腾,激情喷涌,最后攀上欢乐的巅峰。这样的比喻可能有点粗俗,但是意思没有错。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它是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大变革、大震荡、大决裂。
官方意义上的“五四运动”,只是在某个节点上一次特殊的行动。在后来中国式思维中,这场从思想到文化的伟大复兴被简化成为狭窄的爱国运动,甚至连科学与民主也丢掉,却单单将“五四运动”突出出来,提升为一场爱国运动。但是这一点不妨碍一九一九年在中国的摧枯拉朽,真正的摧枯拉朽,夹杂着电闪雷鸣,冲刷着积淀在中国大地上的封建尘埃。从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洞开六十年,庚子赔款让一大批学生奔赴海外留学,完全有别于东方专制的海洋文明让中国人目不暇接,目瞪口呆。国门既已打开,再也无法关闭,从太平洋上吹来的飓风呼啸而入,霉味扑鼻的中国老宅里飞沙走石风雨飘摇。这是从未有过的激情与碰撞,新文化运动便一呼百应,应运而生,干柴早已预备,只一点点火星它便马上烈焰腾空。已发生的一切肯定是水到渠成应运而生,一旦逆运,它便不可能发生,这是天地定律。
虽然后世对那场运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一代全新的人群已经在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中迅速成长,长成有思想有头脑的热血青年。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是偶然事件,但是历史就是由一连串的偶然演变而成,它之所以这样走而不是那样走,肯定不是偶然,偶然在这里就是历史的必然。
谁也没有想到,历史的重任会落在一个从徽州深山里走出来的清秀学生身上。那是一九一零年九月,二十岁的胡适抵达美国纽约,他是二期“庚款”留美生。对胡适来说,从上海到海上,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美国民主、自由之文化精神与古老国度的文明传统激烈碰撞,一代全新的民国文化人正在脱颖而出,他们将主宰未来中国的精神之舵,这其中就有他,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青衣书生。这是命中注定要发生的事。
一进入美国,胡适马上便成为美国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一切似乎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那一年正好是美国大选年,各政党的政治集会遍地开花,美国民众也积极参与,热情高涨。胡适全身心投入,佩戴一枚象征着支持老罗斯福的大角野牛襟章,兴奋得跑来跑去。在美国的几年,胡适脱胎换骨,他迫切想将这里先进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去,改变腐朽、没落的祖国。在他看来,只有打开国门兼收并蓄,这个民族才会强大,才会有全新的未来。大洋上的海风吹进了胡适有点迂腐的头脑,美国精神正一点一滴融进他的骨肉,中国走到了一个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民族传统的根基,现代文明的坐标,东西文化的激烈碰撞,造就了学者胡适。七年后,一代大师终于迎来了一个属于他的全新时代。
这一天应该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开始,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篇划时代的文字仿佛一枚重磅炸弹,让一潭死水般的中国顿时狂飙突起。也就在这一年的八月,胡适成为北京大学教授,一时万众瞩目,成为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这时候陈独秀趁热打铁,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高高举起了“文学革命论”的大旗。仿佛为他们的文学主张作注脚,鲁迅在翌年发表了不朽的巨著《狂人日记》,一把“大火”冲天而起,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熊熊燃烧起来。历史在这里翻开这全新的一页,这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历史选择了胡适、陈独秀乃至鲁迅,也是命中注定的选择。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就在于它的理所当然和独一无二。
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在当时是大势所趋,新文化运动的异军突起其实是有着漫长的思想铺垫——从根源上来说,新文化运动从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的洋务运动就已经开始,鸦片战争使中国被动地打开了国门。西风劲吹之后,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东西方存在的巨大差距,也清楚地知道中国落后在哪里。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人性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甚至可以说,落后就没有生存的理由,当然风靡一时的《天演论》佐证了这一点。一大批忧国忧民之士掀起了洋务运动,他们创办新式教育、新型企业,试图增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改变中国人长期被动的落后挨打的局面。经过近百年的漫长积累,洋务运动几兴几衰进展缓慢。要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形象,仅仅从实业层面改变成效低微,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必定要触及体制与文化——民国以后的思潮涌动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水到渠成,用胡适的话说,全都是被逼上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