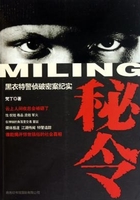“好!”宫神一点头正要坐回驾驶室,却被独孤凛手中的枪抵住了脑袋,“不错啊,连一个狼心狗肺的人都值得你舍身相护,慕容诗涵!”
听着他的话,宫神一恍然大悟,‘原来她是……’
容诗涵抬眸看了他一眼,伸手,一点点解着欧阳于谦的腰带,“女人,你做什么?”他再一次扣住了她的手腕!
动作被打断,容诗涵有些不悦,瞥了他一眼,昂了昂下巴,“褪下他的裤子!”丝毫不觉得指挥他有什么不对!
偏偏独孤凛还照做,甚至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
宫神一哪知道独孤凛的想法,此刻,某凛自然有他的花花肠子!
随即取出银针,看着独孤凛……
‘该死的女人!’独孤凛低咒一声,有些粗鲁的将欧阳于谦的衬衣拽开,砰、砰、砰……扣子飞溅!
看着欧阳于谦身上遍布的疤痕,还有那翻飞的皮肉,烫伤,子弹,还有……
容诗涵眼底一酸,‘不过一月不见,他……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
抬手,一根银针轻轻的扎了进去!
“嗯……”欧阳于谦吃痛,警觉的睁开眼睛,看着头顶惨白的小脸,条件反射的抬头,看向自己的左腿,“诗涵……我……”
“没事,不要紧的!”容诗涵轻轻一笑,“谦,有我在,不会有事的!”她低哞,手在银针上一滑,抬手,三根整齐的没入他的大腿!
独孤凛看了一眼,反手掏出手机,“是我,让霍瑞斯去慕仁医院等着,半个小时,找不到他,你们也不要回来了!”
“霍瑞斯?”容诗涵愣住了,‘那不是世界著名的骨科医生吗?他可是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最年轻的得主!而且他对神经受损也颇有研究!据说即便是十年的四肢无力,在他的治疗下,不出三个月便能跑跳自如!只是,他……怎么会认识?’
慕仁医院。
为欧阳于谦安排好一切,容诗涵终于暗暗松口气,‘真好,马上就可以……’看着从自己面前走过的男人,她忙拉住他的手腕,“你……”
独孤凛湛蓝色的眸子从她的脸上划过,慢慢的落在握在自己手腕的小手上,“有事?”
听着他毫无起伏的声音,独孤凛身子一僵,慢慢的松开了他,“对不起,我……我只是想知道,那位霍瑞斯医生要怎么联系?他什么时候有空?谦……我是说欧阳于谦……”
“我有说过他来是为了欧阳于谦吗?”‘他不远万里把那个人叫来,不过是因为眼前的这个女人!为什么,为什么她眼里只有那个男人,没有了他的存在,甚至……没有她自己!?’
听着他的说辞,容诗涵愣住了,“那他……可以告诉我他在哪里吗?我自己去找!”
独孤凛看着她,冷冷的吐出两个字,“让开!”抬脚,一步步朝着电梯口走去……
直到电梯门打开,他才缓缓的回头,“想知道他在哪儿,今晚去铜雀台,除了我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铜雀台那里可是最著名的情侣酒店,他……想做什么?’
轻轻的推开病房的门,看着站在窗前的身影,唇角微微一弯,“怎么起来了?”
“我怎么会在这儿?诗涵……你,你都知道了是吗?”欧阳于谦的声音有些颤抖,“诗涵……你会嫌弃我,厌弃我,甚至,远离我吗?”
容诗涵心底一酸,失控的环住他的腰际,“谦,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会有那么一天的!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的,我不管这一个月,你经历了什么,我都要谢谢你!谢谢你还肯活着,谢谢你!谢谢你没有再一次丢下我……和玥!
谦,答应我,不论为了什么,都不要再冒险,好吗?不论是你,还是玥,我都不希望你们有任何意外!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
欧阳于谦缓缓的转身,轻轻的拍着她的肩膀,“傻丫头,吓着你了吧?都是我不好!是我对不起你!”
“不,没有,没有!”容诗涵摇着小脑袋,“我是害怕,是怕你会像……会像以前一样,从我眼前消失,那样的痛苦,我无力再承受一次!你明白吗?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
“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仿佛发誓一般,欧阳于谦抱着她的右臂紧了紧,“再也不离开!绝不离开……”‘哪怕是日后你赶我走,也绝不离开!’
“来,病人呢,就要有病人的样子!谦……”轻轻的将他推到病床上,“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许下来!听见了吗?”
欧阳于谦眼底溢上一抹笑意,“是,小的遵命!小妹命令,谦断不敢违!”
嗔怒的砸了他一拳,拿起一旁的碘酒,转头恶狠狠的说道,“现在,脱衣服,在我没看够你之前,不许反抗!”
“是、是、是……”欧阳于谦懒懒的脱下衣服,“任你处置!这世上,也只有湮儿一人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诗涵,千万不要因为我是娇花而怜惜我哦!”
容诗涵唇角抽了抽,伸手将棉签按了下去!
“嗯……得,这就翻脸了是不?”欧阳于谦伸手,看似用力的捏了捏她的小脸,“你……恨过我吗?恨我那么决绝?恨我和玥……”
容诗涵指尖一颤,轻轻的为他擦拭着碘酒,“都过去了,还说这些做什么?”‘如果当初死的不是她,那么清扬恐怕也要葬身在那场车祸中!他又会不会,像自己一样幸运?所以,何必说这些?’
突然想起那个约定,转头看了眼窗外,犹豫了一下,仍是一点点为他擦拭完伤口,看着那个几乎横贯整合腰腹的刀口,她颤抖的擦拭完毕,终于忍不住,朝着外面奔去……
“慕容诗涵”
“照顾好他!”看了眼前的宫神一一眼,转身,极速朝着电梯奔去!
直到电梯的门合上,她才蹲在地上,将自己环在臂弯之中小声啜泣起来,‘清扬、清扬……你到底经历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天知道她多想了结,可她,她不敢问,不敢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