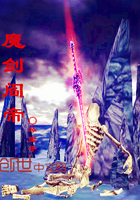“阿昭,你是在怪我?”
“弟子不敢,既然我醒了,还请师尊不要再对那些暗箭伤人者漠视不理了。师尊交代的事,我也会一一完成。”
“自然,本来也是给她一个教训。”
“师尊这几年锋芒更甚,一反常态,是否是时限已到?”
“百岁童颜也不能长久,殚精竭虑这许多年,只想最后尽些力。说到底,我也该休息了。”
师尊期许的目光落在颜昭身上,“有些事,我要从现在开始转交给你。”
“弟子明白。”
师尊的眼睛微咪,露出了相当餍足的表情,像是拥抱着一大捧阳光睡足的猫。
“我倒是好奇,你第一天醒过来不是嚷嚷着要见阿珣吗,怎么这几天转性了?”
其实刚醒的时候颜昭说话都不利索,硬拉着侍药的女婢撒娇,不惜赔上老脸。
“师尊别看阿珣平日不怎么出格,一旦放养,就容易做事出圈儿。她天资虽已是旁人无法企及,却不能囿于此。”
颜昭捋了捋气,往旁边的石头上倚了倚,稍作休息才继续道,“我该说的都在信上,我俩一同长大,也没什么不放心,就怕她心太野,放纵了自己。”
颜昭微微低头,冬日稀薄的阳光淡淡铺在他脸上度了一层金光,像白釉瓶上撒了层金粉,令人心驰神往。半晌,颜昭才喃喃道:“不让她知道,她才会记挂。才想得起,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阁,阁里有她的阿昭哥哥。”
“你自己的风流事没了阿珣给你遮挡,也不知道,能瞒得几时?也不知道,拂尘阁是中了什么邪,陆……上一辈也是这样。若是受了折辱,你是否能安排妥当?”
颜昭紧攥着手掌,指尖已经洇出了血痕。
“师尊不必担心,处处留情,本就是无情。”
阿昭撑了一会儿就往回走,还未恢复的身体有些摇摇晃晃,不时还往前踉跄。蓄灵室能修人内力,护人心脉但不能愈合皮肉之伤。那七十多道天雷横贯前胸后背,舒珣只受了几道就有些后患无穷的意思,何况是他,百倍之痛不止。
山下。
舒珣带着阿默在十八村落一一拜访,阿默出生在这,虽没待过几天却一直想来看看。
两人感受着初入人世欢喜和自在,还有村落里众人的热情与淳朴。哪怕是很多年之后回想起来,这段日子都算是天赐的礼物。它在舒珣对人世充满防备以致整夜无法安眠的时候像一座遮雨亭阁,能让她暂且放下心累的伪装,毫无顾忌地做事,救得了救不了都不会有人怪罪,张扬还是放肆都不会有人置喙。
最后,舒珣带着阿默来了陶阿婆家。
“陶阿婆,这是保暖的药,天寒难耐的时候就敷上一些。我把药方写下你让小孙子去附近的药堂取就是了。”
“舒阁主,这些年多亏你了。”陶婆婆脸上的皱纹聚到一起,慈祥地看着她。
“没事,忘忧阁在山下采药也多亏你们照拂。”舒珣还记得上次来时陶阿婆送她的辣椒,她和颜昭都不吃辣,颜昭更敏感一些,她还拿来戏弄他,想到这舒珣不由得灿然一笑又无奈地摇摇头。
“阿姐,是想起了什么吗?”
“一些过往的趣事罢了。”
“阿姐,不必担心。”
“嗯,我知道。”
“婆婆,我和阿默就先告辞了。”
他们不可能缱绻在一处,总要去触碰那些尖利的触角。
两人从陶婆婆家出时天上已经开始飘雪,下得并不大,昏黄的灯光晕染着多出几分回家的暖意。阴云包裹了天雪山山顶,零星的雪花粘在舒珣的发梢。白皙的小脸泛着微红,缩在白毛大氅里。
等雪将将停了,阿默才驾着马车载舒珣离开。
十八村落久居天雪山下,受忘忧阁庇护,算不得外界和外人。这一出村,舒珣才有一种“莫敢回头”的怅然。
舒珣靠在车壁上,手指恋恋不舍地从汤婆子里抽住来,从袖中拿出还未来得及拆开的信,小心翼翼地揭开,一封一纸千字的信看得人眼花。字体虽小却不凌乱,收放有力,盘虬卧龙,洋洋洒洒,带着行云流水的自如。
舒珣把纸放近鼻尖轻轻一嗅,是她熟悉的檀香。舒珣心道,果真是阿昭那个假公子干的出的真风流。
信上大致不过是他挂在口头天天念叨的下山须知,只不过他说话向来偏爱“之乎者也”的腔调,百十字能讲清的事非拖到上千,以致舒珣的读后感言只有无奈而心暖地摇头。她又伸进信封去取另一部分,是层层叠起的······地图
朱红在三七之境上圈出精确到店名的客栈,黑色的小楷在三大国七小国的版图上注了世家大族和各处隐藏的暗桩······不同的字迹在硕大的地图上写得密密麻麻,都是其他几位阁主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埋下的亲近,还有富可敌国的钱粮银两。
舒珣眼眶发酸再也控制不住涕泗横流恨不得现在就回去。她为人淡漠,外人看来多少有些自命清高,其他几阁平日尽量避着她。
如今,来送别的只有师尊一人。他们虽没来送她一程却也用另一种方式尽了心意。就连秦雪也似有若无地描了堪堪几笔,却把最大的据点托给了她。
外面天冷,在方被外搁置许久的手都有些冻僵,微冷的指尖泛着淡淡的血红,屈指都甚为艰难。
舒珣哭地稍稍狼狈,收好这些心意。刚想让外面的阿默找地方留宿,就听她急急停了车,不由得晃了晃身子。阿默探头进来,神色凝重。
“阿姐,前面有人受伤了,好像是·······箭伤!”
方才的伤感骤然散去,只觉得惊讶疑惑。他们走了半天已经早就望不见天雪山高大巍峨的身姿,连呼吸都少了清澈冷冽只有黄沙呛进鼻腔的不适。
天雪山在地图上一片空白,若论边界则位于李唐和北川的交界。因而政事迭起之际,星渊阁派人去这两大国的也最多。按脚程算此处已经入李唐境内。为箭所伤一来极小可能有猎户,一时失误伤到了人;二来就是战乱。
李唐向来以礼治国,看李朗就知道“翩翩浊世佳公子”才是风尚,民风断然没有北川人剽悍。而且······这人穿的好像是李唐的士兵打扮。舒珣并不是很了解,毕竟术业有专攻。
舒珣跳下车去看靠在树上满脸血污,昏迷不醒的人。那把箭离心脏偏了一寸,洇出的血颜色乌黑,箭头上淬了毒无疑。舒珣去探他的脉搏,虽然微弱但聊胜于无。
“哒哒哒!哒哒哒!”舒珣不了解情况好歹耳聪目明,附耳在地上就听见了整齐有序的马蹄,眼神一下子变得凌厉,示意阿默将人抬进马车里。
阿默年纪小但机智聪明肯用功,也算得上是骨骼清奇,天生神力。阿默把人隐进不远处的树丛就和舒珣一样躲在树上看戏。
果真,没过多久就有一队十人左右的的士兵整齐而迅速地停立。他们身上的衣着与车里那位极为相似,而面容却是极大的不同。眼窝深邃,鼻梁高挺身上染着的风尘是广袤凌冽的塞北大漠赐予的骄傲与荣光。
为首者,孤狼作战,至死方休。
是朔北铁骑,舒珣并不惊奇,但若只是为了一个李唐伤兵出动以一敌百的铁骑,未免大材小用。还是说·······马车里是什么重要的人物?
“大人,情报有误,那人不在这里。血已经凉透了,这里还有轻微的车轮印记。看来是中毒未深,被人救走了。”
“救走?苍郁殿下不是说那毒一击毙命吗?我们冒这么大风险,就是要确认那人死透了。”为首者皱着眉头,十分为难。
他们开口说的是北川话,舒珣听得磕磕绊绊,也能大致猜出些。这个伤兵是遭到刺杀,中毒后被人故意扔到这里的。
舒珣不禁冷笑,李唐军中大概有细作,但朔北军中的细作就在眼前。阿默把车辙匆匆作了掩饰,这人既然能看见车辙必定心细如发,又怎会注意不到车辙走向,一看便知那人藏在什么地方,何必遮掩说被人救走。那下马去看的人似乎察觉到什么略微抬了抬头,又自然地垂下去。
“这西北地旱,辙印不清晰,大致向东边驿站求救去了。”他又开口迷惑道。
“向东追,若是活着剜骨钻心,若是死了将尸体悬在缰绳上拖回。”
为首的将领十分信任下马查看的骑兵,立即带人向东去,舒珣远远望了一眼只觉得那人有些熟悉。
阿默翻身下去将马车推出来。舒珣去探那人气息,直叹其命大。一边解其衣带,一边取药。打开随身药囊取了几味止血药材敷上。又把珍藏许久的化毒丹拿了出来,在阿默羡慕到哀怨的注视下给他服了下去。
“阿默,你不会心疼了吧?”舒珣每每看到她这难以抉择的模样就想要调笑。
“阿姐,这化毒丹是留着急用的,一时半刻也很难练成。这个人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万一是坏人呢?”
“嗯,很有道理啊。”舒珣赞许地看了她一眼,小丫头考虑地不少啊“如果我没猜错这个人是李唐的将领,有北川人要置他于死地,那他于公必然有护卫李唐一方百姓的能力,于私必然对北川的某位殿下做过什么。最近比较乐见北川人吃瘪,救他一举两得。”舒珣狡黠的笑着,打着自己的算盘。舒珣取了几根银针插进伤口附近将毒逼了出来。舒珣看着几根发黑的银针,眉头紧蹙。
是无花。
曾经在南绍一带疯传的毒,让百艳之地寸草不生,人碰到也是见血封喉。舒珣好奇地打量枕在她腿上的人。
看起来不过是个大不了她几岁的少年,或许才及弱冠吧。皮肤白皙细腻,一点也不像被漫天黄沙摩挲过。擦去满脸血迹,才看清清秀的眉眼,有着少年人凌厉锐气和未退尽的青涩。上衣已经被扯开露出比脸上更单薄的颜色,接近心口的暗疤分外扎眼。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痕从那道疤蔓延,断断续续遍及整个胸膛。舒珣用指腹轻轻摩挲,凸起的脉络狰狞地像爬虫般紧紧蛰在这具近乎完美的身体上。残破的美感在舒珣心上悄悄划过。
“啧啧,这模样可以和颜昭比肩了。”舒珣不禁感叹,远在拂尘养生的某位在打喷嚏后默默加了件衣服。
“是身体里另一种毒阻止了‘无花’吗?你因它受了不少苦吧?没关系,这次就当你因祸得福,也当我被你美色所惑吧。”舒珣喃喃低语,似是被自己逗乐一般,浅笑了一声。平日的玉笛在内力变化下变成一把利刃,舒珣干脆将那道暗疤重新划开,皮开肉绽,一刀见骨。
舒珣吩咐阿默驾车去悦福客栈,便投入到解毒的过程。
不知行了多久,阿默掀开帘子时车里的血迹已经干涸了,阿姐脸颊贴在在那人胸膛上小憩,连日奔波确实累人。
窸窸窣窣的声音还是把浅眠中的舒珣惊醒了,她才意识到已经赶车赶了一天。阿默尽管年轻,也累的够呛。舒珣刚想下去,就看见那队铁骑拎着客栈老板的衣领将他扔到地上,在店里也是又摔又砸,不多时才愤愤离去。阿默将车停在街角,窥探着动静,见那人绝尘而去,舒珣才出去。
“阿默,你带人从后门进去,停好马车,将人扛进屋里躲着。”
“阿姐,这客栈不可信吗?这是阿姐自己选的啊。”阿默不解。
“那老板刚受威胁,江湖之人自保的那些不入流的手段,我之前略有耳闻,小心些总不会错。”舒珣这两日所见,就已经寒了一半心肺。两国交战对垒都光明正大,即使偷袭也无非出其不意将人一军。但下毒暗害,折辱对方,通敌叛国那就算不得磊落,一旦发现就是国耻。对军功胜利尚有此歪心何况是只求谋生的店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