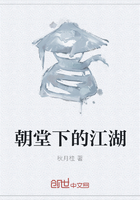二人一路奔袭抵达庐州境界,一路上也未曾好好休息,人困马乏,楚明风见已进入庐州,便道。
“这也跑了三天三夜,估计这马腿早已酸麻无力,如今天色已晚,还是先下马歇脚,再进庐州吧。”
白玉良见得胯下坐骑早已脚软若云,使不出半分气力,只是低下马头,“呼呼呼”的喘着粗气,自己也早就筋疲力尽,便道。
“也好,这太阳落了山,只怕庐州城也进不去了。我看前方有一片树林,不如去那里歇息一晚,等到天亮,再做打算。”
楚明风点了点头,二人翻身下马,向树林之中走去,夜黑若墨,月光微亮,树林又是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将本就暗淡的月光遮掩的严严实实,不禁透出几分阴森,二人进入树林,找了处参天大树,从马鞍取下干粮,白水,吃了些许,围坐在树下,倚着树干,抬头望去,竟依稀之中能望见隐隐月光。二人奔波劳累,早已是困倦难当,如今天气闷热,又起了阵阵微风,更是令人睡意大发,白玉良道。
“三弟,你先睡下,我再忍一忍,等过了两个时辰换你守着。”
楚明风此时早已熟睡下去,除了微微鼾声,听不得半点声响,白玉良不由得暗自发笑,起身活动筋骨,见得前方林道有一黑影闪过,速度极快,眨眼功夫便消失不见,白玉良连忙揉眼,定睛细看,一手手握住剑鞘,一手握住剑柄,顿时睡意全无,眼前林道却是空无一人,白玉良暗道:难不成是整日奔波,出了幻觉。遂即,又抬起头来,观望四周,见得四周寂静如常,林头鸟雀也未见惊走之状,暗道:定是我连日奔波,过于劳累,若这林中当真有人,怎不见鸟雀惊走。
遂即,又回到原处,白玉良戒心刚消不久。只听得四周风声四起,白玉良连忙将楚明风叫醒,楚明风睡眼朦胧,揉了揉眼,只见得四周树枝摇摆不定,二人背背相靠,环顾四周,只闻风声,未见人影,楚明风低声道。
“看这架势,这树林之中至少也要有十个人。”
那树林之中可谓伸手不见五指,二人定睛凝神,也只隐约见得树枝摇晃。倏然,从那树上传来一阵浓烈风声,白玉良抬头望去,只见一道银光落下,宛如闪电一般,那银光直奔二人头顶而来,二人连忙分开闪避,待到银光落地之时,只见一柄明晃晃的长刀将土地劈出一道裂缝,二人见状,不由得从额上流下几颗汗珠。二人惊魂未定,又听得身后风声骤急,二人连连躲避,只见身后又多出两柄明晃晃的利刃,那两柄利刃转刺为砍,分别向二人腰间砍去,变招之快,不禁令人冷汗直流。白楚二人连忙格挡,前者拔剑格挡,剑未出鞘,便已被长刀震出数步之外,刀剑相触之时,白玉良只觉得右手酸麻,虎口传来钻心疼痛,暗道:这人气力好大。与此同时,楚明风抽出纸扇,纸扇本就便于使用,楚明风便将纸扇打开,已扇身格挡,又闪身而去,纸扇小,只得贴身取胜,楚明风双脚交替点地,转动身躯,向前移去,又暗自运功蓄力,对准刀柄之后,打出一掌,这临近之时,楚明风方才见到这持刀之人身着黑衣,头戴斗笠,面遮黑巾,看不清长相,却看得出是一副番邦人的打扮,那人也打出一掌,两掌相对,楚明风竟沾不得一丝便宜。二人对掌之时,楚明风只听得头上似有声响,仰头一看,不由得惊得魂不附体,只见从树上极速落下一白光,那白光正是长刀刀尖,刀尖直奔楚明风头顶百会刺去,楚明风连忙撤掌,向后退去,待到站定之时,楚明风道。
“二哥,你没事吧。”
白玉良正要答话,只觉身旁似有二人从东西方向分别疾驰而来,转眼之间,二人脚步声愈加急促,已是近在咫尺,只见得两柄明晃晃的刀刃分别刺向白玉良前胸后背,白玉良连忙抽出佩剑,左脚点地,借力跃起,手握佩剑,环绕一周,才将那两柄利刃格挡开来,白玉良道。
“没事。”
话音未落,只听得上头风声又起,似有暗器打来,白玉良连忙闪身向后跃去,还未着地,那两柄利刃又分别刺来,直取白玉良腰身,白玉良见状,一招本门剑法“月笼长江”,持剑点地,又倏然发力,滑砍而去,白玉良此时武功半废,能使出这等武艺已是万难,只得将那两柄利刃格挡开来,却也无力反击,站定后,已是浑身无力,单膝跪地,故作呼吸稳定。白楚二人相互靠近,却被林中黑衣人围住,两活人面面相觑,相互试探,却也谁没先动手。
楚明风道。
“这群人好生厉害,只怕你我难以取胜。”
白玉良低声道。
“我将马匹解在了那棵大树东面五十步,你我以进为退,尽快脱身。”
楚明风也没答话,点了点头,二人一齐冲向前方,与那黑衣人战到一起,二人身着白衣,在黑夜之中与黑衣人形成鲜明对比,宛如黑泥之中绽放的两朵白莲。
二人拼死突出重围,翻身上马,黑衣人在后紧追不舍,黑衣人轻功卓绝,又长于夜战,二人本就身着白衣,在黑夜之中甚是显眼。二人策马疾驰,白玉良时不时回头望去,见得与黑衣人距离渐行渐远,遂即长呼一口气,二人并不知对方几人,只听得身后“嗖”的一声,宛如撕裂长空一般,黑夜之中难以识物,也不知打来的是什么物件。白玉良连忙挥剑格挡,却不想听得楚明风闷哼一声,遂即伏在马背之上,不再做声。
白玉良见状,连忙握紧缰绳,向后勒去,胯下马匹一声嘶鸣,划破寂静黑夜,白玉良回头望去,见得黑衣人并未追上,这才送了一口气,一把拽住楚明风马匹的缰绳,勒住马头,又看向伏在马背上的楚明风,借助微弱月光,白玉良只见得楚明风白色衣衫已被染红,白玉良连忙贴在楚明风身旁,见得楚明风还有微弱呼吸,面色惨白,额上豆大汗珠不住流下,心道: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可如何是好?便道。
“三弟,三弟,你撑住,我带你进城,我带你进城。”
说罢,将楚明风放到自己的马背之上,向庐州城疾驰而去。这马匹本就疲惫不堪,如今又承载二人,速度自是满了下来,那身后黑衣人未过多久便追身赶上。白玉良道。
“这群人什么来头,好生厉害。”
月亮从云层中探出头来,照在大地之上,白玉良这才发现,那身后追赶之人,共有八人,且个个儿身着黑衣,头戴斗笠,手持长刀,步伐轻盈。白玉良不由得想到方才在树林中与几人交手的经历,几人配合默契,且个个儿武功不弱,不禁令人冷汗直流。
那马匹越走越慢,最后竟瘫倒在地,口吐白沫,白玉良见状,心道:天王我也。
那黑衣人也赶了上来,一齐抽出长刀,向二人砍来,白玉良连忙提剑格挡,使出最后一丝力气,与八人战了片刻,便被八人逼到一棵槐树之下,那八人面面相觑,说着白玉良听不懂的话,白玉良道。
“原来你们不是中原人。”
八人听罢,一齐抬刀砍向白玉良,电光火石之间,千钧一发之时,只见得白玉良身后打来数颗石子,那石子不偏不倚的正打在八人持刀的手腕处,八人手腕传来一阵剧痛,手中长刀不由得掉落在地,八人一齐发出哀嚎,皆是左手握住右手手腕,在地上打滚,白玉良回头望去,只见槐树后站着一人,那人背对月亮而站,看不清长相,白玉良道。
“多谢前辈相救。”
那人也没答话,气入丹田,缓缓流出,说道。
“尔等杀才,不知死活,敢在老夫的地界上肆意杀戮,老夫曾发愿起誓,今生不再杀人,你们快滚,不要让老夫在这片林子里见到你们,不然定会打你们一个筋骨尽断。”
白玉良听罢,只觉这人说话内力身后无比,直达听者心腹,若是这人将内力由声传出,若非内力深厚之人,定会伤及脏腑。
那八人听罢,虽说不知含义,但心中自知不敌眼前这人,只得站在身来,相互搀扶着,仓皇逃去。
白玉良回头再看,那男子竟是一招“移形换位”闪到二人面前,将楚明风背起,冷道。
“你这朋友怕是不成了,老夫先将他带走。”
说罢,将楚明风背在身上,一跃而起,左脚点在槐树树枝,右脚又寻另一树枝,这一身高明轻功,二人重量,双脚交替点在树枝之上,树枝竟如枝上无物一般,丝毫不动,白玉良见得这男人身法,似曾相识,似乎在哪里见到过,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白玉良道。
“前辈,晚辈去哪里找您啊?”
那男人话音悠长,正是一招“隔空传音”的法门,本已离开数百步,声音却传了回来:林外延河数里有一茅屋,你去那里就成了。这隔空传音的功夫若非内力极为深厚,是万万使不出的。
白玉良听罢,连忙跟了上去,一路施展轻功,快步跑向树林另一端,但也见不到那男人的身影,直到拂晓,白玉良才听得不远处似有潺潺水声,便加紧步子,向水声处奔去,见得林前溪流,又延溪而下,走了几里路,才见得眼前茅屋,一股子草药香气传来,白玉良这才放下心来,加之此时早已是气喘吁吁,四肢无力,便倚坐在一棵槐树之下,只听得屋内那男人又道。
“臭小子,你这轻功是哪个狗屁师父教的?还不如乌龟爬的快。就走这几里路,好像丢了半条命似的。”
白玉良听罢,正要发作,他平生最恨别人辱骂自己师父,但却转念一想,这男人听力当真厉害,我还未进茅屋,他便知道我的位置。
那男人又道。
“在外面懒够了,院子里还有些剩菜剩饭,你爱吃不吃。”
白玉良听罢,扶着一旁树干起身,向茅屋走去,见得院子里的一个破木桌上果然有半锅稀粥,两个馒头,还有些小菜,白玉良正要拿起馒头,那男人又道。
“吃完饭,想着把碗洗了。”
白玉良点了点头,正要拿起馒头往嘴里塞时,那男人又道。
“前辈和你说话,你怎么装作听不到?”
白玉良这才说道。
“晚辈实在是累到说不出话了,请前辈恕罪。”
那男人笑道。
“快些吃饭吧,不逗你了。”
说罢,从茅屋里走了出来,白玉良这才见得这男子体态消瘦,约摸着五六十岁的样子,面黄如蜡,看着样子不像是一个健康的人,那男人道。
“老夫且来问你,你们是怎么招惹这些倭人的?”
白玉良道。
“前辈如何知道他们是倭人的?”
那男子从袖口中取出两枚铜制的四刃镖,道。
“看到这个,还能不知道这是倭人吗?老夫年轻时曾收过一个倭人徒儿,那倭人说倭国地狭民穷,铁矿稀少,不比中原,只有以次充好,用这铜替代铁做些暗器。”
白玉良听罢,又道。
“前辈,我那朋友?”
白玉良欲言又止,男人笑道。
“他是你什么人?看你二人长相也不像是孪生兄弟。”
白玉良道。
“他是我结拜义弟,义同生死。”
那男人听罢,竟仰天大笑一阵,又轻蔑道。
“什么结拜兄弟?真是可笑,嘴上的言语兄弟罢了,难不成屋里那小子若真一命呜呼,你还真能与他共死不成?”
白玉良见得这男人脾气古怪,喜怒无常,便道。
“若是三弟当真不幸亡命,晚辈断然不会独活,不过死前,晚辈定当杀光那群倭人。”
男人冷哼了一声,回头走进屋内,推门之时,低声说道。
“他没事,静养几天就好了,那四刃镖有毒,好在那小子中毒不深,如今已无大碍。”
说罢,走进屋内。白玉良心道:这人真是奇怪,喜怒无常的,还是不要冲撞了他,只是这男人一身的神秘,那轻功身法,总觉得似曾相识,却又记不大清。
白玉良发呆之时,那男人推开门,扔出一大木桶,道。
“小子,半个时辰之后,你去溪边打来几桶清水,把这木桶装满,你那兄弟体内还有些毒气,若不逼出来,只怕一身的武功,是注定要废了。”
白玉良连忙应下,拿起那大木桶向河边跑去,那木桶足有半人高,磨盘粗细,那男人道。
“你就是在溪边把水装满了,你也拿不回来的,这木桶装满水,足有百八十斤重,看你的样子,只怕也是有伤在身,莫要逞强。”
白玉良听罢,见得院内有一扁担,两只小桶,便折了回去,拿起扁担和木桶,扛在肩上,向溪边跑去。
这来来回回折腾了三五次,才将那大木桶装满,男人又道。
“傻小子,我要热水。”
白玉良木讷的答应着,又将大木桶里的水腾到大锅里,烧开之后,搬到屋内,见得楚明风躺在床上,脸上有了几分血色,表情也没像昨晚那般痛苦,心上巨石也悄然落下,又见那桌上放有一本《道德经》,那《道德经》封面碎烂,边角卷起半寸有余,想必被人翻了不下千遍万遍,便回过头打量着那男人,暗自嘀咕道:这人也不像道士,怎么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男人道。
“傻小子,老夫运功逼毒之时,你要不停的加热水,不要让外人打扰老夫,不然你这兄弟只怕性命不保。”
白玉良连连应下,二人将楚明风衣衫脱下,搀到木盆之中,那背上伤口以由黑转红,显然那四刃镖的毒性已被排出大半,但也有些肿胀。白玉良赶忙拎起木桶,不停的加入温水,那男人见捅中温水足有两尺之高,便摆了摆手,示意白玉良停止加水。白玉良授意后,将木桶放到一旁,两只手搭在木桶边沿,探头看去,男人道。
“老夫为你这兄弟疗伤之时,你切不可多言。”
说罢,也不等白玉良回答,盘膝坐在楚明风身后,蓄气运功,变掌为指,封住楚明风周身要穴,楚明风就如已死一般,面无表情,不动如山。白玉良在一旁见状,不由得担忧,但又不得出言相问,心道:昨夜见得这人内力颇深,定不是寻常之人,想必有些手段。
那男人封住楚明风周身要穴后,移步在前,盘膝而坐,双掌发力,推在楚明风胸前,内力由男人双掌传入楚明风身体,只听“咕噜咕噜”桶内温水竟冒出水泡,宛如沸腾一般,白玉良探指试温,桶内温水虽说冒起大泡,但水温依旧如常,又过半壶茶的功夫,只见楚明风额上汗如泉涌,豆大汗珠纷纷落下,桶内温水也愈见混浊,最后如浓墨一般,楚明风见状不由得大骇,连忙挪到楚明风身后,见得伤口也不断渗出黑色血液,此时楚明风神志已逐渐清醒,慢慢睁开双眼,见得眼前男人也是汗如雨下,正要开口说话,却不想那男人竟将自己哑穴封住,只得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男人见楚明风已醒,又见桶内温水已如浓墨,连忙收功撤掌,长出一口气,擦拭额上汗珠,解开楚明风周身要穴,便道。
“这便无碍了。”
说罢,起身走向床头,盘膝而坐,依两仪幻虚功恢复内力,楚明风见状,心道:这人如何会道家上乘的内功心法?
白玉良见那男人练气打坐,也没再多说,将楚明风搀到另一张床上,轻声道。
“三弟,你且好生歇息。”
楚明风点了点头,见白玉良走出房间,回过头看向男人,见得男人竟练得出完整的两仪幻虚功的练气法门,更是吃惊,他自是明白,这两仪幻虚功乃是道家不传之秘,世上会此功法的也只有师父,师伯二人,就像李一逍,杜万遥二位师叔,也只懂些皮毛,这人是如何练成的此等上乘功法。
那男人一边打坐练气,一边嘴里轻声念着两仪幻虚功的心法。
“天地初开之时,阴阳初动之机,原气沿督脉下行,后功沿仁脉贯穿,由外向内旋为聚,自内向外旋为散,和合四相,伴生两仪,要穴移位,身轻若飞……”
楚明风听罢,更是大惊不已,瞪大了眼,暗道:这男人到底什么来头?怎么将这内功心法背的一字不差?
未过多久,那男人便恢复到七七八八,呼吸畅快,缓缓睁开双眼,走到楚明风身前,看着楚明风,道。
“小子,你可是徐一星门下之人?”
楚明风道。
“前辈如何知晓?”
男人冷哼一声,道。
“难不成老夫这半辈子还识不出纯阳道阳的内功,若知道你是徐一星的徒弟,老夫绝不会救你。”
说罢,拂袖而去。楚明风见状,便道。
“我倒想问问前辈是如何会我道家的两仪幻虚功,看前辈方才打坐练气的法门,这两仪幻虚功已臻化境了吧?”
那男人听罢,猛然回过身子,双手狠狠拍在桌上,怒道。
“你道家内功心法?你道家的两仪幻虚功?这道家典籍难不成是你师父亲笔所著?这练习内功的法门难不成是你师父摸索得到?这都过去了二十年,你师父还是那副臭德行。”
楚明风听得这陌生男子辱骂自己师父,已是怒不可遏,便道。
“前辈虽说救了晚辈性命,但晚辈不知前辈与家师有何恩怨。就算有些宿怨,也不至于如此出言不逊,实在不该。”
男子道。
“你师父?呵,你师父。哎呀,你师父总是自命不凡,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他哪里容得下别人,臭小子,你才和徐一星认识几天,老夫认识他的时候,怕是你还没开花结果。”
门外白玉良听得屋内似有争吵之声,连忙推门进入,见得二人四目相对,连忙道。
“这是怎么了?大家好说好商量,义弟切莫鲁莽,若无前辈出手搭救,只怕如今你我兄弟二人早已是曝尸荒野。”
男人道。
“若知道这小子是徐一星的徒弟,老夫绝不相救。”
说罢,拂袖离开。白玉良见得男人坐在院落石凳之上,面色凝重,双拳紧握,似要与谁拼命一般。
白玉良道。
“这老前辈性格古怪,脾气暴躁,三弟莫要与他一般见识,好生休息。”
说罢,走出房间,坐在男人一旁,道。
“前辈,舍弟重伤初愈,言语之间,若有冒犯,还请前辈恕罪。”
男人道。
“哼,有其师必有其徒,这小子和他师父一个德行。”
说这话时,男人故意将后半句话抬高了音调,话音刚落,只见楚明风颤颤巍巍的从屋内走出,倚在门框,道。
“前辈虽说救我性命,也不至于如此辱骂家师吧。”
男人道。
“呦呵,都能下床走路了,臭小子,老夫能救你,就能杀了你。”
楚明风听罢,面无恐惧之色,只是目不转睛的盯着那人,那人见状,更是气恼。遂即起身,闪身而去,站在楚明风身前,白玉良见状不妙,连忙赶了过去。男人伸手箍住楚明风脖颈,冷道。
“臭小子,老夫若再使得半分力气,你小命难保。”
楚明风此时早已呼吸困难,面色渐渐发紫,却从嘴中挤出几个字来。
“我的命是你救的,你要取我的命,拿去好了。”
白玉良连忙伸手攥住男人抬起的手腕,正要发力,那男人回过头瞪着白玉良,道。
“你若阻拦,连你一齐杀了。”
白玉良道。
“那便杀了最好。”
话音刚落,男人伸出另一只手,也箍住白玉良脖颈,白玉良也顿时喘不过气来,使不出半分力气,心道。
“这男人好大的力气。”
男人见得二人同心协力,皆无恐惧之色,心中不禁暗自赞叹,又想起自己往事,不由得心中悲苦,便收手将二人推到一旁,仰天大笑道。
“若是老夫也有这等兄弟,岂会落得如此下场。”
说罢,顿时黯然神伤,拖着身子走到一旁,坐在一处,望向远方。
二人相互搀扶着,走到庭院,正欲离开,男人道。
“那小子伤势未愈,你们若是出了这茅屋,定会遭到仇家追杀。”
楚明风道。
“就算是死在他们手里,也总比死在这里强的多。”
男人笑道。
“小子,没想到你还有点骨气。”
说罢,起身走向二人,双手轻搭在二人肩膀之上,二人只觉得男人掌心处传来一股莫名力量,直逼二人心肺,未果片刻,二人便呼吸顺畅,神清气爽。
那人又道。
“若你二人死在这丛林之中倒不打紧,只是还要麻烦老夫给你二人收尸,若你二人不屑与老夫共处,那便不要理会老夫。”
二人听罢,不禁看向对方,不知这老头子葫芦里买的什么药。
男人说罢,回身走回茅屋,楚明风道。
“还没请教前辈名号。”
男人听罢,停下脚步,站在原处,悠悠说道。
“庐山之下,茅屋之中。怪癖老朽,笑傲江湖。罢了,罢了,老夫也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了。”
楚明风听罢,连忙道。
“前辈。”
男人好似没听见一般,继续走着,推开房门的那一刻,冷道。
“老夫黄徽。”
说罢,关上屋门,一人呆坐在桌前,不知想些什么。
楚明风听罢,绞尽脑汁去想,也想不起来黄徽这号人物,暗道:这男人武功如此高强,怕与家师不相上下,如此人物,为何在江湖之上却不曾留下只言片语,若留下半点名头,我自小游历中原,也会知道的。可如今,又怎会听得这名字如此陌生?
白玉良道。
“三弟,咱是走不走啊?”
楚明风摇了摇头,说道。
“暂且还不能走,一来,我伤势未愈,若是真遇见了那群倭人,只怕你我应付不下。二来,这黄徽定是与家师有什么渊源,我想查一查。”
白玉良听罢,却道。
“可适才,那人可是要杀了你我。”
楚明风笑道。
“二哥且信我一次,如若黄徽真要杀了你我,只怕刚才就杀了,就凭你我兄弟的本事,只怕不及他十之一二,他何必半路收手,他本无心杀人,只是适才不知哪句话刺了他的心吧?”
白玉良点了点头,直觉楚明风所言有理,又道。
“无论如何,前辈救过你我二人性命,虽说前辈脾气古怪,性格难测,但也不像恶人,你我兄弟理应怀揣感激之心,不可心生歪念。”
楚明风笑道。
“二哥你就是心善,就怕你是要成也心善,败也心善啊。”
白玉良呵呵一笑,他何尝不知如今世道混沌,乾坤颠倒,哪里需要什么善人,只是这脾气秉性出生便长进了骨髓,此时若要改变,难于登天。
白玉良道。
“可惜啊,我天生就是这般,只记得别人对我的好,却不想着别人对我的恶。”
楚明风听罢,也没多说半句,只是看着白玉良天真的笑脸,心中不免忧虑,打蛇不死反受其害的故事,他虽未经历,却也对其谈声色变。
二人决意在这茅屋之中住下,时间一久,二人对黄徽的戒心愈见淡然,也发现这男人虽说脾气古怪难测,却不是恶人,与黄徽也渐渐有了话题,三人晚饭过后,常常坐在柳下谈论事实,黄徽本就对前些时日,出手袭击二人之事,耿耿于怀。如今对二人也不再恶言相向,反而与二人结成忘年之交。楚明风的身子也渐渐恢复,那日晌午,楚明风在溪流之中打捞些水物,又去附近的镇子上沽了些酒,三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楚明风道。
“晚辈有一事不解,还请前辈赐教。”
黄徽听罢,笑道。
“老夫还纳闷,怎么今日想起与我这糟老头子喝酒,原是有事相求。也罢,你且说来。”
楚明风道。
“不知前辈与家师有何渊源,还请告知晚辈,晚辈从中调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岂不妙哉。”
黄徽笑了笑,叹息一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仿佛吞下万柄利刃一般,双眼流下两行泪水,抬起头来,望着碧蓝天空出神发呆。白玉良看向楚明风,楚明风也看向白玉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良久,黄徽道。
“世间恩怨,原本难明,前尘往事,何必再提。”
楚明风道。
“前辈若是有难言之隐,那就算了。”
黄徽道。
“也没什么难言之隐,既然你这娃娃想知道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老夫便告诉你。”
说罢,缓缓起身,踱着步子,走向一旁,若有所思道。
“按着辈分,你也应该叫我一声师叔。”
楚明风,白玉良二人听罢,不由得看向对方,楚明风连忙道。
“既是同门兄弟,又有什么大仇大恨,只是晚辈为何从未听师父提起过前辈?”
黄徽冷笑道。
“呵,若是你做了亏心的事,还会大肆宣扬吗?到时搞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他又如何做得上道阳派的掌门?”
楚明风听罢,也未反驳,但心知肚明,自家师父乃是江湖上少数的正派人士,在荆襄之地享誉盛名,怎么会做亏心之事?
黄徽见楚明风面色难看,道。
“老夫知道你不信这话,也对,若是旁人当着我的面说我师父的坏话,老夫也不会相信。”
说罢,顿了顿,又道。
“这事,也有四十多年了,那个时候,老夫与你师父,你师伯我们三人同时拜在寒山真人的门下学习道法武功,你师父师伯年长于我,自然成了师兄。本来啊,我三人情同手足,齐心协力,武功也不分上下,一齐学习道家内功,外功。师父传给我们三人两仪幻虚功,你师伯呢主要修习道家拳法,你师父呢主要修习道家掌法,至于我呢,虽说拳法掌法不及他二人,却习得一些暗器的指法功力。待我三人功力大成之时,生了一件大事。这话说来也就长了,三十多年前吧,老夫上了岁数,也记不大清,只记得那是一年寒冬,有一扶桑人来寒山求道,可道家功法本就不轻易传人,更何况是异族之人。我呢,自学武之日起,便发愿将道家功法发扬光大,但我自认为我没有错,何种武功,唯有相互研讨,不断交融才可立于不败之地。我便背着师父收那扶桑人为徒,其实也不算收他为徒,毕竟他与我年岁也差不许多,只是一心想着传他一些到家根基功夫,教他一些颐养天年的法门,他呢,也将扶桑的功夫说与我听,我二人互传功法,但我却从未将两仪幻虚功等上乘内功传给他,其实也不是不传,只是,若要将这功法练到极致,除非自幼修习道家根基功夫,不然难若登天。我与那扶桑人互传武功的事告诉给了你师父和师伯,我本以为我三人从小一起长大,感情似海,他二人也说过绝不会出卖与我,还对我说了好多冠冕堂皇的话。我本想待到我和那扶桑人传功完毕之时,我便将这些功夫中的精髓也说与你师父和师伯,想着道家内功天下无人能及,扶桑功夫又是注重外家功夫的修养,这二者若是相互融合,必能让功夫更加精进,毕竟那时我们都想着赢得一个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可我未曾想到,你师父师伯竟将这事告诉给了师父,我本一腔热血,被你师父和师伯搞得心灰意冷,最后师父将我逐出师门,将发扬道法的大愿交给了你师父和你师伯,我最初只道是你师父师伯遵规蹈矩,毕竟我的想法时至今日也算异类,最后待到一切明了之时,我才明白,一碗肉粥,三人分食,总比不过两人分食来的巧妙。至于我呢,就像是孤魂野鬼一般,无门无派,于是啊,我便来到这庐山附近,搭建了这茅屋”
白玉良道。
“前辈说的什么肉粥,是何意思?”
黄徽笑道。
“一份黄金是三个人分了好,还是两个人分了好?”
白玉良道。
“那自然是两个人分的好,但对于第三人讲,未免有些不公。”
黄徽冷笑道。
“呵,公平?何为公平?这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世人不患穷而患不均。若要公平,必有牺牲。”
白玉良叹息道。
“唉,如此说来,前辈也应开宗立派,可谁知如今却守着这茅屋,踌躇不前。”
黄徽道。
“老夫本无心于江湖虚名,之所以对此事耿耿于怀,只是觉得若要弘扬道家功法,若没些名气,又有谁会来拜师学艺?”
楚明风听罢,似灵光乍现一般,连忙道。
“前辈可还记得那扶桑人叫什么?”
黄徽道。
“铃木青。”
白楚二人听罢,连连叹息,齐道。
“前辈啊,你怎能教他道家功法。”
黄徽道。
“你二人这是什么意思?守尘抱旧吗?”
楚明风摇了摇头,便将近些时日铃木青勾结洛千克侵害中原武林的事说与黄徽,黄徽听罢,不由得叹息,道。
“唉,早知如此,当初老夫就该一掌拍死这倭贼。”
白玉良道。
“唉,前辈又不知这铃木青这般混账,也怪不得前辈。”
楚明风道。
“我终于明白这铃木青为何如此精通道家内功。也罢,前辈还是接着说吧。”
只听得此时上空飞过两只燕雀,黄徽也未探头观看,只是左脚猛然点向地面,见得两颗石子凌空而起,电光火石之间黄徽伸手夹住两颗石子,甩向空中,石子如闪电一般划破长空,只听得两只燕雀发出一声哀嚎,便落在地上,二人见状,不由得大惊,皆赞叹黄徽高明指法,楚明风心道:这指法怎么和林梓枫,韩青松使暗器的手法一模一样?
黄徽又道。
“然后啊,老夫便在这茅屋内收了两个徒弟,将我打暗器的功夫传与二人。之后,再也没收过徒弟。”
楚明风又道。
“那二人是否一个叫林梓枫,一个叫韩青松。”
黄徽听罢,诧异道。
“娃娃,你是如何知道的?”
白楚二人互相看着对方,只觉哭笑不得,楚明风道。
“放下我见前辈打石子的手法和韩青松,林梓枫的手法如出一辙,便斗胆猜想。如今那韩青松帮助洛千克不知残害多少江湖义士。”
黄徽听罢,心中不禁愧疚,思索片刻道。
“这混账东西,当初老夫传他功法之时,便告诉他不可做有违侠义之时,这混账将这话忘的一干二净。”
遂即,黄徽又道。
“不过不碍事,老夫既能传他武功,便能破了他的武功。”
说罢,看向楚明风,楚明风正欲开口,黄徽又道。
“你也算我师侄,这样,我将破解我指法的功夫传与你,来日你若见到韩青松,便可将他制服,适时,任你处置。”
白玉良道。
“如是这般,那便太好了,中原武林有救了。”
楚明风道。
“晚辈斗胆请前辈出山,晚辈武功低微,怕是领悟不到前辈高深功夫的精髓。”
黄徽苦笑道。
“老夫年过半百,这一条腿踩进了棺材,也有三十年未曾踏足江湖,如今心中有愧,早已没有颜面踏足江湖,我将破解暗器指功的法门传与你,也是一样的。”
楚明风听罢,连忙道。
“多谢前辈。”
黄徽笑道。
“不必谢我,老夫也算做了对不起江湖众人的事情,这样也能让老夫心安一些。”
白玉良道。
“前辈高义,晚辈钦佩万分。”
黄徽道。
“小子,你天行纯良,对你这兄弟也是肝胆相照,前几日我见你身上似有旧伤,不知是何人下此毒手?”
白玉良听罢,便将自己身中千毒掌的事情说与黄徽。黄徽听罢,不禁眉头紧锁,又叹息道。
“唉,这千毒掌毒性刚猛,老夫也无能为力,若是宫首天还活着,或许能用他的功力化解此毒,不过老夫虽未与洛千克交过手,对于他的毒辣武功也是略有耳闻你身中千毒掌,又怎么能活这么久?”
白玉良道。
“这要多亏唐灵门的镇寒珠和无伤丹,不然的话,只怕晚辈早已化成一堆黄土了。”
黄徽笑道。
“镇寒珠?无伤丹?这可是唐灵门的宝贝,小子,你蛮有造化的。你天性善良,又侠义为怀,老天不该如此薄情啊。想必日后,必有福报等着你吧。”
白玉良听罢,不禁苦笑一阵,道。
“什么福报不福报的,晚辈只求问心无愧罢了。”
黄徽笑道。
“老夫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说罢,回过头,看向楚明风,又道。
“小子,伤势恢复如何了?若无大碍,明日老夫便将破解暗器指法的功夫传于你。”
楚明风抻了抻胳膊,道。
“已无大碍。”
黄徽道。
“那明日日出之时,你便随老夫去那树林之中练功。”
说罢,起身走向茅屋,楚明风见得天边斜阳照在黄徽背上,地上影子,更显修长,心中不由得一阵酸楚,见他躬身行礼,跪在地上,道。
“前辈。”
黄徽愣在原地,也没回头,冷道。
“何事?”
楚明风叩首道。
“晚辈代家师向前辈赔罪了。”
黄徽听罢,仰起头,长呼了一口气,泪水从眼角滑落,又很快低下头,眼中含泪,笑道。
“都过去那么久了,老夫不甚在意,小子,你好生学习功夫,也算对得起老夫了。”
说罢,推开房门,走了进去,背着身子,顺手将门带上,熄了烛台,又是一个人坐在桌前,透着窗户,不知在想些什么,一片黑暗之中,唯有那一件青衫十分显眼。
楚明风也没起身,直是在那里跪着,白玉良道。
“三弟,前辈进了屋,你也起来吧。”
楚明风道。
“是我师父对不住他,我得替我师父了却这孽债啊。二哥,你也早些回去歇息吧,前辈若不原谅家师,我这心里总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儿啊。”
屋内黄徽闻听此言,早已是老泪横流,心道:徐一星啊徐一星,我与你斗了半世,本以为我教出来的徒弟远胜于你的徒弟,可今日来看,我怎么也想不到你竟能收这般忠义之人为徒,也罢,我输了,输的我心服口服。
白玉良见状,便道。
“三弟若要跪,那哥哥便陪着你跪。”
说罢,也跪在地上,只见此时忽然乌云密布,漆黑一片,电闪雷鸣,闷热潮湿。未果半壶茶的功夫,便下起倾盆大雨,又是狂风骤起,雨水打在二人身上,寒风刺进二人心中,黄徽见状,生怕雨水加剧楚明风伤口,又担心白玉良受了风寒,激发体内千毒掌的毒性,连忙从床下拿出一柄纸伞,推开房门,快步走出,打开纸伞,遮在二人头上,便道。
“臭小子,你俩是不是疯了?”
楚明风道。
“前辈,因家师一念之错,使前辈在这茅屋之中屈居数十年,今日晚辈淋上一夜雨,也有不得半分心安。”
黄徽道。
“你快写起来,看这架势,这雨要淅淅沥沥的下上一夜,你有伤在身,就是铁打的身子在雨里淋上一夜,也会吃不消的,况且你若是染了风寒,明日该如何学习武功招式?”
楚明风道。
“若前辈不原谅家师,晚辈便跪死在这茅屋前,也算是了却家师所欠下之孽债。”
黄徽道。
“你这娃娃,老夫平生最恨别人威胁我。”
说罢,将那纸伞丢到一旁,快步走向茅屋,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道。
“算了算了,怕了你了,你先起来,早些休息,明日与老夫去树林中练功。”
楚明风道。
“前辈是原谅家师了?”
黄徽无奈的点了点头,道。
“老夫没成想徐一星居然收了你这么一个好徒弟,老夫与他比了半生,自认内功外功不输与他,在教育徒弟上,老夫输的是心服口服。”
说罢,将二人搀起。
二人回到自己房间睡下,楚明风却是夜不能寐,他自小被徐一星收入门下,虽说是外门弟子,但师父对自己却视如己出。在他眼里,师父是江湖上少有的正派之人,平日里又教给自己许多人生道理,总是训诫自己不可做有违天地良心之事,可今日得知师父对黄徽所做之事,不禁谈之色变,不愿去想,由不得不想,他只道若是连师父都做过如此卑劣之事,江湖之上,他又该相信何人?黄徽与师父本是同门兄弟,师父也能为了一己私利,横下狠心,做此歹事。人心,到底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啊,说它是红的,便是红的,说它是黑的,也便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