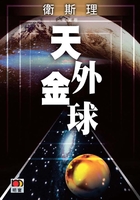“呃……呃呃……”
抽搐着,扭曲着。
“感受你的上帝吧,我让你提早结束痛苦,回归人间……”
神啊……
幻灭着,又创造着。
致幻剂粗暴的功效在发挥,倒地的可怜儿此时口吐白沫,他双眼瞪的巨大,眼珠子似乎都要跳了出来。他身体扭曲的挺直了,并不断抽搐着。
痛苦,奥瑟能够轻易看出他此时的感觉,但在这毫无保留的痛苦中,却有一丝如同狂信徒步入天堂的狂喜。
这药效……是不是有些过头了?
奥瑟有些感慨的打量着这奇怪的家伙,然后扭头看向剩下的两人。一个是被奥瑟一下子戳穿了腰的家伙,另一个是下巴都被敲裂的家伙。他们都用一种难以描述的表情惊恐的瞪着自己的同伴生不如死……他们不清楚这是一种容易上瘾的自虐性药物带来的功效,也不会知道……这是奥瑟的邻居兼同事的维克多·马丁私造的药物,一个失败的产物。
奥瑟把它当作特效药带在身上,专门稀释掉后喂给一些令他不爽的病人吃。
稀释前的药效……确实不错……
“你们谁想试试?”
齐齐摇头。
奥瑟嘴角微微上扬,露出愉悦的微笑。
他抬起胳膊,让手杖拄在地上以来支撑自己大部分的身体,他的脸藏在臂弯之后,铅灰的眸子冷漠的反射着烛火昏黄的微光。
哪怕他脸上的微笑都无法缓解这种残酷的冰冷。
因为有面具遮掩。
“告诉我想知道的一切,可怜的孩子们……”他声音在面具下变形,变得沉闷扭曲,圆圆的镜片擦拭的十分干净,处于阴影中的那一只让人清晰的看到了那颗冷漠的眼睛。
“快乐,是人生活幸福的根本,”手杖收回,杖头随意地敲了敲身后那人开始剧烈抽搐的躯体,“像他,是吧?”
乌鸦的脸高高抬起,一半处于微弱的光亮中,一半沉没于深沉的黑暗中。
形如死神啊……
“是、是啊……”
尚且还算活着的两人带着哭腔叫道。
……
奥瑟不知道这个黑奎蟒是什么,也从未听说过……或许自己的好友,那个身兼地下黑医的法兰西人维克多·马丁知道,但那家伙此时不在自己身旁,奥瑟只能够一个人凭着残缺的情报去找那个威胁自己的家伙。
自己杀了一名帮派成员,当晚就有人找上门来复仇……总感觉这明显不对劲。
用于威胁自己的,是自己的“真实身份”……
现在仔细一想,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威胁的话题。
对方索求什么?仅仅只是为了报仇?简单的面子问题?专门来找疫医的麻烦?他们在这么短时间里得知自己的日常身份和真实职业之间的关系的?
奥瑟明白了,他可能被某些看自己不爽的人盯上了。或许是之前那个意外受伤的主治医师,找了一个帮派来解决问题……
可实际上完全不必要如此。
奥瑟这么想着,已经在夜里穿过河边薄薄的迷雾,来到了建在病村河岸上的一户吊脚楼门前。
屋内灯火通明,简直就是昏暗无光的病村中耀眼的萤火虫。这就是占据了并存相当大的话语权的、在最近短期内于码头区异军突起的帮派——黑蝰蟒的据点。
惹人总得找对人……期待你们不会再找错了。
奥瑟手上的手杖灵巧的转动了几圈,大衣猎猎作响。
他踏上前去一步。
门外守门的小弟注意到了来人,刚想发声问话,就看见对方忽然暴起来到自己面前。他一个膝踢撞在了对方的肚子上。
呜咽声压过了原本该叫出来的高呼,悲鸣声被噎在了嗓子眼里。
简简单单的一记手刀打在了他的脖子上,让他昏了过去。
这个看门的混混背后虚掩的木门里,传来喝酒打牌的声音。
就只是普通的帮派吗。
只见奥瑟突然毫无征兆的一脚踹开木门,里面的众人在惊觉中起身。
下一刻奥瑟挥手一把爆裂粉,空气中立刻炸出了一片火花,像是枪声齐鸣的场景让黑帮们一时之间手忙脚乱。
快步走上前去,用力让杖头一下子锤倒最近一人,顺势收回的手杖没有收起抓在手里,而是一击从下往上挥在一个冲上前来的人的胯部。
漂亮的弧线,不是吗?
碎裂的声音传来,奥瑟自己都觉得毛骨悚然。
但此时管不了那么多,天晓得它有多蛋疼?
在混乱中,奥瑟顶着敌人措手不及时的脏话,右手一棍抽倒一人,转身躲过另一人的刀子,同时弯腰避开砸过来的酒瓶,然后左手握拳锤在刚刚拿刀子试图攻击自己的家伙的肚子上,力气之大令其五脏六腑都在翻山覆水。
“呕……”还在弯腰干呕着,这人被奥瑟扯着后领站了起来。他刚想强行挣脱反抗,却看见眼前爆裂粉产生的硝烟之后,自己同伴仓促地举起一把霰弹枪,而枪口,就朝着挡在奥瑟前面的自己……
“……呕……”
在变成筛子之前,他觉得自己还是有些反胃。
“彭……”
枪声还余音绕梁的时候,奥瑟推开已经失去站立力量的死尸,俯身快步冲到还在给子弹上膛的恶徒面前。
“咔噌——”
然而枪已经上膛完毕。
持枪恶徒几乎和奥瑟面对面而立,只不过高大的恶徒和俯身仰头的奥瑟身形差距如同狗熊和猎犬一般。
“——彭……”
左手轻轻推开枪管,奥瑟笑着。
随后右手挥着手杖,加速、用力——一击抽在恶徒满是污垢的脖颈上。
“祝你睡得安好……先生。”
奥瑟看着那家伙缓缓倒地,由衷祝福到。
…………
迷雾漫漫,水波平静。
虽然月亮在总是阴天的夜里并不常见,但那纯净的月光仍旧穿过了重重迷雾,隐隐洒在朦胧的世间。
河景很美,就是此时脚下一群站不起身的黑帮也是如此。
不过这也得忘掉那些关于水鬼和病村的恐怖故事才对……那并不是什么很好的民间故事。
奥瑟视线透过窗户遥望着外面的夜景,河上浮动着一层薄薄的雾气……他很久没见到过这么单薄的雾气了。
好像有人影在河中心走过……
奥瑟愣了一下,再次看去却别无他物。
是因为自己最近忽然频繁起来的幻视症吗?还是说什么奇怪的水草?
总不会是那些无法在河底安宁的溺死者所化的怨灵吧?
“真是笑话,这世间怎么会有鬼这种东西?”
奥瑟嗤笑道,他低头看着那些排排跪坐在地的黑帮成员,自己打击犯罪的行为让不好的心情舒服了那么一点点。
“说吧,你们刚刚见过面的那个家伙,究竟去了哪里?”
实力深不可测的疫医翘着二郎腿坐在一只还算干净的椅子上,面具下沉闷的声音穿出。
如同窟窿头一般的眼眶中嵌着的镜片,空洞且无情…………
河水静静淌过,吊脚木屋偶尔发出惬意的吱呀声。
河面上,迷雾逐渐浓郁。
伦敦塔隐藏在浓雾之后,顶天立地的如同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