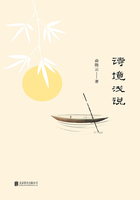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对有情人演出的千古悲剧中,有一个不露脸的角色,却时时让人感受到它可怕的存在,那就是无情的“命运”。
同样地,在悲剧《雅典人泰门》中也有一个不开口、不见于剧中人物表的角色,可它作威作福的势力像阴影般笼罩着雅典城。剧中上上下下的人物无一不围着它团团打转,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受它无形的操纵、支配。它是谁呢?它就是“黄澄澄、亮光光、最贵重的黄金”。
从剧名看,这似乎是一个个人的悲剧——“雅典人泰门”的悲剧。泰门刚出场时,何等荣耀煊赫,人人都争着向他献媚邀宠,他被包围在一片赞美、歌颂声中。可是一旦金银散尽,倾家荡产了,从他身上再没油水可捞了,那些胁肩谄笑之徒,立刻忘了平时受过他多少好处,一个个掉头而去,把他抛弃了。泰门从飘飘然的五彩祥云中一落千丈,流落在荒野,栖身洞穴,掘树根为食。泰门成为一个自绝于人类的野人,内心燃烧着不可熄灭的仇恨的火焰。
从一个慷慨豪华、有求必应的大施主,经历了世态炎凉,看穿了人心的虚伪奸诈,一变而为人类的憎恨者、诅咒者——他大起大落的兴衰荣辱,从满脸春风到精神崩溃,构成了泰门不堪回首的个人的悲剧。
然而要看到,泰门的个人悲剧不过为整个戏剧提供一个情节框架罢了。个人的兴衰荣辱无非像镜子般折射出世态炎凉的众生相。这一个以讽刺性、批判性为基调的悲剧,自有它内在的深度,远远超出于泰门的愤世嫉俗、满腹牢骚的咒天骂地。
强调《雅典人泰门》首先是一个社会性的悲剧,就必然需要我们从可怕的“泰门情结”中摆脱出来,不受泰门那种喜怒无常、大起大落的情绪所煽动,而以一种冷眼旁观的超然的态度去审视泰门这个人物和他个人的悲剧。
戏剧一开始,就以阴暗的色调呈现出一幅腐朽社会中的百丑图。这一伙人眼里认得的只是金钱,而泰门就是他们的摇钱树。
如果我需要金子用,
那好办,只消偷乞丐的一条狗,
去送给泰门,这条狗就会给我
变出金子来。要是我想把我的马
卖掉了,再买进二十匹更好的马,
怎么办?把这马送给泰门——也不用
开口要什么,给他送去就是了,
它立刻会为我生下二十匹马——
全都是骏马。
(第二幕第一景)
被捧得飘飘然的泰门,从酒席上站起身来,神态高贵,满怀激情,把天天上门来大吃大喝的食客们称作是天神特地从千万人中挑出来赏赐给他的“可亲可爱的朋友”——
你们不是都和我这颗心连在一起的吗?你们都太谦虚了,一句也不提自己的优点,我却在我的内心替你们说了许多的好话……充分证明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第一幕第二景)
谈到这里,这个自作多情、终年被包围在歌功颂德声中,精神上中毒太深的人,已经忘乎所以,产生一种幻觉,竟然以为在他的人格力量的感召下,人类已不分你我,财产公有,一个乌托邦时代就在他的宣告中诞生了:
我们天生就是为了以助人为乐,把朋友们的财富认为就是我自己的一份财产——还有什么比这更合适、更天经地义的吗?噢,这是让人多么欣慰的美事啊——有那么多亲兄弟一般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支配彼此的财产。
(第一幕第二景)
这时候的泰门真是眉飞色舞、神魂颠倒,自我感觉良好极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白日梦,肥皂泡般在他眼前飘浮起来了,借着那幻影,他看到了他本人就是人类大家庭的精神盟主——不用说,还是一位人人都心悦诚服的天然盟主。此刻的他正代表全体成员在表达人类大家庭的一个共同的信念。
古代寓言《狐假虎威》中有一只给老虎开道的狐狸,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错觉在狐狸的头脑里产生了:山林中的大小走兽望风而逃,并不是因为它挟着身后的虎威,而是它狐狸本人的威武吓破了它们的胆。凡是长年累月被奉承谄媚所包围,弄得晕头转向的人,最终都免不了会变成这么一只丧失了现实感的蠢狐狸。泰门就是最好不过的一个例子。
他受崇拜、他被捧上了天,他还以为完全出于人们对他泰门本人的爱戴、敬仰;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他全靠金山银山在背后给他撑腰——只有当他肆意挥霍、仿佛拥有用不完、掏不空的金山银山,像《红楼梦》中全盛时期的贾府那样,“把银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他才成为众人眼里最可爱的人。他好不心花怒放啊,当他看到——
哪一个不自称甘心替泰门效劳?
哪一个不声称把忠诚、才智、力量,
手中的剑,手头的钱,都奉献给
泰门老爷?伟大的、高贵的泰门呀!
可敬的、帝王般光荣的泰门呀!
只有忠心的总管,旁观者清,恳切地向主人指出,那火热的吹捧和歌颂,跟友谊毫不沾边儿,只不过是沾满铜臭的金钱交易罢了:——
收买这一片赞美声的金钱一旦
花完了,众口交赞的声浪也寂灭了。
用酒肉换来的“朋友”脚底上了油……
乌托邦的美梦哪里能容得进这冷酷的现实?泰门宁可闭着双眼把蠢狐狸做到底。这时候他已经穷下来了,债主们纷纷上门逼债来了,他毫不在乎,反而责怪总管太扫他的兴了——
竟以为我会没有朋友吗?放心吧。
要是我去叩开人们藏在心中的
对我的爱,开口借钱去试探
他们的情意,哪一个不乐意把所有的
听凭我使用呢?——就像你听凭我使唤。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灾难临头了,他的美梦却还只顾在膨胀。他不可思议地张开双臂,欢呼贫困的到来:家产败落了,可他拥有最大的精神财富呢——亲兄弟般的友谊。掏空了金山银山,更能见出人间的真情呀,更显得周围的一片歌颂都是冲着他本人的美德而发出的喝彩声呀。他人格的光辉因此格外亮丽夺目了。这岂不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吗?——
我眼前的“贫乏”可说是头戴金冠,
我要称它为“幸福”,我可以借此
探出我朋友的真心;你就会明白,
你怕我穷下来而担心,真是多余的。
我有这许多朋友,我怎么会没钱呢?
(以上引自第二幕第二景)
他越说越亢奋,一个最动人的幻象在他眼前飘过:他这位天然盟主只消在烽火台上点起一把火,各路诸侯一望见告急的信号,马上一窝蜂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勤王保驾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无须多说了,一个耻辱接着一个耻辱,一个打击连着一个打击,都落到了泰门的头上。一个个满脸笑容的“好朋友”一转眼变成了一个个无情的债主。幻梦破灭后,面对冷酷的现实,思想上毫无准备的痛苦,是难以表述的。泰门疯了。
在人生的七情六欲、浓淡深浅的感情色谱上,泰门所懂得的,永远只是两个极端:不是眼眶里含着喜悦的泪珠,想把全人类都拥抱进自己的胸怀;就是口沫四溅,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全人类。一旦白日梦破灭了,狂怒的他成了一座感情爆发的火山。在大喜大怒的两极之间,不存在中间地带;非黑即白,没有浓淡深浅的色谱。他不能控制感情,不明事理。没有自我反省这回事,完全意识不到他个人的悲剧,其实是他自己亲手造成的,是咎由自取。他只知道咒天骂地,却没有勇气去面对他自己。
在这一点上,泰门远不如李尔王。李尔王也是长年累月被包围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精神上中毒太深的一头蠢狐狸(一心以为摘下王冠、走下王位、交出了王权的李尔,将依然是受崇拜的李尔)。他和泰门可说是一对难兄难弟。遭受到重大的打击后,他同样地发了疯。可是不同于泰门,他的发疯正是他清醒地重新认识现实生活、重新认识他自己的开始。在天昏地暗的荒野上,在无情的狂风暴雨中,他不由得回顾了自己错误的一生,对于自己做出了这样一个评价:他是个“受罪大于犯罪”的人。
他眼前所受的罪太深太重了,可他终于认识到在他个人的悲剧中,有他自己的一份不可宽恕的过失。更好的是,这个向来唯我独尊的暴君,由于自身的落难,推己及人,联想到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的受苦受难的人民:
可怜你们赤身裸体的穷鬼呀,
没处可躲,逃不了这狂风刮、暴雨淋,
头上没一片瓦、肚里没半粒米,
披一片、挂一块,千疮百孔,怎对付
眼前这天气!唉,我几曾想到这许多!
最后他还说了一句话,无疑是触及了自己的灵魂:“荣华富贵,到外面来领受一下穷人受的罪吧!”
李尔接受了现实生活给予他的严酷的教训,他的眼睛睁开来了,分得清是非好歹了,性格开始转变了;而我们观众(读者)对这位暴君的看法也随之而逐渐转移,我们不再是冷眼旁观地看着他自作自受,而是对于他多了一份同情心。
回头再看泰门又怎样呢?他什么都没学到。一旦衰败失势了,在泰门的眼里,天地一片漆黑,人心一片漆黑,他的诅咒把整个人类一网打尽:从今以后——
叫泰门的憎恨,一天比一天深——
让憎恨吞没了全人类……
(第四幕第一景)
这无边无际、吞没全人类的憎恨,仿佛就是他们应得的惩罚:不分男女老少,都必须得为他的倒下去负责;而他泰门俨然凌驾于一切之上,是道义力量的化身。这是他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他借此可以逃避面对现实,逃避面对自己,逃避应有的羞耻感和悔罪感。
泰门对人类发出了滔滔不绝、令人毛骨悚然的诅咒。其实大可不必。要知道他本人来到人间就是一场大灾难。日日夜夜请酒设宴,挥霍摆阔,漫无节制地把有限的自然资源、把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的社会财富任意糟蹋,这是在慷他人之慨啊!他的总管描述了从他眼里所看到的痛心景象,就是在诉说泰门的罪过:
咱家的整个大宅院吆五喝六的,
挤满了酒色之徒;我们的酒窖里,
酒,满地泛滥,像痛哭流涕;
每个厅,每间房,全都是灯火辉煌,
歌声喧闹;我就独个儿躲在
漏个不停的酒龙头边,我的泪水
也在哗哗地直流……
我总是这么说:在这个晚上糟蹋了
多少酒肉去填饱奴才们的肠胃。
(第二幕第二景)
更可怕的是泰门的挥霍对人性的腐蚀。有了他这株摇钱树,谁还愿意挥着汗水从事各行各业的生产劳动呢?反正泰门高价收买谄媚,只消拣泰门爱听的说给他听就是了。假如给泰门送一条狗去,“这条狗就会给我/变出金子来”,眼前有着这一条现成的生财之道,那么一切费心耗力的正当劳动都将黯然失色了。
泰门自称拥有的土地直通到斯巴达(第二幕第二景)。但终究还不出雅典境内;如果整个世界都归给了泰门,陆地海洋上的一切资源财富全都归泰门支配,财神爷普鲁托当真成了他的管家,那又怎样呢?泰门早已当众表示过了:“要是啊,我拥有一个个王国,拿来/一一地分送给我朋友,我永不会厌倦。”(第一幕第二景)毫无疑问,无穷无尽的财富都会被他用来收买、腐蚀全人类,直到整个人类堕落为只知道尽情享受的寄生性动物,忘记了正当劳动的求生手段,再不懂得挺起腰背,用自食其力来维护做人的尊严了。
法国有一句谚语:“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好心铺成的。”总管说到他主人,有一句话同样发人深思:“罪孽深重,就为他只知道做好事!”(第四幕第二景)魔鬼曾经化身为蛇,用鲜红的苹果去引诱人类的祖先。人类第一次堕落了。现在,慷慨豪奢的泰门有求必应,这其实是用更诱人的金黄色的苹果,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诱人类走上第二次堕落的道路。
人类的祖先被驱逐出伊甸园,用滴在泥土上的汗水学会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坏事因而变成好事。这第一次堕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泰门手拿着黄金的引诱。他漫无节制的“慷慨”(幸而他还没有漫无止境的财富)如果当真给人类带来了第二次堕落,那么人类再没有自救的希望了。因为他已什么事也不会干,什么事也不屑干,他只消学会在黄金面前曲意奉承就够了。在把人生的第一要义“劳动”抛弃的同时,他的人性也随之被扭曲了,干枯了。
把泰门这个精神上的低能儿当作悲剧的主人公,那是过于抬举他了。只有把他从他潜居的主人公的宝座上拉下来,我们的注意力才会集中于他身后的靠山:那冷酷无情、没有人性的金钱。几乎所有的剧中人物,在灵魂深处都打上了金钱的烙印。黄金,这个不开口的哑角,才是这个悲剧的中心人物,它才是真正的主人公。不把《雅典人泰门》仅仅看做个人的悲剧,而是以社会的悲剧、人生的悲剧去认识它,那么它自有内在的深刻意义,激发我们去深思:古代雅典的社会悲剧,会不会是一面镜子,让今天的我们从中窥见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呢?就是说,在我们有声有色的人生舞台上,会不会也存在着一个幕后的主人公在操纵一切呢?而且它也就是那冷酷无情、没有人性的黄金。
堕落为人类憎恨者的泰门,发誓要与人类割断一切关系,他逃避到荒野,却忽然挖掘到一坑黄金,然而这万人贪求的“黄澄澄、亮晶晶”的金子对于他,已一无用处了,只能触发他愤怒的回忆,让他深恶痛绝地诉说黄金的罪状:它能“把黑的变成白的”,又能——
使丑的变成美,无理变成有理,
卑贱变尊贵,白头变成了青春……
让该遭诅咒的,蒙受祝福,又能叫
白斑点点的麻风病,受众生爱慕;
能抬举小偷,偏叫他高高在上,
受屈膝的敬礼……
(第四幕第三景)
在这段为马克思引用过的著名的独白里有着泰门的痛苦的经历,我们相信也隐藏着剧作家本人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深沉的感触,我们今天读来不能无动于衷,因为想到了一旦人类失落了自身的尊严感,拜倒在黄金的脚下,只认得黄金是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人性被扭曲了,异化了,人类社会就会演不完一幕幕香臭好恶完全颠倒过来的荒诞剧。
正因为这样,带着现代人的一份焦虑去读《雅典人泰门》,仿佛这带有寓言色彩、用极度夸张手法所展示的一幕古代悲剧,就是莎翁留给后人的一个思考题:金钱和人性、物质和精神间的关系,一旦倾斜了,失常了,甚至一边倒了,我们还能以泰然的心境瞻望人类的前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