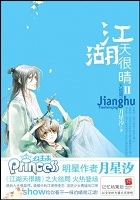王景云正与几位好友赏花吟诗,听着山下弱水河面传来阵阵笑声便多看了一眼,才发现正是自家妹妹王倩盼与其他外家的小姐妹。
“这花色生得别致。”王倩盼轻嗅,见着模样与紫薇花似,不过不知紫薇花亦有蓝柴色的。一旁俊秀男子见此浅笑,温言说道,“这亦是紫薇花,寻常的品种是紫红色,而这种是翠薇。”
王倩盼见身后有人,心中微惊缓缓回头,眼前这男子生的俊俏,一身并不张扬的淡青色难掩其气质,细看眉眼有些相熟,却一时想不起是谁,想着这样盯着外家男子实在不妥,低头侧过脸去,嘴角却泛起浅浅笑意。
“盼儿,你瞧着是不是面熟?他是表哥谢灵兴的堂弟,谢灵东。这谢兄最是温润有才,我曾与你提起过。”王倩盼之兄王景云如此说道。
“原来是谢表哥的兄弟,失礼。”王倩盼并未抬头去瞧,只是行了礼。谢灵东还礼,亦对身边王景云说道,“刚才听你们在船上说笑,是在说些什么乐事,倒也让我等亦笑一笑。”
一旁的王静佳上前说道,“我们刚才是在猜谜玩……”
王倩盼走到她身旁,示意止住话头,“女儿家玩闹的谜实在不入名士之眼,何必让各位公子少爷笑话。咱们只管赏花,他们只管作诗。”
“若姑娘想赏花,前头还有赤薇和银薇,亦是紫薇难得的品种,在下愿作陪。”谢灵东话拱手道。
“晓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春;桃李无言又何在,向风偏笑艳阳人。”听着有人吟诗,正好解了这片刻的安静。吟诗之人正是同行中人,年纪稍大些许是三十有余,面貌倒是普通。
王倩盼在一旁浅笑,低声对兄长王景云说道,“樊川居士这首诗称赞紫薇花盛开时节长久,桃李再如何也亦凋落,此人说出来倒让人觉得自诩紫薇花,众人不如他长久。不过再长久又如何,亦是要落的,此人实在是想不开。”
“你这眼睛也太厉害了些。这位柳公子刚封官正是得意时,你莫扫他的兴。”王景云亦笑,伸手将落在她头上的紫薇花拿去。
“我哪里有兴致去扫他的兴,哥哥也太小瞧我,我只是想瞧瞧他能借樊川居士几首好诗。不如学一学古人曲水流觞,如何?”王倩盼伸手拉着王景云的衣袖,自从幼时开始,只要她拉兄长的衣袖,没有哪次心意是没有如愿的。
曲水流觞本是上巳节的宴饮以去灾祸祈福,众人于弯曲小河流而坐,放酒杯顺着水流而下,酒杯在谁面前留下,此人便吟诗饮酒。虽不是上巳节,此举倒不失为文人墨客相聚的好法子。
众男子分开坐好,酒杯从上游缓缓流下,在首位王景云跟前打了个转,继续往下走,逗的一侧的刘妹妹笑,再眼巴巴看着这酒杯到底会在何人跟前停留。酒杯似有灵性,偏生就在之前那位吟诗公子跟前停下。
王倩盼浅笑,说道,“还请柳公子饮了此酒,再作首“春”字的诗。”
此人饮了酒,大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众人皆面面相觑,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应,在一旁当看客的小姐们已有人掩嘴笑,柳公子不知众人为何如此,此次亦是自己初次参与名流之宴会,怕是出了错惹得人笑话,一时手上的酒杯亦不知是该放下还是端起。
见此,谢灵东出言,“孟郊此诗倒是极符合柳兄刚刚高升之喜,用的极好。”
众人亦拱手称好。
王倩盼瞧了谢灵东一眼,却发现他亦瞧着自己,微微脸红低下头去不敢去望向那边,只取了酒,又开始新一轮。这酒杯似通了性,停在谢灵东跟前,于此王倩盼才好与众人一般看着他。
谢灵东端起酒杯,便向王倩盼所在的高处看去,见着她浅笑便知她为何笑。不知为何此女子的一颦一笑都似有灵性般,显得动人又醉人。
“谢公子请饮酒,再以这酒字为诗。”
谢灵东饮酒,浅笑着环视众人,便缓缓说道,“醉吟先生有首诗倒是极好。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众人亦是愣住,不过在座都是通透之人,转念便心领神会,亦笑。
倒是王倩盼让王静佳替了自己的位置,起身准备去前头走走,不愿错过难得赤薇和银薇难得品种。可惜四周转了一阵,却没能寻到,不过山间杜若开得不错。
王倩盼想着正巧今日乞巧,虽有其他物件倒也没什么巧趣,这杜若幽香再好不过,便采了许些。
不知何时那处曲水流觞之宴会已罢,王景云与谢灵东二人正遇着王倩盼,三人便说笑。
“这曲水流觞竟玩的如此无趣,的确不如早些散去。”王倩盼不去瞧谢灵东,这话偏是对他说的,“小女子浅薄,竟不知拾人牙慧也能登名士之宴。”
王景云见谢灵东只是浅笑并不恼,于是出言笑道,“柳公子是初次来这样的宴会,失了些许礼。但你这背后说人,岂不是更加失礼?”
“柳公子是初次见这样的宴会,那谢公子呢?谢公子难道不知无论是行酒令还是其他,都需得是自己做诗,作不成多吃两杯酒便是,哪有人拿着书卷直接生搬的!难不成谢公子作不出好诗来,又不肯失了面子?”王倩盼打趣。
“在下在姑娘面前竟作不出诗来,实在是羞愧。”谢灵东倒也不辩。
王景云大笑,说道,“这就是谢兄的为人之善,为了让柳公子不失体面只能如此。谢兄喜诗书乃是名流中人人皆知的,盼儿你居然说谢兄作不出好诗,实在是冤枉谢兄。”
“听闻王家家风素来是熟读诗书,在下不敢在姑娘面前卖弄。不过若姑娘喜欢,日后我作了诗便托景云兄给姑娘,还请姑娘赐教。”谢灵东说罢便觉得自己有些唐突,今日不知怎的接连失了洒脱风范,着实不像名流之人。
三人正说着话,远处刘妹妹走了,向两位公子行了礼,对王倩盼说道,“盼姐姐,这日头快到晌午咱们也该回去了。”
王倩盼生出丝丝懊恼,自己竟忘了今日乞巧,需得沐浴焚香行礼,于是说道,“哥哥,我与众妹妹先行回去。”行了礼,便又匆匆上了船。
谢灵东看着她所在的船远去,都没有瞧着一旁偷笑的王景云。
“谢兄,船已走远!”
谢灵东便知失礼,拱手笑道,“景云兄见笑。”
王倩盼回到院子时,如水如月两位大丫头已将沐浴焚香以及晚上乞巧用的东西准备得齐全,她们二人年纪虽不大,却也是从小跟着伺候算得上是老手,自然会有有差。
“姑娘,奴婢将这杜若烘干后缝制个香包?”如水接过刚从离山采摘回的杜若,转身放进内房。
每逢祭祖亦或过节,沐浴焚香乃是必然。
王倩盼不知怎的全心想着的便是今日遇见的那位谢灵东谢公子。若说才华横溢倒也未亲眼所见,若说是面貌出众倒也不然,想比由祖父带着参加的诗会所见的名士之流,那位谢公子也只能算作上游却非顶好。可此人却与常人不同些。
好在热水腾出迷雾倒也让她发红的脸不至于引人疑问。
可是片刻过后,王倩盼却微微摇头,心里暗想道,祖父从小亲自训导自己,其用意旁人看不清,难不成自己也不清楚么?
王家的女儿自是要护王家的根基与荣耀,哪里是容得其他的,可偌大的宫,他人口中威严的帝王,都是陌生的,乃至带着丝丝凉意。
王倩盼想着,若自己不是庶出,好歹也能嫁个寻常公子不争是非,自是鸳鸯的日子。身为嫡女自是风光,亦比庶出尊贵些,不过其中滋味自是旁人不知的,王家的嫡女便是要为王家生为王家死,倒是不重视的庶出却还能依了自己心愿,平淡一生,这亦是王家嫡出女儿不可望不可求的。
王家家大业大,子嗣自然比寻常人家多些,此次乞巧节自如往常般热闹。王倩盼正与妹妹们吃着酒,瞧见兄长王景云招手示意,便悄从宴席中离去。
“哥哥不去吃酒,叫我过来作甚。”王倩盼问道。
王景云笑道,“耽误盼儿吃酒,是为兄的不是,这里先向盼儿赔礼。”说着便拱手。
“就会拿我打趣,小心我不理你。”王倩盼见着他如此,噗呲一笑。
“那可不行,这封信的主人还等着盼儿你回信呢。”说着便从衣袖中掏出一封书信,递给王倩盼,而她未接反而侧过身捂鼻掩笑,却故作不知,“是谁?”
“谢家公子谢灵东,今日见着的那位。谢兄本说好是今日归去,却在别院住下,全是因为想等这封回信。你也知道,谢家的封地离咱们这也不算近,走动几次自是不易。”
王倩盼心头一惊,之后便是酥酥麻麻的,正准备接过那书信却突然愣了半晌。
“哥哥,这信我不能收。”王倩盼看了一眼那信,转过目光,“哥哥应该知道祖父的打算,为何还如此糊涂。为不惹是非,还请哥哥将此信原封不动的退回去,此事就当没有发生。”
“既然妹妹知道祖父的打算,那便听听为兄的打算。当今圣上年轻有为自是不假,可宫中女子太多,妹妹在宫中岂不是要受苦?若是其他人家,万一婆家有人给你气受,为兄的自会替你出气。若是帝王之家,为兄便是有心无力,再不能护着你……”
王景云叹气,继续说道,“这位谢灵东自幼丧父且由伯父母养大,他伯父母是咱们姑父姑母,有这层关系在,你嫁去他家也不会受委屈。我与他亦是数年好友,知其非池中之物,今日我见他对你有意,便有心撮合。说来做哥哥的是担心自家妹子明珠暗投,又担心你日后受委屈。”
王倩盼听着已是梨花带雨,“哥哥想护着我,我亦想护着哥哥。只是万一我入了宫,哥哥的这些苦心被有心人知道,便会害了哥哥。今日听哥哥的一片话,却让我难过。哥哥会有嫂子,而妹妹也会出嫁,不过任他沧海桑田,哥哥的对我的好自是不会忘记。”说着便是掩面哭泣。
“是做哥哥不好,又惹盼儿伤心,该罚。”王景云将信又收好,“为兄这就去吃杯罚酒,盼儿你看如何?”
王倩盼眼带泪嘴带笑,“罚你多吃几杯,喝醉了出丑逗我乐。”
“得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