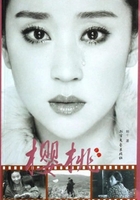十二年后
“把你的手举高!”我拨着吉他弦,欢快地唱着,一边对着我最喜欢的“客户”麦克斯露出微笑。
“脚也踢起来。”我继续唱,“现在转圈圈,转转转!弯下腰来碰你的——”
“——鞋!”麦克斯大喊。
“做得好,麦克斯!”歌词是我随口诌的,但自闭症的麦克斯还是跟着玩了起来,疯狂地咯咯笑。而当麦克斯碰到脚趾、直起身来蹦跳个不停时,他的母亲乔雅也在我办公室的角落里笑得很开心。
“还要,凯特小姐!”麦克斯央求着:“还要,还要!”
“好吧。”我严肃地说:“不过,这一次你要跟着一起唱,可以吗?”
“好!”他一边大喊,一边举起双手开心地挥舞。
“保证哦?”我问他。
“好!”他的热情是有感染力的,我发现自己也跟着笑了起来。
“来,麦克斯,”我慢慢地说,“跟着我唱,好吗?”
我从事私人音乐治疗师的工作已经五年,专门提供一些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治疗,而麦克斯就是我的首批病患之一。经由语言治疗师的推荐,乔雅在他五岁时带他来看我,因为麦克斯在她那里没有任何进展,始终拒绝说话。在我们每周一次的治疗课程中,我半哄半骗地先从他那里得到单字的回应,然后是简短的句子,再逐渐进展到完整的对话。现在,我们的治疗课程变成了唱歌、跳舞、一起玩闹的时光。表面上看来,我帮助他增进了说话和运动神经的技能,但实际上绝不只如此,这也有助于他的社交,让他可以敞开心门,信任别人。
“好,麦克斯,现在你要填空哦。”我开始了,边弹起吉他边唱:“我的名字叫麦克斯,我有——”
“——棕色的头发!”麦克斯边叫边笑,“我的名字叫麦克斯,我有棕色的头发!”
我大笑。“好棒喔。”我弹出另一段旋律,唱道:“我长得好帅,所有女生都盯着我看。”我唱着对他挑挑眉。
麦克斯笑到跌在地上,我等着他重新站起来。“凯特小姐,这样讲好三八。”
“三八?”我假装吓唬他:“三八就三八啊,先生,你到底要不要跟着我唱啊?”
“再唱一遍、再唱一遍!”麦克斯说。
我向他眨眨眼睛。“我长得好帅,所有女生都盯着我看。”我重新弹起吉他,重复唱。
这次麦克斯跟着唱了,因此我接着往下。“我刚满十岁,我变得好——”我唱道。
“老!”他大喊,挺起胸膛,伸出十根手指。“我变老了!”
“没错,你这老家伙!”我拨动琴弦,继续我的即兴创作。“但我最棒的优点是,”我唱道,“我金子做的心。”
等麦克斯跟着唱时,我停下拨弦的手,放到胸口上。“我最棒的优点是我金子做的心。”麦克斯又开始傻笑,伸手遮住嘴巴。“这也好三八!”
“你说的没错!”我对他说,“但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麦克斯。”
他又露出大大的微笑,并且挥舞起双手。“你也是好人,凯特小姐。”
我将吉他放下,空出手来拥抱他。今天,与其说是他需要我,其实我更需要麦克斯和他天真的乐观,但我不想让他知道,因为治疗课程的重点不应该是我。
“谢谢你,凯特小姐!”麦克斯紧紧地环抱住我的腰,将头压在我胸口上,高声喊说:“我爱你!”
“麦克斯,你真的很特别。”我回答他,惊讶地发现泪水刺痛了我的双眼。“为了你妈咪,这个星期要乖乖的,好吗?”
“好的,凯特小姐!”他开心地说完后,蹦跳着过去给了乔雅一个拥抱。
“谢了,凯特。”乔雅微笑地说着,站起身来也给她儿子一个紧紧的拥抱。“麦克斯,你要不要先去候诊间看看戴娜?我要和凯特说一下话。”
“好!”麦克斯说,“凯特小姐,再见!”他一边叫一边冲出了办公室,任门在背后重重摔上。
我转身面对乔雅。“一切都还好吗?”
她微笑。“我正要问你这个问题呢,你今天不太对劲啊。”
我摇摇头,暗暗责备自己,竟然让私人生活影响到我的专业。“没事,我很好,乔雅。”我说,“谢谢你。”
她站近一步,近到足够我可以看到她眼底有一丝怀疑?“和丹恩进行得还顺利吗?”她问。
“很顺利。”我迅速地回答。过去五年来,乔雅和我变得很熟,我知道她是个单亲妈妈,她很艰难地维持收支平衡,并且努力让儿子的生活尽量正常和轻松。而她也知道,我还在努力克服十二年前帕特里克骤逝的悲伤,但最近我终于开始与一个男人认真约会,而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认为他很适合我。
“所以,是别的事啰?”她轻声问。
“没事,真的。”我回答得太快,也太轻松。我看见她眼底闪烁了一下。“别担心我,”我重振所有的信心又补充了一句,“我没事。”
但等乔雅满脸怀疑地牵着麦克斯的手离开,我跌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里,将头埋在手里。花了整整五分钟才重新恢复力气,打开医生今天给我的档案夹,里面写着一堆医学词汇,像是慢性不排卵及原发性不孕。
两小时后,我完成今天的病患记录。我往南走沿着第三大道准备前往“椅子”,这间温馨的酒馆位于莱辛顿和第四十八街的转角,是过去一整年丹恩和我的最爱。我们预约的时间是七点,越接近目的地,我的心越是怦怦跳得厉害。
我必须将医生给的消息告诉丹恩,让他知道我的卵巢基本上已经停工,但要是他因此改变心意,不想和我在一起了怎么办呢?失去帕特里克后,他是我第一个认真交往的人。我好不容易终于做出决定,愿意让自己的人生和另一个人的重叠在一起,我不能失去这份感情,我无法再次孤单一人。
你又不知道丹恩会说什么。在转过第四十八街转角时,我这样提醒自己。我们从未认真讨论过孩子的事,只在刚开始约会时粗浅的对话里聊到过。我们认识时,我才刚满三十八岁,照理说,我的生理时钟应该还能运作正常,但很奇怪却是一片死寂。我一直以为(年纪越大怀孕就越困难,这点我当然很清楚)还有大把时间来考虑要不要孩子,却怎么也料想不到,自己会在不到四十岁就被宣告怀孕无望。我连想不想要孩子都不确定,但机会之门就这样被关上,我实在无法接受。
万一丹恩也没办法呢?
抵达“椅子”的入口处后,我看了一下手表。我已经迟到十分钟,但我心里却有一部分渴望就这样转头回家,我可以发短信向丹恩道歉,说我被某个病患耽搁了,然后建议我们点外带餐就好,这样我就可以多出一个小时不去面对这个事实。
“凯特?”
丹恩从餐厅走出来,让我的计划破灭,他关切地皱起了眉头。
“喔,”我挤出微笑,“嘿。”
“你站在外面做什么?”他走上前一步,伸手放在我肩膀上,我立刻感觉好多了。这就是丹恩,完美先生,金发蓝眼,每个人的好朋友,对我的爱理智而合度。一切都会没事的,他不会只因为我的卵巢就放弃我,弃我而去。
我深吸一口气。“丹恩,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他脸上掠过一丝犹豫,但随即微笑摇摇头。“我们先进去再说吧?”
“是这样的——”我才开口。
“等到坐下了再告诉我,好吗?”他牵起我的手,没等我回答就转身往里走。我叹了口气,跟着他进门。
“惊喜!”我们刚踏进门,一片招呼声冲着我们齐声响起。我倒抽一口气,往后跳开一步,好让眼睛适应餐厅里昏暗的光线。过了好一阵子我才辨认出,入口的走廊上挤满了人,全是这世上我最爱的人:我姐姐苏珊和她先生罗勃还有他们的孩子珊米和凯文、我最好的朋友吉娜和她先生韦恩、十来个我这些年交往的朋友、丹恩的弟弟威尔以及他最好的朋友史蒂芬,还有好几对我们偶尔会一起出游的情侣和夫妻。
“发生什么事了?”我直接对着我姐姐表达出困惑,因为能帮我解开谜团的人似乎总是她,但同时会批判我的人通常也是她。但她只是露出微笑,指指我背后。
我像慢动作一样,缓缓往门口的方向转过身,惊讶地发现丹恩正单膝跪在地上。我对着他眨眼,心跳得好快。“你,这是在求婚吗?”
他大笑,“看起来应该是吧。”他从口袋掏出一个蓝绿色的戒指盒,打开盒盖,高高举起。“凯特,你愿意嫁给我吗?”
朋友们热烈地鼓起掌来。我看着盒里完美的蒂芙尼单钻戒指,感觉时间像是给冻结住了。刹那间,我心里只浮现一个念头——不对,这和帕特里克求婚时拿的古董订婚戒差别太大了!但这念头随即被强烈的罪恶感所取代。我不应该想起帕特里克的,我是怎么了?此时我应该考虑的是在没说出医生的消息的情况下,我能不能对丹恩说我愿意?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又如何拒绝他。
当然,我并不想拒绝他,我提醒自己。丹恩很完美,总是帮忙扶住门,从不忘记说请和谢谢,是所有母亲心目中最佳的女婿典范。事实上,我母亲就从不吝于把握机会提醒我,能找到丹恩是我的福气。我从未考虑过结婚的事,不过,这确实是很合理的下一步,不是吗?所有相爱的两个人都会这么做的。
“凯特?”丹恩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
心跳加速的同时,我感觉自己挤出了一个笑容。“我愿意。”我听到自己这样说,而且我也知道这是正确之举(这不是很明显吗?)因此,我又重复了一次:“我愿意,我当然愿意。”我告诉自己,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的心满满的。“是的,我愿意嫁给你,丹恩。”我微笑着对他说。
他欢呼着并跳起身,将我拉进怀里,转圈跳起舞来,朋友们围在我们四周欢呼、吹口哨。“凯特·魏斯曼,”他说,“我会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快乐的女人。”
我笑着看他将戒指滑进我的手指,看着戒指在灯光的映衬下,折射出上百万颗的小星星。
“我爱你,凯特。”他将我拉近,低声说道。但在一片嘈杂中,我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
接下来的时间里,朋友们将我们团团围住,讲述关于我们的故事、称赞我们是一对璧人、拍拍丹恩的背、亲吻我的脸颊,而我行礼如仪地微笑或大笑,但感觉却十分茫然。至少有六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很高兴看到我继续往前走了,还有六个人说,丹恩真是个理想伴侣。我发现有好几次,吧台后的女服务生起劲地盯着他看,我很高兴他似乎都没注意到。
苏珊一直忙着追赶她那两个调皮的小鬼,因此,当丹恩和他的朋友们打交道时,是吉娜挤到了我身边来,我知道她一定了解现在我心中就像坐云霄飞车般的情绪波动。在前夫比尔过世的六年后吉娜再婚了,我还记得当时她告诉过我,答应求婚后的心情感觉就像是狂风过境一样。因为自己往前迈进而感到罪恶、又因为再度找到真爱而感到喜悦,对于即将展开的新生活抱持审慎的乐观、也因为彻底搁置旧有的人生而感到懊悔。
“你还好吗?”她递给我一杯香槟,问道。
“还好。”我微笑,“谢啦。”
她轻轻地拥抱我一下。“真难以置信,就为了在所有朋友面前向你求婚,他竟然把整间餐厅包下来。”她笑着摇摇头,“这家伙真有一套,是吧?”
“吉娜?”正当她准备走开时,我抓住了她的手臂,问道:“万一我不能生孩子的话,你觉得丹恩还会愿意娶我吗?”
“什么?”吉娜愣住了,直直盯着我。“凯特,怎么回事?”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今天去看过医生。”然后我颤抖地将今天医生说的话大概复述了一次。“没关系,我应付得来的,”看见她担心的样子,我连忙说:“我只是担心丹恩而已。”
“喔,凯特。”她静静地抱着我。“那他想要孩子吗?”过了好一会儿后,吉娜问。
我耸耸肩,直起身来。“我不知道,我们没有谈过这个问题。”
“你们没有谈过?”她的语气没有指责的意思,但我还是感觉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
“总是找不到适当的时机谈嘛。”这理由连我自己说出口都觉得很傻。“而且,我本来应该怀的是帕特里克的孩子。”我用低得像耳语的声音加了一句。
吉娜的眼中满是理解。她咬着下唇,以我对她的认识,我知道她正忍住某些话不敢说出口。但最后她终于还是说了:“那你想要孩子吗?”
“我不知道,但我还没心理准备接受自己不可能有小孩这件事。”我在泪水溢出前,先抹了抹眼睛。
“没人说不可能吧,”她坚定地说,“或许你可以试试试管婴儿,或者如果你还有健康的卵子,也可以雇用代理孕母,甚至可以考虑收养。方法有很多,不准你丧气地以为一点机会都没了。”
“谢啦。”我露出虚弱的微笑。
“至于丹恩,你一定得告诉他。”她继续说,“但这绝不会改变他对你的心意,他爱你。今天晚上先别烦恼这件事了,好吗?好好享受。不过,要跟他谈谈,凯特。马上要和你结婚的男人,应该要能和你聊这些事情。”
“我知道,我会的。真不该告诉你这些的,别担心我,好吗?”我换上笑脸,趁她还来不及开口之前先走开。
直到二十分钟后,看见帕特里克的母亲推门进来,我才真正醒过来。
“凯特!”她惊呼着、冲上前来,紧紧抱住我,身上还带着我熟悉的肉桂和面粉香味。“是吉娜邀我来的,希望不会造成你的麻烦。”
“当然不会!”帕特里克死后,我们仍然维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且九年前她丈夫乔过世后,我们甚至变得更亲近。帕特里克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因此,在乔也过世后,我感觉自己对她有责任,而且这份责任是我乐于承担的,因为我爱她,她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我很开心你来了,琼恩。”
“我要是准时到就好了!”她翻了个白眼说,“你相信我竟然没赶上火车吗?害我整个时程都被打乱了。”
琼恩住在位于长岛上的一个小镇葛兰湾,帕特里克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有时我会担心她独自一人住在那里,被过往的记忆所包围。当初,我在帕特里克葬礼的三个星期后,便搬离了我们在市中心的公寓,就是因为无法忍受在我们曾共享的空间里有着满满的空虚感。每次走进门,我就忍不住期待看见他站在那里。有时在下午时分,我会站在客厅里无法控制地尖叫,而这也引起邻居的抱怨。因此,当我在租约到期前搬离时,房东开心得很。
“别担心,你赶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发现有泪水从我脸颊上滚落,自己也吓了一跳。“琼恩,听我说,我很抱歉。”
“为什么?”琼恩茫然地看着我。
“我……我不希望你以为我忘了帕特里克。”我边擦眼泪边开始啜泣,抬起头不敢注视她的眼睛。
“亲爱的,”她温柔地说,“你可以向前走,也应该要向前走了。”她伸出手臂环抱住我,“我们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好吗?”她带着我到餐厅外面,一走过转角,她立刻从皮包里拿出一包面纸递给我。“凯蒂,亲爱的,已经快十二年了。帕特里克会希望你快乐的,我知道他一定在天堂微笑地看着你。”
我们俩同时抬头仰望天空,今晚整个城市的上空都被云给包覆,遮住了所有星星,这让我觉得天堂非常遥远,我很好奇她是否和我有着相同的感受。
“你还戴着那枚硬币吗?”见到我没回应,她轻声问道。
我点点头,将藏在衬衫底下的银币拉出来,这是帕特里克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在他过世几个月后,我找到一位珠宝师傅愿意帮我将银币打洞,穿在一条长链子上。
她微微一笑。“凯蒂,帕特里克相信这世上有各式各样的好事情。”她说着伸手碰了碰那枚银币。“他相信爱、幸运和快乐,他一定也希望你能得到这一切。这些银币的意义就在于此,你要永远记得,他会希望你拥有最美好的未来,亲爱的。”
“我永远爱他,你知道的。”
“我知道。”琼恩说着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但这并不表示你不能去爱另一个人啊,人生必须继续走下去。现在的你很快乐,不是吗,亲爱的?”
我点点头。
“那就表示你做的事是对的。”她做出结论。“所以,让我们回到你的派对吧?我很想见见你的未婚夫。”
我介绍丹恩给琼恩认识,然后又喝了一杯香槟,这时,有人在点唱机点了一首艾瑞克·克莱普顿的《今夜多美妙》(Wonderful Tonight),丹恩微笑地对我伸出手来。“跳舞吧,我美丽的新娘。”
他夸张地将我旋进临时的舞池,我们一如往常立刻找到舒适的节奏,开始跳起舞来。
朋友们也开始纷纷加入,在我们身边成双成对地翩翩起舞,“派的母亲人挺好的。”丹恩轻声在我耳边说。
“是帕特里克。”我纠正他。丹恩有个恼人的坏习惯,总是用他自己发明的昵称来称呼我前夫。“是啊,她真的很好,这辈子能认识琼恩是我的福气。”
“是啊。”他说完停顿了一下,又补充说:“所以你觉得我们要继续和她保持联络吗?”
我将身体往后退,对着他说:“当然了。”看他没有回应,我继续说:“为什么不要?”我的语气听起来有出乎意料的防御性,因此我露出微笑,试着缓和气氛。
丹恩再次将我拉近。“我只是以为等我们结婚后,你或许会想让那部分的过去结束。但我不介意,她人似乎蛮好的。”
“她是我的家人,丹恩,永远都是。”
“很好。”丹恩迅速地回答。
但这听起来一点都不好,丹恩似乎认为我做错了什么,这让我不禁自我怀疑了起来。
音乐才一结束,吉娜就拿着一杯香槟朝我走来,才踏出舞池,就已经被我分两口干光了。她担心地盯着我看。“想和我谈谈吗?”她边问边拿走我手上的空杯,并且示意服务生再拿一杯过来。
“不用。”酒精已经开始在我脑中起了作用。
“和琼恩有关吗?”她问,“还是丹恩说了什么?”
我点点头,瞥了丹恩一眼。他正和一群同事在舞池里大跳着YMCA,看得出来他正努力想让舞步变得酷一点。“是啊。”我懒得解释了,我想吉娜应该了解。
“如果你在自我怀疑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没做错任何事。”她说。服务生又端来一杯香槟,这次我喝得没那么猛了,但我的头已经开始旋转。
“你确定吗?”
“确定。”她坚定地说,“琼恩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以后也永远是,这件事一点错都没有。”
“好。”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随着时间越来越晚,我灌下一杯又一杯的香槟。趁苏珊还没将珊米和凯文带回家赶上床睡觉之前,我和他们一起跳了傻气版的《有空打给我》(Call Me Maybe)。十点左右,我和琼恩拥抱道别,将她送进出租车,叮嘱她平安到家后要立刻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和丹恩跳舞,他将我拉得好近,告诉我他是全世界最幸运的男人。
将近午夜时分,丹恩的朋友史蒂芬点播了一首枪与玫瑰乐团的《我甜美的小孩》(Sweet Child O'Mine),把他拉进舞池里跟一群朋友摇滚起舞。我移到吧台边的座位听歌,我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唱的不是关于小孩,但还是忍不住一直想到孩子的事。
或许是因为香槟的作用,也或许是因为这世界感觉像个奔走不停的旋转木马,当我低下头不禁想起,要是帕特里克和我刚结婚时,若曾努力生个小孩的话,情况又会如何。要是我在他过世前,我的卵巢还没罢工时怀孕了,会怎样呢?那我现在就有个十一岁的孩子了吧,而帕特里克的一部分就会永远留在我身边。一阵悔恨涌来,让我的喉咙发紧。
歌曲结束,紧接的是一首滚石乐团的歌,丹恩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他在我耳边轻声说句“我也好开心”,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正在哭,他将我失落的泪水误认为喜悦的眼泪。
就让他误会吧,毕竟我的确很快乐、太快乐了,不是所有人都有再一次幸福的机会,于是我深情吻了他,直到史蒂芬和他其他的朋友在远处口哨鼓噪不断。我直起身,看着他的眼睛。
“谢谢你。”我认真地说。
“谢什么?”他微笑着并吻了吻我的额头。
“谢谢你爱我。”我说,“谢谢你让我感觉自己好特别,谢谢你和我结婚,谢谢你努力地了解我,还有……”我说到一半就停了下来,因为我忘记自己原本要说什么。
丹恩笑了,“看来有人喝了太多香槟啊。”他扶着我站起来,他说的没错,我有点歪歪倒倒的。“我要带我美丽的新娘回家,带她上床睡觉,你觉得如何?”
“但我还不是新娘啊。”我辩驳道,惊讶地发现自己讲话全糊在一起了,像是泡在蜜糖里一样。“嗯,好吧,上床睡觉。”
他又笑了,将我拥进怀里,挥挥手和我们的朋友们道晚安,然后带我回家,让我靠在他坚实的胸膛上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