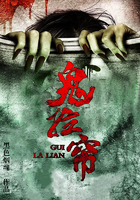弄不清楚在哪儿,周围黑压压的都是树,连成一片,望不到边际的黑色海洋。夜那么深,那么骇人,倾心置身于黑暗之中,耳边除了寒风撕扯树枝发出的阵阵哀鸣,便是自己拼命的嘶喊:救命啊……有人吗?……
眼泪在寒风中像刀子刮在脸上,喉咙早已喊破,口腔里充斥着浓重的血腥味儿。
这里是哪儿?她不知道。
恐怖魔鬼般裹夹着冰冷的空气舔舐她的心,还有被折磨得快要失去知觉的身体。她用肿胀的泪眼重新审视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森林。
求生的本能,使她紧咬牙关,用仅剩的一丝力气挣扎着站起来,沾满泥土的双腿因长时间跪地不受控制的抖动。双手被捆在身后无法动弹,她踉跄地试着走了几步,知觉渐渐恢复,希望像燎原之火,催促她往树影稀少处跑。
从未这般奋力奔跑过,心脏剧烈的跳动,每一秒都要挣脱胸腔的束缚。既便如此,不知跑了多久,明明前方有隐隐的光,却如何也逃不出漆黑的丛林……
就在希望即将燃尽的时候,森林像被人施了魔法,一点点退去,视野豁然开朗,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停满废弃公交车的坟场,斑驳残破的车身,空荡荡的车窗像一具具面目狰狞的丧尸。
倾心惊恐的环视四周,诡异的气氛不由得让她倒吸了口凉气,不想吸入的却是被现代文明遗弃后的腐烂气味,犹如腐尸的臭味。
一阵巨烈干呕,吐的肝寸断,五脏六腑仿佛倾囊而出。她发狂似的拔腿狂奔。
想跑……一声声鬼魅的笑声从废弃的汽车中传来。
突然间,僵尸般的汽车摇身变成一具具血肉模糊的丧尸,血盆大口向她袭来,她“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倾心吓得坐了起来,须臾间,血淋淋的噩梦消失,刺眼的光晃入眼底,她被人抱入了怀里。
“别怕,没事了。”陈铎搂住惊醒的倾心,温暖的手摩挲她的后背,“我在这儿,别怕。”
她头抵在陈铎的胸口,手指揪住他胸前的衬衫,良久,缓缓地抬起头,陈铎俊郎的脸出现在眼前,那深邃漆黑的眸子如此熟悉,她怔怔的看着,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你是谁?”她推开他,退到床头,因为太过用力,头一阵的眩晕,好像坐过山车的失重感。
陈铎扶住她:“你刚醒,别乱动。”
“谢谢,”她勉强挤出两个字,手撑住头,脑子里像有东西在搅,无法形容的感觉。
“先躺下,”陈铎搀着她,让她顺着自己的手劲儿躺下,“医生特别嘱咐,你要多休息。”
倾心陌生地看着他,“你是谁,告诉我好吗?我……”倾心眉头深锁,抚着太阳穴说:“我一时想不起来。”
陈铎掖被角的手忽然停了动作,“倾心......”他对上她满是疑惑的眼神,喉结滑动,“我是陈铎,你的老公陈铎。”怕她不信,“我们已经登记结婚了。”
“结婚?”倾心睁大眼睛,不敢置信,“我怎么不记得?”
犹如冷水兜头泼下,陈铎表情凝住。她肚里子怀着他的骨血,半月大的胎芽,一个可爱的小生命,她竟然把他忘了。
心上像被人豁开一个洞,指关节攥得发白,好一会他才找到声音:“你先休息,别想太多。”他温柔的笑笑:“听话,我出去一会。”
她的记忆出了问题,珍视如命的女人,没保护好。素来冷静的陈铎一拳砸在病房外的墙上。一念不忍,造成今天这种局面。
昨晚若不是瑞丰总裁临时改约,如果不是他想给她一个惊喜,他不敢设想结果会不会更糟…….行程有变,陈铎提前归家,车行至小区门前,傍晚的残阳被积云遮去了颜色,天还没有黑下来。陈铎放下车窗,刷卡通行,却见东边人行路上倾心的身影,同时晃入视线的还有尾随其后的黑色骄车。
陈铎心上一沉,调转车头追上去。同时拨倾心的手机,不等接通,就见那辆车上跳下一个矮胖平头的男子拦住了倾心,随后在她面前抖了一下手,紧接着倾心被拖上了车。动作麻利,一气呵成。
陈铎刹时急红了眼睛,一脚油门咆哮地冲上来。到底是豪车提速快,几秒钟车身超过了那辆黑色轿车,他猛的打方向,一声刺耳的急刹声,车子横在了那辆车的前面。
那辆车刹车不及,一头撞上了陈铎的右车门,发动机盖登时翘了起来,白烟翻滚。
陈铎迅速跳下车,猛力拽开那辆车的后门,绑匪见势不妙,撒腿就跑。黄毛司机被撞得满头是血,晃过神,捂着伤,弃车而逃。
顾不得那么多,陈铎抱出失去知觉的倾心,驾车直奔医院。因为撞击力集中在车头,倾心的位置在司机后面,所以并没有外伤。
当医生拿着倾心检查结束告诉陈铎,一切正常,但因怀孕初期,胎儿不稳,须卧床休息时,陈铎百感交集。不禁为自己撞车救人的做法捏了把汗。
当时情急之下别无他法,担心她被绑匪伤害,幸好无事。这孩子算是命大。陈铎在病床前守了一夜,等倾心醒来,把消息告诉她。
不料却是这样的结果……..
这一刻,陈铎内心是矛盾的,他扯开衬衫的领口,深呼了一口气,却挥不去胸口的郁结。
“怎么会这样?”陈铎找到脑外科赵主任。
赵主任把核磁片子插到光板上,重新看了一遍,转头和陈铎说:“确实未见异常。出现这种情况,考虑是药物麻醉,或是突然撞击造成大脑海马区记忆短暂损伤。”
“多久能恢复?”他急切的问。
“很难说,”赵主任顿了下,“快的话几周。”
“慢呢?”陈铎追问。
赵主任没有马上回答,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慢的话,几个月、几年,甚至更久都有可能。”
陈铎漆黑的眸子陡然暗淡,彻夜未眠的他,看起来状态很不好。“你不要太紧张,”赵主任从桌后绕过来,拍拍陈铎的肩膀:“大部分患者很快都能恢复。”
赵主任试图说服他放轻松些,但并不奏效。陈铎离开医生办公室,穿过半个走廊,停在倾心病房前。透过玻璃,见倾心又陷入了昏睡,陈铎攥紧了拳头,眼睛红得吓人。
“陈总,”小李跟过来。
陈铎脚步沉重地转回身,人疲惫地靠在门上,“给我根烟。”
小李犹豫了下,掏出烟,给他点上。
陈铎大口大口地吸着,脑海里浮现她叫自己戒烟时的话:“你戒吗?我不喜欢烟味。抽烟对身体不好……”
白霭霭的烟雾在指间袅袅升起,这是他答应戒烟后第一次失言。他多希望她能从病房里跑出来夺走他手上的烟,可她却把他忘了。
半根烟抽下去,在尼古丁的安抚下,小李见陈铎的精神提振了许多,才敢开口:“陈总,那两个王巴蛋抓到了。”
陈铎鹰隼般幽深的眸子看向小李,“在哪儿?”小李靠近,和他耳语了几句。
陈铎暗沉的眼底窜起一团怒火,猛吸了口烟,转身看了眼昏睡中的倾心,烟头丢到地上,狠狠碾灭:“走!”
地下仓库,两个劫匪被紧紧捆在椅子上,四周漆黑一片,只有头顶昏黄的一束灯光罩下来。两个人嘴被破布堵着,鼻子发出呼呼的喘气声。
其中,一个男人头发染得金黄,一个矮胖平头。
“不知死活的家伙。”邵伟叼着雪茄斜睨了眼被绑成棕子的两个男人,扭头和靠在沙发上的光头男人说,“他们是哪条道上混的?”
“这种小瘪三也配称道!”光头男吐出一口烟雾,笑了,“他们碰上我就是死道。”
“这种小混混根本不入大哥的眼。”站在光头男身旁,脸上有刀疤的男人抄着一副破锣嗓子附和。
确实,敢太岁头上动土,只有这种愣头青才干得出来。
昏暗的光灯下,邹伟陪着光头男吞云吐雾,很快两人就被团团烟雾笼罩。吱嘎一声,厚重的铁皮门被推开,陈铎走进来。绑在椅子上的两个人看到陈铎,登时瞪大眼睛,止住了呼吸。
陈铎扫了他们一眼,走到沙发前,冲光头男微微一笑:“谢了。”
“随你怎么处理。”邹伟点了支雪茄给他。陈铎叨在嘴里,猛抽了口,转身朝两个劫匪走过去。
那两个人吓得往后靠,肩膀扭动着作困兽状。眼见陈铎逼近,鼻孔撑得硕大,其中一个额角还在流血。陈铎噙着怒火的眼睛,像靠近了汽车桶,轰的炸开。他飞起一脚,两人被踹翻在地,第二脚下去凳子腿断了,两人痛苦的脸扭曲变形,偏又发不出声音,像两个滑稽的哑剧演员。
“陈总道上混过?”脸上有疤的男人问邹伟。
“这两脚够瓷实的,”光头男子摸着锃亮的脑袋说:“要了这俩小子的半条命。”
从小到大,邹伟没见过陈铎这么发狠过。他上前拉住陈铎:“这种粗活用不着你亲自干。”说完,朝站在门口的几个人摆手。
跟班小弟随既在杂物堆里拽出两条破棉被。“专业点,”邹伟嘱咐,然后拉陈铎到沙发上坐。
两个劫匪被从椅子上解下来,接着棉被盖上去,之后就是一阵消了音的拳打脚踢。
打了好一会,陈铎突然出声:“说,谁让你们干的!”
跟班掀开棉被,拔掉绑匪嘴里的破布,剧烈的咳嗽、呻吟声从两人嘴里冒出来。
邹伟上前,撕开绑匪的衣服,不见一点伤痕。“打的漂亮。”他转头给了几个兄弟一个赞许的目光。邹伟鞋底蹬到黄毛男人脸上:“药你下的?”
“不是我,不是我,”黄毛男人吓得直喘粗气,“是他,他下的……”他咧着嘴,指身边的同伙。
眼见被出卖,那人也不遮掩:“是我下的,可全是熊强让我干的。”怕再招来一顿打,他指向黄毛男人说:“是他,是他和他马子怂恿我干的,说敲笔大的给我分层,我就是个帮忙的…….”
“你马子谁?”邹伟一脚踩到那人脸上,熊强痛苦的蜷在地上,“别打了,我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