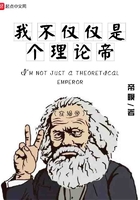“你终于来了。”谢晓娟声音很哑,但清晰,她笑着看云影,“别怕啊,我打不了你了。”
云影轻轻地嗤笑一声。
“听说你女儿丢了。”谢晓娟说完这句话,脸上竟浮现出死灰复燃似的大笑。
云影停顿一下,声音平静地说:“会找回来的。”
谢晓娟笑出了声,随即咳得脸部扭曲,好一阵子才缓过来。她还在笑,说:“放屁!童家这么有本事铺天盖地找,连我都看到不少新闻,能找着早找着了,没找着,早没了。”
谢晓娟看着云影,说:“你就认了吧,就是你克的。”
云影眼睑抽动,坚定道:“不是。”
又是一声大笑,又是一阵咳。
谢晓娟倒也没有反驳她,而是盯着天花板喃喃地说:“下一个会是谁呢?童乐?你儿子?童晋?乐纯?克走了夏家五个,童家也得有五个才公平啊,真好玩,可惜啊,等不到了……反正你命长,有的是时间慢慢来,说不定明天出门又是一个……”
云影面不改色,双手捏紧了真皮包包的带子。她看着谢晓娟,一字一顿地说:“你要下地狱了。”
“谁知道呢?”谢晓娟不甚在意地说,她脸上的笑敛起了些,看向云影眼睛深处,“反正你现在不比下地狱惨。”
云影用力地看着谢晓娟。
谢晓娟继续说道:“我对你不好,也养过你。对了,要是我对你不够坏,你不够可怜,你根本入不了那位菩萨心肠的少爷的眼。毛都没长齐就被随便卖给一户人家,大字不识一个,能过得现在这样富丽堂皇的生活?这是我做的好事。”
“我再难,再苦,也儿孙绕膝,近十年来不愁吃不愁喝,甚至不缺男人,快活自在。你不同,你是命定的,改变不了,你怎么就是不相信呢?”
“如今为时尚早,早晚一天,该来的还是报应,那时候啊,你就能明白,我为什么这么恨你了,我可怜的老三啊……”
谢晓娟一边咳一边笑,一边笑一边咳。
云影走出医院,才再次撞见夏星一行人,刚才该是去买东西吃了,几个孩子正人手一条雪糕。
看到云影,夏星他们没招呼,夏月老公抬了抬手,被夏月横了一眼,旋即收回。
管得住男人,生活都不会差到哪里去。云影讥诮地扯了扯嘴角,脚步未停,径直向前走。
“等会儿!”夏月在身后喊道。
云影慢慢地停住脚。夏月走过来,上下打量她一番,冷笑道:“别找了,你女儿找不到的,让童乐也别再承包电影片头了,观众都要看吐了,没了就是没了……”
云影静静地摇了一下头,垂着眼看夏月,沉着开口:“你们夏家不是最信命吗?我女儿出生后,我婆婆的朋友也给她批命了,好着呢,最少八十岁。童家有的是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别说拍电影,买下电影院又如何?”说着,她不经意似的上前半步,微微低头看进夏月的眼睛:“你管得着吗?”
夏月脸上一僵,马上又哼笑一声,压抑住火气嘲讽道:“是吗?那你可得懂事点,毕竟你的八字挺煞夫家的,别人到中年才离婚收场。”
“那你可有所不知。”云影故意弯了弯腰,凑近她脸,慢条斯理地说,“今天旅游回来,十五年间第一次分开超过二十四小时,一到家就把我拉回房间,缠在一起一个多小时……他那样亲抚我,爱恋我,我真的没办法不承认他需要我太多太多……每当他从我身上得到极致的快乐,他都恨不得拿命还我……中年?”她笑了一下,“今天离,我又亏得哪里去?”
悄悄地说罢,云影站直身子,笑里苦恼地叹了口气,抬手理了理头发,纤细好看的手指里间,一抹璀璨,高贵而闪耀。
夏月咬牙未得,又瞥见云影那一脖子犹如铁证一般的红紫,气得几乎咬到舌根。
云影冲夏月嫣然一笑,随即从身边走过,在众人目送下打开车门,坐进红色小跑里,潇洒地打转方向盘,扬长而去了。
留得夏家人在原地咬牙切齿。
午后的阳光,依旧照射强烈,向每一个暗处延伸。男人拿起手里的烟,又抽了一口,淡淡的烟雾萦绕在那张脸上显得深沉难辨。
明晃晃的地面上,影子动了,烟头扔进了专门放烟头的铁筒。
那个男人走在阳光里的背影,冷冽又平静。
知道妻子到底去见谁以后,童乐也理解了她为何如此反常。甚至认为力度不够,太客气了。
童乐坐回车里,扯过安全带,头向后靠,闭上眼睛捏了捏眉心。蓦地想到了什么,微微露出了一丝苦笑,于是疲惫被封禁,不安在滋长。
思绪沉沦之际,手机响了。
是海康。
童乐和海康是留学时期结交的挚友,两人同校同系同住三年,后又一起转系,拍电影,回国,中间未曾分开过。
之后童乐结婚生子,而海康则在童乐婚后不久宣布当个不婚贵族,这么多年,似乎一直在守护誓言,别说婚娶,身边连个女人都没有。
女儿走丢后,公司交给了海康打理,童乐退居二线。海康一改以往落拓不羁,让童乐放心去做自己的事情,星越有他守住,他就是星越背后的靠山,童乐背后的靠山。
后来,为了更好照顾家里人,童乐没有再回公司任职,只是出席重大决策会议,受聘当起本市重点大学的经济系教授。
有生之年,童乐心中最感激的人,无疑就是海康。
海康在电话里说,昨天晚上他跟朋友上山顶看流星雨,今早下山后又在城郊的民俗村绕了一圈,回来路上遇上了小车祸,车开不了。
童乐神色一沉,立即问道:“你没事吧?”
“就一点小伤,无妨。”海康也没有隐瞒,他似乎深吸了一口气,“你来接我吧。”
童乐把手机扔一边,旋即打转方向盘,把车开得飞快。
云影离开医院后,没有马上回家,半道上路过花店,她在那儿买了一大束玫瑰花,打算去看姐姐,很快又想起姐姐不在那里。
那个地方只是欺骗人的假象。
姐姐不在那里,被人藏起来了,像童遇安一样被人藏起来了。
可是她真的很想念姐姐,想念姐姐茉莉花味的体香,想念姐姐的温言细语,想念姐姐的怀抱。
辽阔的江面在阳光照耀下,像蓄满了金子一样。云影坐在车里,双手抱住大把的鲜花,嚎啕大哭:“不会的,不会的,我不会的……”
那天下午五点,云影才回到童家。
家里只有乐纯和李妈在花园里剪花,童晋带两个孙子出去了。
云影打了声招呼,就上楼了。她没有回她和丈夫的房间,而是到女儿房间。
只是,她开不了门。
门上的锁明显被人换过了。
就像当年她突然打不开童乐的房间门一样。
云影顿时脸色大变,转身下楼,大声呼喊李妈。
一时间整栋别墅似乎都是云影的声音。
“在呢,怎么了?小影……”李妈拖着胖胖的身体从花园里小跑回来。
云影抓住李妈的手就问道:“谁锁了安儿的房间?”
李妈脸上闪烁了一下,欲言又止:“这……”
云影语气重了:“是谁?”
“那个,小影,大家都是为你好,只要你不去想不去碰,慢慢地都会好,就像阿乐刚出国那年,你刚开始也……”
云影什么都听不进去,大喊道:“我问你是谁?!”
李妈吓了一跳。
这时,乐纯平静的声音传来:“是我。”
云影放开了李妈,快步走到乐纯面前站定,她深吸一口气,尽量平静地说:“妈妈,把钥匙给我。”
乐纯今年六十三岁了,但保养得宜,整个人看上去起码比实际年龄少上十岁,加之出身极好,身上那股高雅脱俗的气质与生俱来。
时至今日,云影仍能清晰回忆起第一次踏进童家,她站在乐纯面前,像一件商品一样接受打量,那种由身入心的深度压抑,令她在此后数年间如何改变,在乐纯面前都将打回原形——瑟缩的身影、蜷缩的心态、低头的安然。
“要来做什么?”乐纯问道。
“你锁住做什么?”云影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