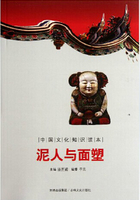马克·扬科维奇
安东尼奥·拉萨罗·雷沃尔
朱利安·斯特林格
安迪·威利斯
“邪典电影”这个词涵盖了众多罪恶,对于这一类型的构成,杰弗瑞·斯康斯或许总结得最好,他说,“这个概念可以将很多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电影亚类型包括进去,比如‘烂片’(bad film)、血块电影(splatterpunk)、残酷实录(mondo films)、刀剑草鞋史诗剧[1]、猫王表演(Elvis flicks)、政府的卫生保健片、日本怪兽电影、沙滩派对歌舞片,还有剥削电影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的不同面目,从青少年犯罪纪录片到软性色情片”(Sconce 1995:372)。不幸的是,我还是要指出这并没有括尽邪典电影的全部类别,斯康斯只能将其余部分都归为“另类电影”(paracinema)——一个从更大的集合中筛选出来的小小亚类型。
虽然名为“定义邪典电影”,但本书并非旨在鉴别某部影片为何会受到邪典粉丝圈[2]的关注。与其说是想挖掘出能定义邪典电影的基本要素,还不如先将邪典电影的本质理解为不拘一格的类别。事实上,并不存在所有邪典电影通用的某种个性,因而也无法据此来定义它,必须通过存在于电影制作者、电影作品或观众之中的“亚文化意识形态”去思考,这种“亚文化意识形态”被视为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的(关于“亚文化意识形态”的研究,参见Thornton 1995)。换句话说,“邪典”总体而言是一种以消费行为来界定电影的方式,尽管电影制作者常常与粉丝分享“亚文化意识形态”并早已开始刻意制造“邪典”素材。
事实上,“主流”本身也不是一个能准确界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他者”。举例来说,在《不可思议的怪片》(Incredibly Strange Films,1986)这本有关邪典电影的书里,“主流”被描述为群体力量、下层中产阶级的从众心态和假正经、学术精英主义和政治阴谋的混合物。尽管很松散,但主流的核心地位还是维持住了,因为邪典影迷需要用它来制造出将自己与费斯克(Fiske)所说的“更‘普通’的通俗观众”区别开来的感受(Fiske 1992)。换句话说,主流的存在很有必要,因为只有通过展示这种“对立”关系,邪典电影观众才能对自身以及对那些把他们召唤到一起的电影赋予价值。
不过,即使是邪典粉丝自己与这些电影的关系也不是一致和连贯的。有时候,一些粉丝将某些电影奉为真正的艺术和政治独立之作,认为电影中区别于主流的特质与政治和(或)文化上的特立独行直接相关;而另一些粉丝却用高人一等的姿态,甚至彻头彻尾的蔑视去看待他们追捧的那些电影。换句话说,很多邪典电影之所以受人追捧,是因为它们是被拿来嘲笑的(参见本书中丽贝卡·费塞[Rebecca Feasey]的文章)。比如在1970年代,《疯狂的大麻》(Reefer Madness)成了一部大热的邪典电影,正是它那蹩脚的反大麻教条让它成了大都市年轻观众的笑柄(Schaefer 1999)。同样,“烂片”被人们欢呼也不是由于它们艺术上的独立性或政治上的复杂性,而是因为试图遵循艺术或政治上的“主流”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这类失败在人们看来往往揭示了主流规范的陈腐套路(参见本书中杰弗瑞·斯康斯的文章)。
不过,尽管邪典粉丝总是表现出自己的对立姿态,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其实是中产阶级男性,他们的对立姿态往往是对资产阶级趣味和男性特质的维护而非挑战。比如说,他们对“烂片”的美誉,不仅是一种形式主义陌生化——布尔迪厄将其阐释为中产阶级审美的核心,这与中产阶级的物质保障直接相关(Bourdieu 1984;Hollows and Jancovich 1995),还涉及特定社会群体的他者化问题。换句话说,邪典电影粉丝的对抗性趣味并不是底层挑战中产阶级,而应在某种程度上视为中产阶级的内部(而非敌我)矛盾(Sconce 1995;Jancovich 2002)。在这些较量中,邪典电影粉丝圈被扯进了“文化中产阶级”挑战“经济中产阶级”权威的过程中。不过,讽刺的是,这个过程往往将中产阶级的下层变成了替罪羊。所以这一挑战丝毫没有威胁到上层中产阶级的权威,反而是种保障。
并且,正如本书中乔安妮·霍洛斯(Joanne Hollows)的文章中所言,这个过程还与性别政治息息相关。下层中产阶级的“他者化”往往是与对他们的“女性化”分不开的。无需惊讶,邪典电影粉丝圈不仅维护了中产阶级的趣味,而且还与男性特质的合法化过程密不可分。造反审美(aesthetics of transgression)(和有意识地去创作“邪典”作品的人)极大地巩固了邪典电影粉丝圈,它们往往直接与家庭生活的价值观对立,因为这种价值观不仅表现出女性特质,而且在历史上一贯被认为属于女性的责任。
其结果是,尽管邪典电影观众总是表现出反学术化和反市场化的姿态,但实际上邪典电影粉丝圈的出现及发展始终在与学术化和市场化这两者暗通款曲(参见Jancovich 2002)。一方面,正如我们所见,邪典电影观众经常采用中产阶级审美的阅读策略,特别是形式主义陌生化原理。其实,正如扬科维奇所言,邪典电影粉丝圈和邪典电影学术研究是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的,而稍后学科内部的“激进化”浪潮也与邪典电影粉丝圈中的变革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电影研究的规范正是这一波粉丝潮的产物。因此,毫不奇怪,本书的四位编者全都是邪典粉丝,这一粉丝身份正是他们的文化资本和属性,既将他们引入电影学术研究中,又使他们能够带着这样的身份去工作。
不过,粉丝圈还与市场性质的变化,尤其是二战之后小众市场的出现有关。是时,普通电影观众的数量急剧衰退,许多影院老板通过开办艺术影院发现了“专业观众”(specialist audiences)的价值。随后又出现了“剧目影院”(repertory cinema)[3]和“午夜影院”,它们正是市场应对的产物,某些内城区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些电影的受众群体也改变了。“午夜影院”更是与邪典电影粉丝圈关系最密切的电影现象。
事实上,邪典电影的文化地理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正如霍洛斯所言,最初,群体聚会主要是在内城区地带,这里被认为与家庭内部的女性化空间截然相反。但它不单单是一个“内城区”现象,还与特定的“文化资本”有关(Zukin 1995),主要以纽约尤其是曼哈顿的大部分地区(Gomery 1992;Jancovich 2002;以及本书中贝茨[Betz]和霍金斯[Hawkins]的文章)为核心。
这样一来,内城区现象就不仅涉及特定的社会阶层,还与特定的文化权力和权威核心有关。于是,正如安德鲁·威利斯(Andrew Willis)的文章所言,这个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即许多邪典电影都是从某个特定的文化地缘中移植出来,又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被消费的。但是,这些作品在新语境中大受追捧,不仅是由于它们与所谓的“主流”格格不入(尽管实际上这些电影在自己的文化中很可能是“主流”的),还因为涉及他者文化的“异化”问题。或者说,邪典电影粉丝圈总是对“奇异又奇妙”的世界电影大加赞赏,但他们的欣赏方式与这些影片的生产语境之间毫无关系(例子参见Tombs 1998)。
文化地理学对于特定的放映场所有重大意义,而且关乎它们随着时间流逝发生变化的方式,不过,放映模式也影响和改变了邪典电影粉丝圈的地域性组织。录像带、有线电视、卫星通讯以及互联网等新媒介都对邪典电影粉丝圈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新科技使邪典电影粉丝圈很少再囿于地理的限制,可以跨空间发行和传播邪典资料。培养更大规模的小众观众已经成为可能,或许它们只在小范围扩散,却足以构成强大的市场动力。而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却威胁到了邪典电影粉丝圈对于其赖以生存的差异性和排外性的感知,使他们苦心建立起来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不仅如此,新科技还能让世界各地的影迷互相交流甚至形成集体,并让这个行业有能力把他们建构成另一个小众市场,这就对他们的对抗性和自我身份的认同造成了威胁。不过,虽然这些科技能使“时空压缩”,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是存在着因为空间分布的关系而形成的不平等,很多情况下新科技甚至在加剧这种分化。
举个例子来说,录像带的崛起威胁到了粉丝圈的排外性,因为“所有那些我甘冒生命危险去看(字面意思,在某些影院里确实如此)的晦涩电影,现在都能在你家门口那家干净整洁的录像带店里买到!这让人有点沮丧”(Frank Henenlotter,引自Vale,Juno and Morton 1985:8)。不过,英国录像带法规的调整也引发了一种全新邪典电影形式,即史上第一个不涉剧院放映的类别:下流录像(video nasty)。当然,内容就是属于“违禁品”的下流视频,然而正是这样的特殊身份让它们很难轻易获得,也让人们格外珍视和渴求这些与“主流”产品完全不同的东西。
本书中的文章都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了这些五花八门的问题及其发展过程。有些文章比较关注普遍性的理论问题的探讨,有些则从事的是具体的影片、导演、类型和明星的研究。有的文章将焦点放在电影生产的语境中,有的则通过营销手段、围绕影片产生的粉丝媒介以及对其批判性的接受,来分析邪典电影的媒体化问题。在此过程中,许多文章还包含着对教学及研究领域内学术实践的批判性和自反性的关注。
比如说,在本书的第一篇文章里,斯康斯考察了研究“烂片”的价值,特别是在教学实践中。在他看来,电影研究应该好好拷问教学实践的目标和对象,不仅要质疑电影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性质以及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还应迫使教师重新审视它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生都是带着期盼和渴望进入电影研究领域的,结果这门课却把他们弄得稀里糊涂、心灰意冷。斯康斯认为,转而研究“烂片”或许能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因为这样的研究不仅能教给学生形式分析的基本问题,还能让他们立足于这个层面去关注更广泛的理论和历史问题。换句话说,它揭露了电影范式的普遍本质,并鼓励学生们去追问这些范式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样子。
在此过程中,上述文章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不仅是为了给邪典电影研究正名,而且试图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置于学科的核心地位。当然,风险总是有的:这些烂片太过拙劣,也许只能供人嘲弄,以至于对它们进行研究反而是在加固既有的规范而不是去对抗它。更有甚者,斯康斯看到,陌生化仍然是电影研究活动的中心,而这样的问题在乔安妮·霍洛斯的文章里遭遇了挑战。
第二篇文章关注的重点不是电影的形式分析的问题,而是文化消费过程的问题,电影在其中被同时视作文本对象和物质文化对象。她考察了文化消费过程是以何种方式与性别表现产生联系的,尤其是邪典电影粉丝圈如何紧密围绕男子气概的特殊表现来运转,又是如何将自身建立在对女性特质的他者化上的。换句话说,她证明了邪典电影粉丝圈不仅与想象性的他者——“主流”对立,而且这个他者本身就与女性特质有关。在此过程中,她还考察了邪典电影粉丝圈在空间上的形成以及相关的消费与收藏活动。
这些主题也出现在贾辛达·里德(Jacinda Read)的文章里,她考察了当代研究邪典电影的一些学术论文,尤其关注学术“迷弟”(fan-boy)的特质。1990年代出现了对学者的影迷身份予以正统化甚至为其欢呼的倾向,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的著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Jenkins 1992)。不过,当这部著作质疑学术界对“通俗”的蔑视和疏离,鼓励学者承认和探讨自身对通俗文化的投入时,里德却发现了一个挑战学术责任观念的全新变量,它的策略与1990年代的“新派小子杂志”(lad mags)——《纸醉金迷》(Loaded)、《男人帮》(FHM)和《马克西姆》(Maxim)[4]等非常相似(Jackson,Stevenson and Brooks 2001)。里德认为,理解这一批评理论,应该从男性气质的特定焦虑入手,尤其是男性气质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焦虑。正如里德所言,这一批评理论把消费行为与女性特质联系起来,是要通过区分“男性粉丝”和“女性消费者”来维护男性气质。
如果说,上述文章提出了邪典电影学术研究中的普遍问题,那么接下来的几篇探索的是邪典电影中的某些特殊方面。比如,安德鲁·威利斯考察了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的西班牙恐怖电影风潮,并证明了一点:这些影片在西班牙之外的地方被邪典电影观众以特殊方式进行消费,但它们在自己诞生的语境中却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探究了一批正统电影和(或)艺术电影导演为何都在西班牙历史上的某个特殊时刻转向了恐怖片制作。他的观点是,西班牙的艺术电影只是拍给经过甄选的精英知识分子看的,它们在海外也只能进入艺术影院放映。而转向摄制通俗的恐怖电影后,那些激进的西班牙电影人就能以隐蔽的方式处理颠覆性的素材,兼顾西班牙普通观众的趣味。换句话说,西班牙的艺术电影尽管也批评佛朗哥政权,但还是被认为满足不了西班牙广大观众的需求,甚而成了佛朗哥政权的“遮羞布”:这些电影在国际上亮相,给人们造成了佛朗哥政权压迫性小、自由度高的错觉,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恐怖电影只面向国内市场。相反,恐怖片的大量生产乃是因为这是最容易出口的电影类型,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观众。威利斯认为,由此可见:西班牙的语境无法引领我们通往这些电影的“真正”意义,因为这个重要语境往往被邪典电影粉丝圈中的一部分人忽略甚至否定,他们为这些影片欢呼只是把它们当做猎奇和歌颂异国风情的范本。
这种对邪典电影粉丝圈的国际性和跨文化维度的考量,也引发了哈莫尼·吴(Harmony Wu)的兴趣。在文章中,她一边对彼得·杰克逊的电影进行分析,一边审视邪典电影制作的国际化语境,不过重点放在了杰克逊“以恐怖片进行交易”的方式上。换句话说,正如吴所言,“彼得·杰克逊的呕吐电影(gross-out films)……为他积累了足够的资本(既有经济上的,也有电影上的),能够超越好莱坞阴影下微不足道的民族电影产业的限制,获得了几乎不可能的成功”。这一策略在最近上映的现象级大片《指环王》中得到了回报。不过,文章聚焦杰克逊早期的呕吐电影时,也比较了《罪孽天使》(Heavenly Creatures,1994)的策略,这部电影也是以暴力为卖点,却吸引了完全不同的邪典电影粉丝。换句话说,她不仅考察了世界范围内邪典电影观众在经济上的重要作用,还探究了不同类型的邪典电影粉丝圈之间的差异。
如果说刚才提到的这些文章主要关注的是邪典电影制作的语境问题,那么厄内斯特·马斯伊斯(Ernest Mathijs)考察的是邪典电影的批判性接受,尤其是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的声望。文中,马斯伊斯考察了各类刊物对于柯南伯格的电影《毛骨悚然》(Shivers,1975)的解读,特别是那些从争议性和话题性角度入手的。正如马斯伊斯所言,这个过程不仅以极为特殊的方式建构了电影的意义,成就了电影导演,而且还使批评家本身得以合法化,即“通过帮助《毛骨悚然》获得邪典电影声望,这些批评家显示了自己在邪典电影问题上的权威”。随后,马斯伊斯观察了(邪典电影声望的)生成机制,影片及其导演的互文性结构正是通过这一机制得以建立和发展的;此外,他还考察了影片是如何成为表现“邪典”魅力的对象的。
如果说马斯伊斯关注的是电影批评,那么彼得·哈钦斯(Peter Hutchings)通过对达里奥·阿金图(Dario Argento)的研究将粉丝和学者的批判性回应进行了比较。在此过程中,哈钦斯指出,许多学术研究都“遮蔽了区域化的‘邪典’特性对于特定对象的反应,以达到建构一个更广阔的文化抵抗和造反图景的目的”。因此,他专门研究了英国地区(对阿金图电影)的反馈,通过分析他发现许多粉丝把阿金图看作具有邪典身份和资质的导演,并强调大多数粉丝都极其推崇他,尊他为“大师”,而不是像很多粉丝行为研究中认为的那样,对他进行文本盗猎以及抵制和侵犯(例子参见Jenkins,1992)。哈钦斯的结论是,新闻记者写的影评、学术性影评和粉丝的影评“各有其独特性、背景和议题”,不可能“归为一个整体”。不过,这并不会让邪典电影研究功败垂成,反而意味着要对这些五花八门的“具体表现”予以更大的关注。在哈钦斯看来,“分类只是理解邪典电影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关于柯南伯格和阿金图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邪典粉丝圈不仅明确地承认邪典电影是邪典作者[5]的作品,还将这些导演与特定类型联系在一起。从本文开头引用的斯康斯所列的类型可以清楚地看出,某些类型或亚类型与邪典电影粉丝圈之间存在着极大关联。比如,柯南伯格和阿金图都拍过大量的恐怖片,他们与恐怖片之间的关系也总会牵扯到邪典电影粉丝圈。正如罗宾·伍德(Robin Wood)在他那篇非常经典的美国恐怖片研究中所言,这种“大受欢迎的类型自有其不寻常的特质,与其他类型片截然不同:它只受狂热影迷的欢迎,其他人对此完全无法接受。人们要么着了魔似的爱看恐怖片,要么从来不看”(Wood 2002:29—30)。
事实上,其他类型片也有类似情况。茉雅·拉奇特(Moya Luckett)在她研究性剥削片的文章里考察了桃乐丝·维斯曼(Doris Wishman)的电影,从女性导演和观众的角度重新评估了这一类型的价值。她的结论是:尽管听起来令人惊讶,但“性剥削片在当时的低成本电影制片业中似乎是女性的专属领域”,不仅如此,“女性特质或许已经成为邪典电影的结构性力量,并且在此过程中重塑了电影对‘性差异’的表达”,尽管它往往“隐而不见或出现在不合时宜的地方”。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维斯曼的职业履历,对其作品风格进行了文本分析。最重要的是,文章称维斯曼不仅“使男性有目的的‘观看’行为不断受挫”,而且还“让女性凝视和女性观影者享有某种特权”。
类型与身体奇观的关系也是里昂·亨特(Leon Hunt)的动作片研究关注的焦点。如果说拉奇特将重点放在导演与类型的关系上,亨特则考察了明星的形象、表演与类型之间的关系,并探究了本真性(authenticity)是如何在邪典电影粉丝圈中被建构和评价的。不过,正如他所强调的,本真性是个“难以捉摸的字眼”,一千个影迷有一千个理解。比如说,有些影迷关注的是某种打斗风格的纯粹性,有些则注重表演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是拍摄技巧或特效做出来的。最后,就算风格变得模糊难辨,仰仗电影科技成了新时代的规则,一些影迷还是再次将关注点放在了演员的形体表现上。比如,成龙的电影经常通过拍摄失误的花絮来展现本真性,其中包括成龙遭到殴打或身体受伤的画面。亨特通过考察粉丝话语来评价电影并观察解读电影的方式,不过他也承认,这个过程应当置于全球化的文化中去思考。他不仅研究了西方邪典电影观众而不是香港观众是如何看待这些影片的,还探讨了好莱坞电影产业中不断引入的香港电影工作者和港式风格是如何对上述问题产生影响的。
对于身体的物理形态的呈现,丽贝卡·费塞在研究以邪典方式消费莎朗·斯通的文章中也予以了关注,不过,如果说男性身体所表演的奇观是动作片粉丝所看重的,那么女性身体所表演的奇观在情色惊悚片中却是遭贬低的。费塞以一本邪典出版物《我们爱烂片》(Bad Movies We Love)为考查对象,分析了莎朗·斯通的明星形象以及她的表演对于邪典电影粉丝的意义。她看了有关《所罗门的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1985)和《剪刀》(Scissors,1991)这两部电影的讨论,发现此书的作者们将作为演员的莎朗·斯通与性奇观直接挂钩,她不仅受到了鄙视,而且永远无法翻身。对邪典电影粉丝来说,就算莎朗·斯通的电影“烂到极点”(so bad they're good),她的女性特质也只是供人嘲笑的对象,并且她自己对此难辞其咎。甚而当斯通试图将自己与那些“热爱裸露”的角色拉开距离的时候,反而被视为假正经,引来了更多的嘲笑。不过,正如费塞所言,斯通不仅在《我们爱烂片》一书里供人讨论,还为其撰写了前言,而这篇前言展示出了她截然不同的一面。斯通并没有假装对自己的糟糕演技浑然不觉,而是表现得非常乐于加入对自己和自己的事业的讥讽中。但是,正如费塞所言,她只有通过嘲弄和剥离自身的女性特质,才能“从文化上成为男性中的一员”(Thornton 1995)。费塞以这样的方式证实了女明星的尴尬定位,更普遍地讲,是邪典电影粉丝圈中女性特质的定位问题。
纳森·亨特(Nathan Hunt)的文章也聚焦于邪典出版物,不过是本杂志——SFX[6]。文章考察了杂志中各种琐碎信息的重要性。亨特指出,这些细节既不应该被简单地否定为毫无价值或毫无意义的迷恋,也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激进的文本重读行为。与此相反,他阐述了这些鸡毛蒜皮的信息是如何在粉丝群的规范化中发挥作用的,特别是他们如何利用这些来界定特定文化文本的所有权的。换句话说,尽管大多数文本也会被特定粉丝群之外的那些观众消费,但影迷可以利用这些鸡毛蒜皮的信息来确保自己与文本之间存在某种特殊且具有优势的关系,并借此营造出一种感觉,即他们拥有某个文本。这显然有助于粉丝捍卫他们这个群体的边界,把“真正”的粉丝与文化上的“误入者”及“游客”区别开来。最后,这些鸡毛蒜皮的信息还可以用来制造、维系和协商粉丝圈内部的等级制度,这可不是詹金斯所形容的公有制乌托邦,而是要靠同性别社交圈[7]中的竞争来一分高下(Jenkins 1992;以及霍洛斯在本书中的文章)。
最后两篇文章探讨的是邪典电影与艺术电影的关系。邪典电影通常被视为通俗文化甚至底层文化,但它所具有的对抗性的、地下的文化感知力恰恰与欧洲艺术电影不谋而合。艺术电影的粉丝圈与邪典电影的粉丝圈不仅从相似的放映方式和学术研究形式的发展中产生(Jancovich 2002),还经常相互影响甚至形成交集。
马克·贝茨的文章重点关注了二战之后欧洲艺术电影的接受问题。但他不仅阐述了艺术电影和邪典电影的关系,还将触角伸向营销领域,发现欧洲艺术电影与剥削电影的营销方式本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前者甚至可能已经取代了后者。在他看来,1959年不仅意味着谢弗(Schaefer)所说的传统剥削电影时代的结束,还意味着“法国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电影的第一个顶峰的到来,标志着艺术电影发展史中现代主义高级阶段的开始”。作为结论,贝茨不仅要求我们反思艺术电影与邪典电影之间的关系,还试图通过“利用文本之外的资料”来寻求艺术电影的复兴,而“这些资料必须是与当前电影和媒介的发展史有着重要关联的”。换句话说,他不仅希望逃离反向势利[8],艺术电影现在经常由于这一特质而遭到无视甚至否定;还希望这种逃离不要退回到不加甄别地赞颂那种具有优越感的电影美学上去。换句话说,他关心的是立足于电影所处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去研究其意义,并将发行和放映作为意义生成的核心元素去考察。或者说,他拒不认为艺术电影能够“‘光荣孤立’[9]于一个不存在经济和物质生活的国度”(Hollows 1995:30)。
上述问题在琼·霍金斯(Joan Hawkins)称为“市区先锋艺术人群”的研究中被赋予了新的形式。对于这个群体的界定,霍金斯是通过“共同的都市生活方式、对形式和叙事实验法的信奉、将人的身体视作社会政治斗争场所的观念、对激进身份政治的热衷以及对财富和权力的制度化机制的不信任”来完成的。与早期先锋艺术一样,它们都有“地下艺术”的敏感;但不同的是,它们“大量借鉴了‘低俗’文化,即情色惊悚、恐怖、科幻和色情”。换句话说,他们是邪典电影与艺术电影交会、重叠、相互滋养的关键所在,而这些交会、重叠、相互滋养正是霍金斯试图强调和分析的。
不过,贝茨和霍金斯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在文章中讨论的运动不仅具有广泛的地理特性,还具有历史偶然性;不仅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还经历了2001年9月11日那场灾难的余震,这个日子极大地改变了曼哈顿的社会和文化景观,世界上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提并论。
我们希望本书中的文章能够就邪典电影及其文化政治提出一系列问题,并且,如果说本书拒绝为邪典电影下定义,那是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邪典电影的文化政治,其关键之处在于寻求定义和差异的整个过程;第二,我们试图不在书中设立任何边界,而是植入有建设性的对话,交换概念与想法。在此,我们非常感谢所有论文作者贡献的时间、经历和慷慨,感谢他们对这本书的付出。我们钦佩他们撰写的每一篇文章,并为能够将这些作品集结成书感到莫大荣幸。